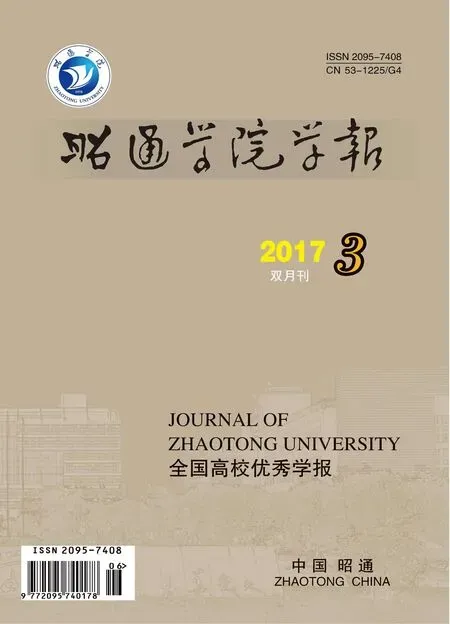姜亮夫先生人生品格之我見
盧敦基
(浙江省社科院 浙江學刊雜志社,浙江 杭州,310007)
姜亮夫先生人生品格之我見
盧敦基
(浙江省社科院 浙江學刊雜志社,浙江 杭州,310007)
姜亮夫先生一生除治學領域宏富、學問博大精深之外,其人生品格同樣令后人高山仰止。綜合來看,其人生品格突出表現為“自強不息”“敬業”“樂群”等三個方面,超越功利主義而追求人生終極價值,對學生及后輩學人具有久遠的啟迪意義。
姜亮夫; 人生品格; 敬業樂群
一、我所見所聞的姜亮夫先生
我于1978年3月來到杭州大學中文系學習,為“文革”后第一屆高考生。來到系里,聽說居然有“八大教授”,一時舌撟不能下。以前小老百姓哪里見過教授?當年的職稱評審制度也極不正常,據說解放后17年才評過兩次,更不用說17年后基本陷入停頓的“十年”。那時一般大學的一個系若有個把教授算是不錯了,但杭大中文系竟然有8個!當然,經過多次運動尤其是“文革”,例有折損,但是姜亮夫先生的大名仍是列在前邊的。其時夏承燾先生已在北京,口傳多時,最后仍未見真容。王煥爊先生,其時為系主任。這三位先生,又在8大教授中名列前茅。
在校四年,見過一兩次系主任,但現在記憶里,似乎沒有見過姜先生,盡管姜先生的大名經常有老師在課堂上傳誦。也是過了很多年后才知道,姜先生身體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已不堪站立,已經不給大學生講課。所以我們無緣得見也很正常。這里要補充的后話是:姜先生后來到1995年才辭世,而與他同輩的能夠站立授課的先生,皆先于他駕鶴西去。噫!人生遭際之不奇,果在此乎,果在此乎!通俗的結論是:一個人,哪怕你身體不好,也不用為長壽操心。
我對姜先生有較深的印象是在大學畢業。當時我們同學自發做了個紀念冊。紀念冊翻開,是領導和老師的題字。領導有兩位,老師則是系王主任和姜先生。王先生的題字很好:“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姜先生的題字則是:“敬業樂群,自強不息”。
我是過了好多年才慢慢讀懂姜先生題辭的含義。其時我是毛頭小伙一個,對長者的智慧,徒識其字,哪知其心?接著到地方上工作兩年有半后,我以考分第一的成績,考到了姜先生任所長的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4年的研究生班,以后才第一次見到了姜先生。這里要解釋一下,我的第一名成績,恰好也印證了高考狀元不能成大器的普遍規律。不過這一點倒是當時我就懂。當時的張涌泉、劉躍進,我早知在學問上必遠勝于我,跟考分多少并無關系。事實的進展恰如預想。
姜先生因為早已不上課,所以他的辦法是,把一班十人全都叫到他家,語重心長地給我們講了一課。一課講了很多內容。然而當時的我,年紀不小仍不更事,先生的話宛如東風過馬耳。只依稀記得示以中國傳統經典十二種書目,分為六大六小,每個學生須讀懂一大一小。今日想來,這是何等重要的治學門徑!然而時至今日,我也沒有讀懂讀通其中之一,當時就更不用說了。另一條記憶就是畢業時,先生高高興興地來到大操場與我們合了一張影。
畢業后,與古籍研究所倒是有聯系的,但由于讀書時不敢去拜謁姜先生,后來也延續了這個不良習慣。又過了好幾年,居然又跟姜先生扯上一點點關系。原來我1993年去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先生唯一的愛女姜昆武老師就在此所工作。有時雨下茶邊,會談到先生及先生之學。尤其是姜先生去世后一年,我自己遭際了一些事情,于是拿起一部《漢書》死啃,突然覺得明白了一些學理世情。其時才對姜先生這位學術大師產生了更多的理解。然而,斯人已逝,以前伸手可及的當面請益的機會永不能覓,此時的我,方于宇宙江山的寥廓蒼茫,初有會心。
二、姜亮夫先生的人生品格之我見
我于姜先生少當面請益的經歷,但是他的學術以外的文字還是看了一些,加上后來與姜昆武老師的閑談,所以自己覺得多少有一點了解。我以為,他的人生品格,恰用他給我大學那一屆畢業的題字可以概括,就是:一、自強不息;二、敬業;三、樂群。
“自強不息”,出自《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今天都知道,宇宙的運行,自有它的軌跡和規律。但如它為一個單純的自足的物體,那么它的規律與軌跡也談不上有什么意義。我自己這次乘機來昭通,在云海上空飛行時,見到寥廓而寂寞的長空,心中也無比的平靜。然而我畢竟馬上要回到地面,馬上要生活在嘈雜紛亂的社會中,這就不得不對人生和宇宙加上一份人格化的理解。古代中國的哲人將“天行”加上“健”的品格。這個“健”,意思多重,康健、雄健、雄深雅健……等等,以一字蔽之。而人要法天,所以必須“自強不息”。翻譯成今天的勵志性話語,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難,你都不要失望,不要絕望,必須永遠保持進取之心,鼓足勇氣,去拼搏,去奮斗。
這不是一個功利主義的考量,不是為了達到某個具體目標的一種標準做法,而是為了實現人的本質所必須的一種永恒態度。人,哪怕只存在一天,都要對未來持樂觀,都要持進取之心,哪怕我們早已知道我們都將同歸虛寂。兩者并不矛盾。《莊子》也是姜先生指定的十二種中國典籍之一,姜先生對道家的透徹了解自在不言中。但是人生在世必須秉持自強不息的態度。這讓人活得有力,活得樂觀,活得有依憑,因而也讓人生充滿了意義。人生本無意義,但是人可以尋找意義。尋找到了意義,人生才顯得有意義!
姜先生的人生經歷正體現了這么一種品格。我知道他在巴黎恭抄“瀛涯敦煌韻輯”時,是抱著為國家繼絕學的念頭。如果說那些事太遠,我也知道先生在“文革”的動蕩顛沛中,也是素心底定,從未悲觀。這未必是如陰陽家算定日后定當無往不復,而應該更近乎儒生的“樂天知命”、“旁行而不流”。我曾于另一篇小文中說到此點:“‘文革’中先生曾留一照片,為惟一之未戴眼鏡者,其時潦倒窮困,無以復加,桌前羅列,無非藥瓶,身上穿戴,皆是舊服。然先生弦歌之聲未斷,青云之志不墜,終身向學,不廢著述,九十三歲方謝世,遠超諸多身體康健之同人。如謂無信念、精神以支撐支離之病體,其誰信與?”
“敬業樂群”,出于《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學校判別教育效果的標準。后面是“大成”、“大學之道”茲皆不論,暫且將此四字拆成兩塊來說。先說“敬業”。
敬業看來簡單,就是敬重你所為的那行,將它做好。它不是一種功利的考量,也是指一種人生態度。古人假設人在社會上有分工,而這些分工皆較為恒久不變。這在技術進步極為緩慢的古代極為正常。你既然從事了某一行業,就要敬重它,善待它,將它做精做好,同時也是將自己的生命意義寄托其中的意思。往極端了講,就是必須干一行愛一行,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職位,肩負該職位的責任。我也曾發揮過此層意思:“面對此業,非敬不可,亦同忠君、愛國一個道理。至于業是否值得敬,君、國是否值得忠、愛,當是第二位事。”在業中要投入所有的智慧和精力,更甚是要投入整個的生命。一個人的一生必須有業,不能游手好閑啃老,要養得活自己,同時亦須對社會有所貢獻,哪怕是在利己條件下的貢獻。司馬遷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跟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同一個意思。如果分工是合理的,你為了利益干好你的職業工作,就是敬業,就是對的。
敬業必須有精神,今天所說的“工匠精神”,說的大概就是這種精神。且莫以為凡是工匠皆有工匠精神,其實,憑我自己對于工匠的調查,有“工匠精神”的匠人其實不甚多。多數人從事工匠還是機會主義者的想法,即為了糊口而已,也不排除有過更好生活的想法。但在技藝上精益求精,只是少數匠人的追求。我們看今天的學術界,凡是有敬業情懷、工匠精神的,不出人頭地也難。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學術事業相對說來還是一個比較公平的領域。姜先生一輩子的勞作,就體現了他的敬業和工匠精神,因而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最后談談“樂群”。從字面上看,“樂群”的意思就是“樂于在群體中生活”。人是社會性動物,不可能完全離群索居,古人的“隱居”、“桃花源”等等設想,也不過是在一個相對偏僻封閉的小社會中生活,少了些同類的傾軋相害而已。
既然在社會中生活,人就應該將自己生活的群體視為快樂的、善意的、有趣味的。這幾乎是一種先驗的設定,應該也是一種有益身心的設定。現實是紛繁的、復雜的、多層面的,它可能是污穢的,也可能是高尚的;它固然是庸俗的,但也可能是高貴的。它有著一切的復合方面。作為生活中的主體,你最好還是多去發現生活中的真、善、美,盡量對丑惡、下流的部分視而不見,至少是少動用自己的身心予以回應。這也是生活中趨利避害的現實一法。當然,任何人都不是凡心不動的神佛,任何人也不可能是不犯錯的圣賢,社會中的錯誤與罪孽常常可能會有我們個人的責任。所以我這里所講的也僅僅是一般化的、粗淺的原則。
“樂群”也同時意味著“為群所樂”。這也提醒了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不應該自以為高明,蔑視眾生,傲嬌江湖。《紅樓夢曲》說妙玉時有“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語,此種劣根性,自有人類似來一直存在,估計今后也不可能改正。所以我讀劉向《新序》“一人舉而萬夫俯首,智者不為也”,不禁渾自頷首。生活中固然經常可以看到眾多的自命不凡者,但不管是內外合一還是名不符實,皆不如平和中正來得恰當,學界尤其。如此也可能減少了許多暗地里的被中傷。
我雖然未聽到姜先生在此問題上的正面立論,但他以他的行為明確地告訴了我們。姜先生似乎不介入學界的一些爭論,他評價學人的學術成果,也多從其學術的源流入手,看清發展的源由脈絡。一旦看清,其成果的利弊高下也就了然于心,無用宣之于口。至于我們同學,幾十年走來,也似無相嫉相爭之病。其性格脾氣愛好特長不可能一致,但大家還是和而不同,相攜相扶,其間有無老師示范與教誨,我不敢說,不過單憑此次討論會的聚首,其樂綿綿,至少說明了樂群的必要和重要。我也曾與一位諳歷世事的官員朋友聊過,他說世界上任何群體總有一些惹麻煩、挑事情的人。你可能會說如果沒有某某這個群體就很好辦。但要提醒你,此人不在了,新來的下一個也可能仍然是這一類。所以不要有完美的想法,而要把它當做常態。此語大有理!但我仍相信如輔之以“樂群”的教導修養,世界大抵會顯得更為潤滑和美好一些。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才能把研究對象做深做透。相比之下,我們的有些年輕人不愿意做這種基礎的工作,一開始就要寫文章,其質量就可想而知了。同時姜老做學問注意普及與提高并重。比如研究敦煌學,既有《瀛涯敦煌韻輯》這樣深奧的專門之作,也有《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概論》這樣的普及之作。他研究楚辭,既有《楚辭通故》這樣的巨著,也有《楚辭今繹講錄》《屈原賦今譯》這樣的普及作品。總之,他每研究一個課題,總是注意從基礎入手,由淺入深,做深做透,最后往往會形成一系列的成果。這種做學問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我們后學認真學習的。
K825.4
A
2095-7408(2017)03-0008-03
2017-06-02
盧敦基(1962- ),男,浙江永康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主要從事古代文學、浙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