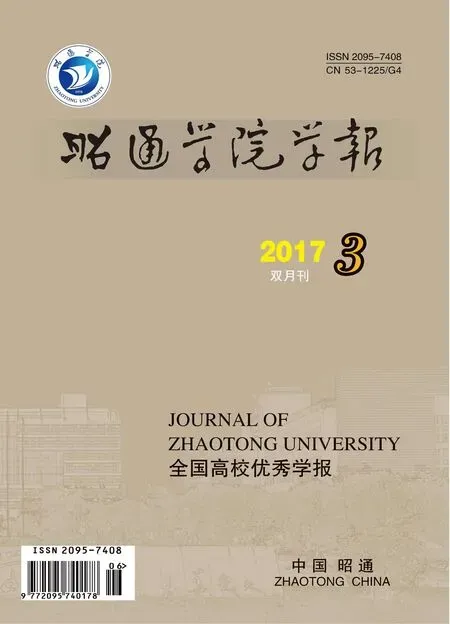《極花》綻放下的道德反思
郗 珂
(云南民族大學 文傳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極花》綻放下的道德反思
郗 珂
(云南民族大學 文傳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極花》是賈平凹的最新長篇小說,講述了一個被販賣到農村去的女孩的故事。這部小說在出版之后便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它所涉及的社會現象,以及賈平凹本人在一些訪談中的言論都讓人們不能將這部小說看作一篇純粹的文學作品。它所蘊含的社會道德的反思力量似乎更能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試圖在尼采的《論道德的譜系》的基礎上從道德反思的角度對這部作品進行淺顯的思考與探究,以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作者筆下所包含的深刻寓意。
《極花》; 《論道德的譜系》; 道德反思
《極花》是賈平凹最新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女性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戕傷史,也是一部直面中國傳統村莊日漸消失的近乎百科全書的斷代史。表面上是一個女孩被拐賣的故事,實際上卻在借用這種特殊的逆城市化向度表達作者對城鄉夾縫中的人群的關切。拐賣婦女兒童這種事情看似遙不可及,但其實也不過就在我們的身邊,每分每秒都有發生。賈平凹以一個作家的身份用文學的手法記錄下了這種畸形的社會現象。一個從農村走到城市的邊緣人再一次被拉回到了農村,在不斷的預謀逃跑的過程中,終是認清了自己的處境與現實,最終安心回歸到農村的故事。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已經忘卻了被拐賣這個令人不齒的行徑,更多的將關注點放在了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上。“為什么要買媳婦?這背后肯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賈平凹說,“小說就是要寫這生活的黑白之間,人心里極難說出來的東西。”[1]《極花》這部作品取材于賈平凹親身經歷的一個事情。一個老鄉的女兒被拐賣之后一群人在不停的尋找線索的焦急,救人的艱難,接回孩子的喜悅,孩子自己又回到那個被拐賣的地方的無奈等,種種心情之間的轉換讓作者開始深入的思考整個事件。千百種不同的思緒在每一個經歷過援救的人心里都存在過,但是到最后,卻只是感到了深深的無力。現實中的故事還在繼續,作品中的故事卻戛然而止在了這里。讀過作品后不自覺的便會開始思考,為什么?為什么那么想要逃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卻還是自己又返回那個千百次的要逃出的地方?作者沒有在作品中給出我們想要的答案,但是似乎我們又可以在作品中自己找出問題的答案。賈平凹說過,如果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要滅亡了。這么一句話曾在網上引起過軒然大波。輿論的指責,群眾的謾罵掩蓋住了作品本身。對與不對的界限已經不再清晰,作品中引申出來的對于道德的反思成為了本篇論文的關注點。尼采曾說“道德的起源只不過是通向一目標的許多手段之一,對于我來說,問題在于道德的價值,”而“我們要批判道德的價值,首先必須對道德價值本身的價值提出疑問。”[2]
一、真實而荒誕,自然而尷尬
“‘好’的判斷不是來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實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說那些高貴的、有力的、上層的、高尚的人們判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好的,意即他們感覺并且確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上等的,用以對立與所有低下的、卑賤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一個初中畢業就輟學的農村女孩胡蝶為了貼補家用和母親來到了城市收撿破爛,但因為輕信他人而被拐賣到了西北的另一個農村,做了黑亮的媳婦兒,成了兔子的媽媽。胡蝶的故事并不新鮮,這樣被拐賣到農村的女孩子數不勝數,甚至如越南新娘、緬甸新娘等雖都是自愿將自己賣掉,但其實質也是對婦女的拐賣。賈平凹將一個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故事用文學的形式表現了出來,由此引發的不再是對于人販子的憎惡和對社會治安不完善的指責,而是更深入的道德思考。買新娘,究竟是好的行為還是壞的?如尼采說的,“好”的判斷不是來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買新娘究竟是好還是壞,便也不能單純的從某一個社會地位的人群的角度來評定了。這個故事是真實的,是作者親身經歷的,透過文字,我們看到了中國農村的腐朽與落后,也看到了中國農村的堅韌與掙扎。但是這個故事是文學作品,是有虛構成分的,它誕生與現實,但卻成長在了虛構中。整個故事都是真實而自然的,但卻透出了某種荒誕與尷尬。
在村民看來,買媳婦是好的,因為農村姑娘都到了城市,農村小伙子只能通過“買”媳婦來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為了種族的延續,生育是必不可少的,中國農村就像一個傳統的部落,他們要讓自己的村子生生不息,他們要讓自己的子孫長久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只有生育才能完成他們的要求。而農村女孩的流走讓村人只能通過其它的方式延續自己的種族。買媳婦,成了唯一的路徑。人類最本能的生存需求使得拐賣婦女在某些落后的農村成了“救命的良方”。而被拐婦女的親人家屬怎么會認同這種“野蠻”的行徑?他們憤怒的尋找,他們失望的尋找,他們淚流滿面的尋找著自己的親人,但是機會那么的渺茫,可以再見面的機會那么的微小。因為被拐婦女被賣掉后大多會被“買家”囚禁在一個隱蔽的地方,以防止她跑掉,這便無形之中增大了被害者家屬的尋找難度,尋找之路是漫漫無邊的,但是小說中,作者用幾筆帶過,把那困難的尋找之路簡化為了幾個簡單的詞組。各種滋味,恐怕也只有參與到事件中的人才能夠真切的體會。而究竟是好是壞,也便無法進行單純的評判。
二、悲憫而溫慧,簡潔而蘊涵
胡蝶的遭遇是值得人們同情的。一個想著為母親減輕負擔的女孩子,一個社會經驗還不豐富的女孩子,那么容易的便輕信了這個復雜的社會,將自己拋入了萬劫不復。在社會中,有很多女孩子愛慕虛榮,想著不付出便可以有收獲,而這些女孩往往會成為騙子的頭號目標。胡蝶其實也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個,但是因為她心中還是想著母親,便也與這些人有了一些區別。胡蝶是愛著城市的,她渴望自己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她穿著時髦的衣服,用母親的辛苦錢買了高跟鞋,她希望可以通過服裝的變化讓自己離城市更近一些。但是城市還是沒有接納她,它用復雜的一面將這個單純的女孩子拋出了城市,拋回到了農村,只不過這個農村并不是她來時的農村,而是更閉塞,更凋敝的農村。胡蝶用手指在墻上劃著道道記錄時間時,讓人們不禁為這個女孩子留下了可憐的淚水。本應該守在母親身邊的孩子,卻被囚禁在了只有一扇窗子的窯洞中。但是悲憫之心無法救出這個可憐的孩子。胡蝶是聰明的,她用自己的方式度過那段黑暗的時光,在老老爺的幾句點撥中,便也參透些許世間的無奈。
整部小說都用一種超然世外的語言為我們敘述著這個引人同情的故事。賈平凹沒有使用過多抒情色彩強烈的文字來烘托胡蝶的悲慘經歷,而是從胡蝶的嘴里講述出了她自己的遭遇,沒有過多的情感渲染,只是平靜的敘述,雖然簡潔但其中還是流露出了許多深刻的內蘊。老老爺這個人物的設定就是如此。他像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神,洞悉著村中發生的一切,他用自己智慧的語言穩定了時時刻刻都想著逃跑的胡蝶的心。不止是老老爺,就連胡蝶自己,麻子嬸,都是不一般的人物。賈平凹雖然寫的是農村的落后與凋敝,但是還是可以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他對農村的懷念和肯定。大智若愚的人是存在在每個村子里的。農村的落后也只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甚至他從這些普通的村民嘴里解決了社會對拐賣婦女這件事情的道德思考。沒有對錯,沒有善惡,不買媳婦,他們就要打光棍了。這是現實,這也是事實。城市在發展,農村也要發展。城市吸引著越來越多年輕的人,但是農村卻流失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堅守在這里的人不得不違背所謂的“道德”,不得不做一些不那么道德的事情。可是一切也不過只是為了繼續活著,繼續讓凋敝的農村活著。所謂道德,不知道究竟應該用何種批判角度對其進行界定。
三、清晰而混沌,疼痛而隱忍
“‘好’即使那種迄今一直被證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級的有價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價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說的,這種解釋方法也是錯誤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從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腳的。”[2]尼采定義了清晰合理的好,賈平凹卻模糊了好的概念。《極花》講的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被拐賣女孩的故事,但是作者的敘述卻是不那么清晰的。胡蝶究竟有沒有見到母親?究竟有沒有回到出租屋大院?從文中我們似乎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也許胡蝶回去了,見到了母親;也許她只是做了一個終于逃出去的夢。但是不論是否回去,最后的最后,胡蝶在這個村子里,在她的窯洞里,在黑亮和兔子的身邊。她開始變得像是一個村里人的時候也就預示了這個故事的結局,從農村出來再回到農村的胡蝶,終究也不過是一個飛在農村上空的蝴蝶,她追求的城市只是一個美好的夢境。
《極花》中農村的破敗與落后像是一根刺扎在了手心,輕輕一握便感受到了那鉆心的疼痛。誰的錯?我們不可而知。但是農村是無辜的,農村里的人是無辜的,被販賣到農村的女孩子更是無辜的。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中曾說過“政治優越觀念總是引起一種精神優越觀念。”[2]城市相較于農村是更接近政治中心的,于是城市用它的優越感俯視著農村,踐踏著農村,甚至蔑視著農村。農村人在這個被輕視的環境里茍活著,隱忍著。他們連買到一個只在城市待過很短時間的媳婦都會覺得是值得驕傲的事情,這種扭曲的心理拉大了農村和城市的距離,模糊了道德與不道德的界限。也許在未讀過《極花》這部作品之前我們會對拐賣婦女的行為大加貶斥,覺得這些沒有道德的人都應該得到最嚴酷的懲罰。但是讀過后,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東西在心里悄然發生了變化。為了發展和生存,淳樸的農村人自動忽略了一些不被人接受的東西,他們始終用一顆最單純的心去考量這個世界,拯救這個已經快要凋零的極花盛開之地。道德的標準不是一句話,一個人,一件事便可以劃定的,有時候我們認為的道德也許正是踩著無數的看似不道德而界定的。
所有高貴的道德都產生于一種凱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隸道德則起始于對“外界”,對“他人”,對“自我”的否定,這種否定就是奴隸道德的創造性行動。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正確的道德,在讀過《極花》之后便有些模糊了。拐賣婦女確實是不道德的,可是農村人用一生的積蓄去買一個媳婦延續后代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這個我們或許真的無法做出很好的判斷。在賈平凹因為這部作品遭到大眾的指責時,一種新的思考便油然而生,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惡?賈平凹說“以小說為新聞事件賦形為的是解開時代面影,挖掘拐賣之地的生存狀態,探究人性的‘褶皺’。”[1]一部被拐賣婦女的血淚之歌讓人潸然淚下,但是中國傳統村莊日漸消逝的境況更是引起人們的深刻思考。胡蝶最后逃回那個讓自己痛苦的村子時,百思不得其解,做夢都想要逃出去的地方為什么又那么輕易的便選擇了回去?細細思考,也許這才是農村人獨有的道德。對于那些指責與謾罵的人,更應該去重新細讀一下這部作品,進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畢竟,《極花》只是一部單純的文學作品,它所講述的永遠不可能和現實等同起來,如果拋開它的文學性而去談社會道德,那么作者希望通過作品所傳遞的內容便也將不復存在。
[1]毛亞楠. 賈平凹:《極花》不僅僅是拐賣和解救的故事[N]. 方圓,2016(6):66-69.
[2]尼 采. 論道德的譜系[M]. 北京:北京三聯書店,1992.
[3]賈平凹. 極花[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4]賈平凹. 《極花》后記[J]. 東吳學術,2016,(01):53-57.
Moral Reflection under the Blossom of Jihua
XI K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500,China)
Jihua is Jia Pingwa's latest novel, tells a story of a girl being trafficked to the countrysid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ovel has been a great concern. It involves social phenomena, as well as Jia Pingwa's remarks in some interviews so that people can not be the novel as a purely literary works. It embodies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and moral power seems to be more people's attention.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make a deep study of th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Nietzsche's ethical pedigree,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the author's pen.
Jihua; ethical pedigree; moral reflection
I207.42
A
2095-7408(2017)03-0057-03
2017-03-28
郗珂(1992— ), 女,山西陽泉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