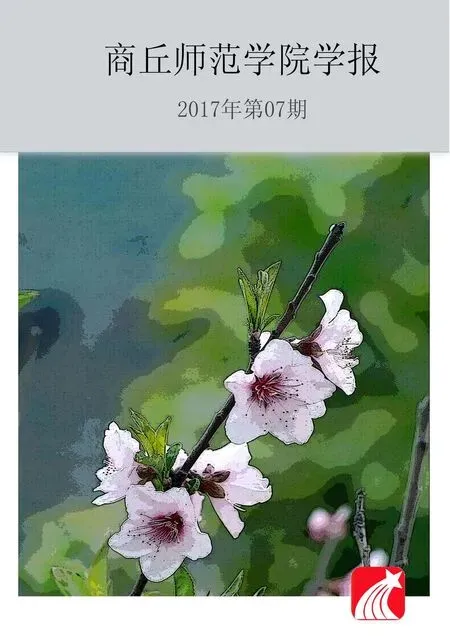論節日祭祀中的集體文化記憶
王 憲 昭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論節日祭祀中的集體文化記憶
王 憲 昭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傳統節日是集體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而祭祀則是眾多傳統節日中最為常見的文化現象,祭祀活動在保存人類古老文化記憶和培育優秀文化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節日祭祀對傳統集體文化記憶具有修復與重塑功能,同時,在當今文化建設中也有必要關注集體文化記憶在節日祭祀中的理性升華與價值實現。
節日;祭祀;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是保存和再現人類智慧的一種重要形式,就個體而言,是人的大腦對所經歷事象識記、保持、再現或再造的過程,而人類記憶則是以個體為基礎群體性識記的結果。當一定數量的個體所產生的共性記憶形成一個群體或多個群體的集體性記憶時,就會產生特定的社會文化功能,并對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傳統節日祭祀作為集體文化記憶再現、傳承和強化、創新的重要載體,也會使群體性的傳統記憶在不同個體的碰撞與交流中得到激活、修復和重造,從而發揮出其他諸多文化樣式難以替代的教化作用。
一、節日祭祀是集體文化記憶的形成與再現的溫床
中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其中許多傳統節日祭祀較好地詮釋傳統節日與集體文化記憶之間的關聯與互動。祭祀是傳統節日中最為常見的事象,在史前文明的人類社會活動中已非常普遍,一般與原始宗教活動關系密切,主要祭祀對象有祭神、祭祖、祭圖騰和祭崇拜物等。祭祀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其內容與儀式在后世社會發展中也經歷了由簡到繁或世俗化的歷程,包括祭祀組織的確定、祭祀前準備、祭祀儀式的主持與祭祀內容呈現、祭祀參與者互動、祭祀評價以及祭祀善后等一系列環節。如孔子所倡導的“禮樂治國”,禮樂發軔并形成于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所實施的制禮作樂形成了特定的文化體系,并在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中得到不斷傳承和發展,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節日祭祀儀禮。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這里的所說的“豊”乃“行禮之器,從豆,象形”。顯然,節日中的祭典在群體性文化中表現出不可取代的地位。節日祭祀中特定的場景與豐富而帶有規范性的禮儀會給予特定人群以情感體驗,并最終會上升為帶有共性特征的文化記憶。
許多群體性的節日祭祀以民眾集體參與為基礎,組織者、主持者、參與者與觀賞者等具有嚴格的身份界定,祭祀則有嚴格的儀式與程序,這就使傳統中的集體文化記憶得到較好的固化、繼承與再現,祭祀中的許多儀禮規范和價值判斷則成為集體記憶的重要信息來源,若干個體經驗只有被集體記憶所選擇、認可并接受時才能得到豐富和發展,否則就會淡化或消失。有研究者把集體記憶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既源于社會也會在社會實踐中拾回和重組;二是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該群體借此得以凝聚及延續;三是記憶具有選擇性和變異性;四是集體記憶依賴媒介、圖像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1]27。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同時,節日祭祀與集體文化記憶的繼承與再現關系非常密切。突出地表現在祭祀活動的豐富性和歷時性有利于積淀相應的集體文化記憶。祭祀一般基于某個特定群體對特定對象的共同信仰,參與祭祀的群體可以是一個國家、民族、氏族,也可以是某個特定區域、村落、家族或家庭,祭祀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禮記·祭法》中記載:“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祭祀一般依托于傳統節日進行,有時某些特定的祭祀也會形成特定的節日。不同民族或地區的祭祀活動重要性、重復性和頻發性,使其對特定群體的集體文化記憶必然產生影響。盡管學術界對祭祀的起源與功能說法不一,如有的認為祭祀源于娛神,有的認為源于對神的恐懼,有的認為源于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有的認為是為了消除災禍,等等。但各種說法之間卻存在一個共識,即認為大多數群體參與的祭祀一般都具有神圣性,不僅存在諸多約定俗成的禁忌,而且對相應的群體具有行為上的約束力。《禮記·郊特牲》中解釋祭祀目的時提出:“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禮記·祭統》對其作用還作出更為具體的闡釋:“夫祭有十倫焉: 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考古及大量文獻表明,群體性祭祀在史前文明時期業已形成,在后世得到充分發育和不斷豐富,社會生產生活中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各種群體性節日祭祀,不僅表現出明顯的社會組織功能和文化教化作用,而且也成為孵育集體文化記憶的母胎和溫床。
祭祀包括個體祭祀和群體祭祀兩類。在形成集體文化記憶的過程中群體祭祀是主體,個體祭祀也具有重要的輔助性作用。如個體的家庭節日祭祖先,可以看作是群體性祭祖的亞態或層級性強化。群體祭祀包括家庭祭祀、家族祭祀、村落或社區祭祀以及更大范圍的國家公祭等。以許多民族的節日祭祖為例,其意義遠不是簡單地對祖先的緬懷與崇敬,而是借助于與祖先的關系,營造出一個強大的關涉群體信仰和文化構建的情感語境。在這個群體參與的儀式中,一方面具有相對固定的神圣祭祀儀式,如祭祖場所、祭祀器物、祭文祝告、祭者職責、祭祖規則、祭禮程序等,據此使傳統儀禮文化得以延續;另一方面祭祖中還會通過神話、祭辭等傳統文化載體使傳統記憶得以重復與規范,如阿昌族祭祀中演述的創世史詩《阿帕麻與遮米麻》、瑤族布努支系的史詩《密洛陀》、壯族的經詩《布洛陀》、畬族的古歌《盤王歌》等,這些演唱往往既有關于天地萬物產生的闡釋,也有關于族源、族譜的溯源,在這個特定語境中把祭祀祖神、強化族源、規范行為、教育后人等有機結合起來,這些文化母題會在耳濡目染中代代相傳,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具有明顯特色的群體性自識或共同的文化心理。
傳統中的文化記憶可以抽取出許多文化母題。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節日祭祀的內容與程式雖然是動態的,但對于某些核心文化母題而言則具有穩定性,并以特定文化符號的形式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中。以黃帝祭祀為例,盡管“黃帝”作為特定的名稱并非一個人的專指,而是“黃帝族”所有成員的統稱,但在祭祀中卻將“黃帝”固化為一個具體的文化始祖。文獻記載中,堯舜禹時代、夏代都把黃帝作為祖先祭祀,商、周時期黃帝后裔祭祀黃帝已形成一種傳統,戰國、秦代除了把黃帝作為祖先祭祀外,還將他作為天神祭祀,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出現了郊祭時設黃帝神位的祭祀,隋唐時黃帝祭祀進一步制度化,宋元時期除沿襲了郊祭時陪祭黃帝的傳統外,出現黃帝陵廟的祭祀,明清時將黃帝陵祭祀列為國家公祭大典,新中國成立后在不同地區公祭黃帝陵的大典也多有發生。這些情況說明,黃帝祭祀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祭祀文化的重要傳統,其中也弘揚了家國同一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傳統文化記憶。祭祖有時也成為“尋根”符號,以山西洪洞縣大槐樹祭祖為例,自1991年起,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日這里都會舉行“中元節祭祖大典”,起因雖源于明朝洪武至永樂年間的官方移民大遷徙,但六百多年來到大槐樹回鄉祭祖的移民后裔絡繹不絕,演繹著執著的尋根夢,其實質與原始社會的氏族時期特別是后來農耕時期的祭祖文化記憶一脈相承。在人們思維中“祖先”“故土”等已成為特定的記憶符號,如在苗族、彝族、納西族眾多民族中至今的喪葬中還盛行著人死后靈魂要回到祖先故地的儀式,有的還要講唱非常細致的“指路經”。這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化記憶更強化了人們的“光宗耀祖”“落葉歸根”等祖先崇拜意識。由此可見,節日祭祀所傳遞的文化母題會在反復呈現中最終固化為集體記憶的穩定文化符號。
祭祀儀式形成的集體記憶對民眾規則意識具有明顯的模塑作用。傳統節日祭祀以其歷史的久遠、眾人參與的共時性和儀禮的規范性,形成了參與者可以心感體受的特殊文化空間,在構建集體文化認同的同時,也強化著相應的文化記憶和規則意識。史前文明時期,人類為了群體生存的需要,祭祀對象是超自然超自我的神靈,在祭神面前只有集體而淡化個體的存在,個體利益包括生命都完全服從于以巫師、祭師為代表的神的意志,這種生存規則也成為具有生存使命感的集體記憶,也是祭祀一定程度上帶有宗教色彩的神圣性的原因。這些規則在祭祀儀式的世代相傳中不斷豐富,形成眾人記憶和現實生活中的教科書。以節日祭祖為例,吉林省九臺市石姓滿族設竿祭祖時,有嚴格的祭虎頭、神鷹程序[2]123-126。吉林省舒蘭市白旗鎮郎姓祭祖神譜時要求,點香懸供,按輩份列行,依次行三拜九叩禮[3]534。黑龍江省東北部的赫哲族九月九日祭祖,馬爾托領著大伙殺一百頭牛、一百頭豬、一百頭羊,煮熟后方能祭神祭祖[4]44-45。內蒙古東北部鄂倫春族在舉行氏族祭祀祖先神“阿嬌魯博如坎”時,由氏族長把族譜打開,念各氏族祖先的名字,參加祭祀的氏族成員都要跪下恭聽[5]226-227。廣西融水縣滾貝鄉苗族祭祖時則要三更蒸糯飯,四更裝好擔,五更祭祖上,六更辭故鄉[6]88,等等。這些情形說明,祭祖不僅是早期文化記憶的重要構成,也是人生觀念的來源,“對祖靈的信仰以及對祖靈的祭祀,構成一種宗教作用場,人們在此氛圍中受到觀念的熏陶和強化”[7]140。通過追溯祖先業績和履行嚴格的儀式,引發每一個祭祀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激發祭祀者在群體中的責任感,并不斷強化著懷念祖先、不忘本原、恪守倫理、尊重規則、履行孝道、敢于擔當、家國并重、維護榮譽等文化記憶。這些集體文化記憶都在當今許多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節日祭祀對傳統集體文化記憶具有修復與重塑功能
集體文化記憶并非一成不變的文化現象,它在再現與傳承中既可以個體與群體之間相互影響,也可以表現出特定語境下的自我修復與重塑。筆者在2015年參加貴州省紫云縣麻山苗族的祭祀祖先亞魯王祭典時,遇到這樣一個情形,祭祀中有一個砍馬儀式,幾個手舉大刀的操刀手要一次次砍向祭場里奔跑的“神馬”,直到馬鮮血流盡倒地為止,最后砍下馬頭獻于祖先亞魯王的靈位前。當詢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如何看待“殺馬”時,她馬上糾正了我的說法,祭神的馬不能說“殺”,要說“砍”,還進一步解釋說“殺的牲畜人可以吃”,“只有砍死的馬才能獻給英雄”,如果把這些不能走樣的語言表達與歌師嚴格按師承誦唱的送葬經詩、不同村落參祭者規范的舞蹈結合起來,不難發現,這類祭祀情形在口耳相傳或耳聞目睹中會逐漸形成民眾對集體文化記憶曲解后的自覺修復。同樣,不同村寨的參祭者高舉不同旌旗,穿戴不同的服飾,表示他們是亞魯王不同支系的后代;不同的舞蹈與兵器則模擬古代爭戰的不同情境,似乎都在努力實現著對傳統記憶的修復。同時也會發現,無論是服飾還是道具,都融入了現代制作材料,并且具有刪繁就簡的當代表演特征,反映出新的社會背景下,對歷史記憶修復中的重塑。由此可見,許多文化母題作為記憶中特定的表意符號,既可以表現為與記憶性質相關的時間維度上直線流傳的一維性,也可以表現出空間維度的可重復性和逆向流動性。這種可重復性和逆向流動性會造成當下文化表述對以往文化記憶的解構和再呈現,其結果是造成當今節日活動對以往集體文化記憶的修復與重塑,其中影響集體文化記憶修復與重塑的動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順勢原則。順勢主要表現為文化記憶的與時俱進。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認為,人們對于過去發生的感興趣的事件,只有從集體記憶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回,而當集體記憶框架變化時,相應的記憶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變化的趨勢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古今結合的與時共進。“記憶的集體框架也不是依循個體記憶的簡單加總原則而建構起來的;它們不是一個空洞的形式,由來自別處的記憶填充進去。相反,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以用以重建關于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8]71任何一種記憶的傳承都不是原有歷史記憶的簡單移植,而是以當下特定語境下對以往集體記憶的再次感知、判斷,并在得到情感認同之后實現新的認知與接受。在傳統節日祭祀中,將場景的神圣性和虔誠的情感體驗融為一體,一方面使人可以周期性地共同回憶家族、民族或國家的歷史,重溫并傳承著古老文明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也會引導自己通過現實體驗和運用知識素養去重新理解并充實傳統記憶。從祭祀的對象看,不僅三皇五帝這些被中華民族公認的文化祖先是集中了無數優秀歷史人物事跡而形成的“箭垛式”現象,而且一些區域性的“小人物”也可以在長期的祭祀中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神”。無論是祭祀中的祭神還是祭祖,傳導的往往是積極向上的共性認識,特別是許多祭祀把那些對民族或國家有貢獻的人和為人類做善事有貢獻的人尊奉為“神”,借此得以精神鼓舞。這類情況在傳統節日中非常普遍,如在沿海地區廣泛流傳的媽祖節,將為人除害的普通女子敬為護佑出海平安的女神;白族的一些村落將歷史上功澤后世的英雄尊為本主在節日時祭祀。再如被多個民族和地區祭祀的屈原、岳飛、關羽等,都倡導了一種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被祭祀的對象作為特定的文化符號不僅具有便于記憶與傳播的特點,還有利于強化民族起源的群體認知和增強民族自豪感。這些優秀文化記憶的生成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相互影響與作用的結果,也是借助于特定的民俗活動特別是傳統節日與時俱進的產物。因此,“社會在其所有重要的回憶中,不僅包含著它所經歷的各個時期,而且包含著一種對其思想的反思。過去的事實可引以為鑒,已經作古的人也會具有激勵或警示世人的作用,所以,我們所謂的記憶框架同時也是一個集觀念和評判于一體的結合物”[8] 293-294。節日祭祀實踐也表明,只有那些適應了時代發展和當下社會群體需求的節日文化,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二是趨利原則。集體文化記憶的形成還源于人類自身的精神需求。美國行為學派代表人物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有五個層次,即基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事實上,人的生存中產生的眾多需要中,一旦滿足基本生存需要,更為關注的問題就是被周圍社會的接受,使自己融入社會關系之中,在社會活動的參與中刷出自己的存在感。這樣,在傳統節日中的祭祀就有了更重要的文化功利作用,特別是祭祖儀禮不僅喚醒人們對祖先的敬仰與崇拜,在強化人生歸屬感的同時成為一種積極的人生激勵,而且會引發個人對自我的定位與思考,將個人自覺融入群體之中。“對共同始祖的信仰,使群體成員之間產生了一種基于共同血緣關系上的親和力,以及對所屬群體的自豪感、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造成群體內部的凝聚力。這一信仰觀念及行為的周期性鞏固、強化,又使凝聚力不斷得以維系、加強,從而有利于群體的完整與和諧統一。”[9]178
三是自適原則。任何事物包括精神產品都毫不例外地是矛盾統一體。無論是節日祭祀的主體,還是祭祀過程的具體內容與環節,都處于動態發展的進程中,其中的“變”與“不變”都會以自身的適應性為原則,記憶的存活也必須以歷史經驗和現實基礎為依據,其變化主要是根據社會形態和周圍環境的變化,通過自我調適,對固有文化表述體系進行修復和改造。傳統節日集體記憶的修復與重塑還依賴與之相適應的民間生態,即生態民俗。民俗不僅有約定俗成的性質,而且大量的節俗儀禮特別是節日祭禮有利于民眾在長期參與中形成具有穩定性的心理體驗和程式化記憶。這些體驗和記憶雖然有時表現為一些個體行為,但無數個體卻帶有高度的祭祀儀式和祭祀內容的情感認同和行為規則,并且在每次類似的祭祀中人們會使用業已形成的文化記憶對祭祀本身和祭祀中某些個體的行為作出評價,這樣就在祭祀表演者、一般參與者和觀賞者之間建構了一個重拾、修復與重塑集體記憶的橋梁。雖然每次祭祀可能在某些細節上具有靈活性和不規范性,甚至難以表現出明顯的價值評判,但因為人們對祭祀的多次感受而融會于心,并不會從本質上解構集體文化記憶的經典性和體系性。
三、集體文化記憶在節日祭祀中的理性升華與價值實現
傳統節日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和增強民眾親和力的生動文化形態,更重要的是,傳統節日中的許多文化主題或母題都與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在反映集體文化記憶心理認同的同時,在凝聚人心、培育人文精神和增強自我教育等方面發揮著其他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力倡導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當今社會,關注傳統節日中集體文化記憶的創新與傳播就顯得尤為重要。
集體文化記憶的傳播是記憶重塑與創新的結合體。任何傳統文化記憶及其再現的文化精神都不是對以往事件的簡單復制與重復。關于集體文化記憶的創新,我們可以用一個金字塔式結構來描述,從族體文化而言,無論是早期的氏族集體文化記憶、還是由氏族結合而成的部落文化記憶,抑或是后來更高意義上的各民族乃至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每個特定時期都可能產生不同范圍的“文化傳播圈”,這種情況也可以從當今作為個體的人的歸屬感得到證明,如每一個人首先屬于一個家庭,而家庭會屬于一個特定的村寨,村寨則會屬于固定的鄉鎮(社區),鄉鎮之上又有區縣,區縣則有特定管轄的省市。恩格斯所說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明確提出了人本身社會歸屬感的復雜性。人的歸屬感的復雜性也就形成了人的文化記憶中價值判斷的多層次性,如關于個人價值與家庭榮譽、國家榮譽的關系,只有審時度勢融入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才會真正具有時代意義。
集體文化記憶的價值實現主要表現在再傳播與持續傳播這個重要環節,任何一次新的祭祖儀式都可以作為集體記憶的傳播的起點。“在中國社會從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官方舉辦的公祭活動正逐步地從傳統的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典禮,轉變成為以服務社會為主旨的現代化節日,擔負著促進地方文化建設、培養當代市民精神、構建城市人文空間的重要功能。”[10]在集體文化記憶的重塑與創新中,我們不能忽視不同群體記憶之間的差異性。以節日祭祖為例,不同地區或民族祭祖會存在差異性,即使同一個民族的不同支系也可能有所區別,如海南陵水縣苗族把盤皇視為祖先,湖南瀘溪縣苗族認為祖先是帶有犬形象的盤瓠,湘西苗族認為祖先是“剖尤”,黔東南苗族的祖先是“榜香尤”,云貴川西部苗族稱“蚩尤”,四川鹽邊縣苗族認為祖先是伏羲兄妹,湖南湘西鳳凰縣苗族認為祖先是儺公儺母,而貴州紫云縣麻山一帶苗族則認為祖先是“亞魯王”。廣而言之,其他民族亦然,無論是壯族三月三日祭祀始祖布洛陀、侗族年節祭始祖薩歲、畬族祭祖先盤王,還是中華多民族普遍盛行的炎黃堯舜禹祭祀等,都在祭祖的外在形式下蘊含豐富的文化共性和民族情感的相通性。不僅伏羲、女媧、三皇五帝被許多民族奉為文化祖先,而且許多歷史人物都在不同民族祭祀中得到尊崇,集體文化記憶應該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存異求同”實現創新,并在“各美其美,成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框架下,積極弘揚中華民族各族人民密不可分的手足之情和團結向上的文化傳統。
[1]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3]富育光,王宏剛.滿族薩滿.關志遠、關柏榮訪問記[C]//呂大吉,何耀華,總主編.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鄂倫春族卷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4]馬爾托莫日根[Z]//王士媛.黑龍江民間文學(第20輯) .哈爾濱 :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黑龍江分會內部編印, 1981.
[5]趙復興.鄂倫春族游獵文化[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6]楊達香.當逗率眾西遷[C]//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1.
[7]金澤.中國民間信仰[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楊利慧.女媧的神話與信仰[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0]王霄冰.公祭節日與當代城市人文空間的構建[J].文化遺產,2016(1).
【責任編輯:郭德民】
2017-03-16
王憲昭(1966—),男,山東冠縣人,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神話學研究。
I207.73
A
1672-3600(2017)07-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