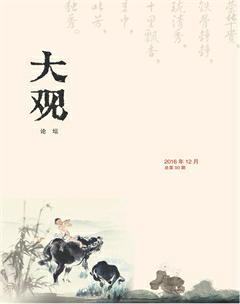抗戰時期圍繞《四庫全書》閣書的文化掠奪戰
[此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2014年度培育項目“民族國家認同與文化權力之爭——中日戰爭期間的《四庫》藏庋與傳播研究”成果。]
摘要:抗戰期間文淵、文津、文溯、文瀾閣書皆受到時事影響,本文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相關資料初步分析了在此期間由于處于戰爭狀態,這些國寶文獻所面臨的交織著各方勢力錯綜復雜斗爭的文化掠奪與反掠奪戰爭。
關鍵詞: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第二歷史檔案館
一、問題史之回顧
《四庫全書》編成之初,分繕寫七部,分藏各地;但由于各種原因,進入二十世紀后,惟余文淵、文津、文瀾、文溯四閣,即所謂之“三部半”《四庫全書》。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說:“中國書籍對于東洋文物而言,不用說,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而其邦變亂無常,災厄波及文物如此。其古籍之殘缺,往往我邦存而傳之。”(1901)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止,日本侵華期間,一方面謀求領土之侵占,財富之掠奪,另一方面還謀求文化典籍尤其是以《四庫全書》為代表之掠奪。敵人直言,對于中國一時一地之破壞,將在極短之時間內得以恢復,而對文化之打擊和掠奪,則中國國脈之根本將為之動搖。由是而有我國政商學工農各界一大批忠勇智慧、堅毅勇銳之士對《四庫全書》為代表的各種寶貴文獻的拳拳愛護、全力襄助之史詩般之壯舉。學者鄭振鐸說:“民族文獻,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睹其淪失,而不為一援手,后人其將如何怨悵乎?”(1940)今天我們來研究這段文獻保護及其相關歷史,對于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反對霸權主義等依然有著顯著而直接的意義。為便于考察,對這一問題之來龍去脈,分5個時段進行觀察:
(一)局部抗戰時期(1931-1937),代表性論著有清茅《古物南遷中四庫全書之保存問題》(1933),村田治郎《熱河文津閣小記》(1935),張崟《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史稿》(1936)。楊家駱說:“這十部現只四庫全書……正本四部尚存人間,其余半數,都犧牲在國際侵略戰和內戰中。”,七閣之中,文淵閣“現在這個建筑仍然存在,至于書則于1933年后因預避日本的掠劫,遷往上海,輾轉到了重慶附近一個鄉村——一品場,想不久會遷回北平或遷來南京的。”此一時段之閣書庋藏研究,文瀾閣多為其抄配史實回憶材料或存書現狀研究情況;北方地區的文溯閣、文淵閣等因局部抗戰之發生,或謀影印,或已南移,材料證明,此時之北方閣書已成為各方關注的文化焦點。
(二)全面抗戰時期(1937-1945),有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1937)、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1937),近藤春雄《四庫全書編纂的動機和目的》(1937),布村一男《四庫全書和俄國》(1939),市村瓚次郎《關于四庫全書與文淵閣》(1943),福地征太郎《四庫全書與文瀾閣部》(1943),祝文白《兩次查看內運文瀾閣四庫全書記》(1944)等論著。此時段對閣書之研究,由于戰火頻燃,國土分裂,偽滿、汪偽、淪陷區以及大后方的各有關文化團體,單位或學者,都或多或少被裹進這一歷史大事件,或力促保護,或加緊研究,或謀求選印,對閣書之命運施加了各種方向不同的影響。鄭振鐸說:“我輩對于民族文獻,古書珍籍,視同性命,萬分愛護,凡力之所及,若果有關系重要之典籍圖冊,決不任其外流”,“若我輩不極力設法挽救,則江南文化,自我而盡,實對不住國家民族也”,“將來若研究本國古代文化而須赴外國留學,實我國民族百世難滌之恥也。”(1940)此語可謂當時致力保護閣書之國人心態之集中呈現。
(三)抗戰結束后至新中國成立前(1946-1949)。代表性論著有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1946),徐伯璞《文瀾閣四庫全書歸閣散記》(1946),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1947),洪煥椿《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之過去與現狀》(1948)。抗戰勝利后,文瀾閣東歸故地,文津、文溯、文淵三閣回歸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各接收員、學者通過視察、指導等表示對閣書命運之關切;其中,東北地區由于接受日寇就地投降,使得文津、文溯二閣書留在東北;由于國民黨政權危機,文淵閣書不得不滯留南京,嗣后不久就移至臺灣。
(四)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1950-1978)。代表性論著有董作賓《從共區搶救出來的四庫全書》(1953),王樹楷《七閣四庫全書之存毀及其行世印本》(1959),徐文珊《建議政府向日本索回四庫全書》(1969)。由于國民黨運文淵閣至臺,加劇閣、書分離;而后由于兩岸長期敵對關系,對閣書的研究表現出一定的對立與封閉傾向。
(五)新時期迄今(1979-2015)。代表性論著有蔣復璁《四庫全書的性質與編纂及影印的經過》(1980),高橋克三《憶四庫全書與恭仁山莊文庫》(1980),孟國祥《調查和追償日本劫奪我國文物工作述要》(1992),陳訓慈《運書日記》(2013),楊斌《竺可楨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遷移》(2013),《抗戰時期浙江省文瀾閣四庫全書內遷史料》(上,下,2015),趙曉強,鐘海珍《貴陽地母洞與<四庫全書>》(2015);境外主要研究者主要有:Carrington Goodrich,松本剛,吉開將人等。綜觀此段研究,利用檔案、日記、回憶錄的傾向日益突出,由于和平與建設成為時代精神,對閣書研究的意識形態對立有弱化傾向;加之相關檔案披露日益廣泛,挖掘日益深入,對閣書在戰時的掠奪與反掠奪斗爭的記錄與分析較以往各時期更加深刻而全面。
二、圍繞《四庫》閣書的各方力量博弈
由于四庫閣書在抗日戰爭時期已僅剩三部半,加之目前國內披露出來的主要是第二歷史檔案館、貴州省圖書館的相關業務檔案,筆者擬圍繞這些資料為中心,并部分結合其他材料,對文溯、文淵、文津、文瀾幾部閣書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各方博弈力量略作探討。
(一)圍繞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各方角力
1909年8月21日,清學部奏請“籌建京師圖書館,請賞給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①,獲得允準,但始終未曾辦理。辛亥革命后,1913年6月北京教育部致函熱河都統準備往取《四庫全書》;1915年10月7日,文津閣《四庫全書》最終得以移交京師圖書館;1920年,陳垣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對收藏在安定門內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進行統計;1928年遷館址于中南海居仁堂,并將京師圖書館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1年北海旁邊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舍建成,文津閣《四庫全書》隨之遷入。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后,文溯閣《四庫全書》由偽滿國立圖書館接管,經檢查,閣書尚有個別闕卷現象,該館于1934年派人赴北平照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補鈔,計補全《揮塵錄》等三種,共12冊。
根據相關資料得知,1943年9月20日,袁同禮《關于抗戰以來國立北平圖書館遭敵劫掠與破壞損失情形呈》:“職館所藏圖書,如……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皆為國家瑰寶,非僅能以貨幣價格估計……北平全部館舍建筑及設備,以及留在北平未及運出之藏書,于二十六年七月底北平失守后,悉數淪陷。”②但盡管如此,文津閣四庫全書還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開放,當時還有記者前往探訪、拍攝并有相關報道,為后方讀者了解文津閣四庫全書現狀傳遞了消息,這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淪陷時期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保存比我們預想的好,或許是因為敵我雙方都認識到四庫全書是中華文化瑰寶,值得珍視,不容糟蹋以及毀棄。
文津閣本在歷史上起到了文獻補輯作用。迄今,文津閣本仍是七部閣書中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且保管最為完整的唯一的一部,為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
(二)圍繞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爭奪
辛亥以后,文淵閣四庫全書送故宮博物院保管,1933年,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華北危急,國民政府將此書送到上海存儲在天主堂街的中央銀行內,四年后,抗日戰爭爆發,又由上海輾轉運到重慶,胡昌健《故宮南遷文物在渝遺址尋訪記》③有相關討論,值得參閱。
1930年6月2日頒布之《古物保存法》規定:“古物除私有者外,應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責成保存處所保存之”④、“私有古物,不得移轉于外人,違者沒收其古物,不能沒收者追繳其價額”。⑤1930年7月3日,宋子文《財政部核定古籍出國范圍呈并行政院訓令》:“職部以為……此后報運書籍,除石印影印鉛印各書準予輸運外,其中國木刻精印之線裝本在規定范圍內者,一概禁止運出國境,方為保存國粹根本辦法,海關執行,亦較便利⑥”。1930年7月23日,教育部呈行政院《鑒定禁運古籍須知》稱“禁止運出國外之古籍,暫定為次列各種……永樂大典及四庫全書⑦。”根據以上相關法規,則《四庫全書》閣書,皆為禁止外運之古物,有此法律上之保證,則對《四庫全書》之保護更加順理成章。
根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工作概況并理事名單》(1928年10月-1936年12月),1929年以后,“按照規定程序,積極整理,設立專庫,分別庋藏,益以資政院、方略館、清史館之圖籍,分為善本書庫,殿本書庫,及經史子集叢五書庫。……自十八年北平警備司令部將所派士兵撤去后,院內警衛即由公安局保安隊及內六區巡警共同擔任⑧。”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歷變八年簡略報告》(1945年6月):“七七事變發生時,馬院長衡適因公在京,迭經請示中樞,命總務處處長張庭濟率同原有人員負責維持。……當察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率二十九軍撤退之后,即由公安局長潘毓桂組織所謂‘四機關警備事宜辦事處,以已故古物陳列所主任錢桐為主任(四機關指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國立北平圖書館、古物陳列所及歷史博物館)。”
1938年8月6日,夏頌明《抗戰一年來圖書館的損失》:“浙江省立圖書館和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四庫全書(此指文淵閣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聶注)均已運出。”(據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國防部史政局及戰編纂委員會檔案)⑨
1949年2月19日,臨近解放前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報告將善本書運臺經過致教育部呈:“遵即密與國立中央博物院暨故宮博物院等機關,取得聯系派干員分批移送,第一第二兩批,系善本圖書館及金石拓片重要文件等業經先后運抵臺中,存于臺中糖廠倉庫。”⑩
綜上幾則材料可知,文淵閣書,在淪陷前就已南遷上海后至重慶;北平之故宮博物院處于“維持”狀態;臨近新中國成立,該書又在杭立武、蔣復璁等人安排下送往臺灣,成為寶島臺灣的又一文化至寶。
(三)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流離及回歸
文瀾閣《四庫全書》在七部閣書中的命運是最曲折的,在太平天國時期就遭受到戰亂之干擾破壞,幸得有識之士發心起愿以巨大之人力財力從各方抄補整齊,到抗戰時期,為避免陷入敵手,不得不離開杭州,千里西進,從杭州、湖南、貴州最后進入重慶青木關丁家灣9號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在地,直到抗戰勝利,然后才又返回杭州。
此書保管員毛春翔撰《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1937年)8月1日,全館職員在孤山分館點書裝箱,總計閣書140箱,善本書88箱,于4日晨裝船運往富陽漁山……自江邊至石馬村,計程十五華里,雇工挑運,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趙君坤良、坤仲富有資產,待人和善,號召力強,一聲令出,數百挑夫立至,故搬運書箱毫不費力。”
內政部1940年7月向國民黨第七次全會提出的工作報告《關于戰區內古物文獻移轉情況的報告》:“浙江范氏天一閣藏書、文瀾閣四庫全書……等均已運藏安全地點……”
浙江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蔣復璁、顧樹森、陳訓慈呈教育部報告接運文瀾閣四庫全書經過情形呈(1946年8月23日):“……督導秘書毛春翔在青木關謹慎守護,并于六七月間全部曝曬,隨時有報告至會。及八月間抗戰勝利,本會旋即開會商討運輸辦法,……承介紹渝蓉廣商車總隊租三噸卡車六輛,即將情形呈報,并附呈概算,當蒙批準,并派定社會教育司徐科長伯璞領隊,會同本會秘書兼管理員毛春翔及部中職員黃閱等共六人押運,……自五月十一日自渝啟程,……于(七月)六日下午止,《全書》安全抵運杭垣,自城站裝赴外西湖浙江省立正圖書館卸放。”
關于四庫文瀾閣四庫全書保護,作出貢獻之人甚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貴州省圖書館藏業務檔案中都有較多相關資料,可供查閱,筆者拙文《蔣復璁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檔案節鈔——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文瀾閣<四庫全書>避寇入黔秘藏相關檔案摘記》進一步披露有部分史料,此不贅述。本文末附有貴陽地母洞二張,可見其時保管此書情景之萬一。
(四)圍繞文溯閣《四庫全書》的相關斗爭
1925年,沈陽成立了“文溯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委員會陷于停頓狀態,但其秘書處認為《四庫全書》的保護問題“關系綦重,須有負責人員常駐管理,方免發生意外”,次年,奉天省政府委派“秦化田暫行管理”,秦化田、關景勛作為文溯閣保管員,開始點查《四庫全書》。此間,日偽曾動議將《四庫全書》運往日本,后因顧及民眾情緒而被擱置。
1935年日軍派人清點文溯閣《四庫全書》后,以文溯閣多年失修及保護閣內藏書為由,在文溯閣前西南處修建了一座樣式非古非洋的鋼筋水泥結構,并在門窗包以鐵皮的二層樓書庫,庫內置鋼銅制組合書架,1937年將文溯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全部移入新庫。1945年日本投降,《四庫全書》為蘇軍接收。抗戰結束后,1946年4月,當時的東北教育接收輔導委員會委員金毓黼、周之風等人接收了偽國立奉天圖書館以及文溯閣《四庫全書》。
根據史料發現,1933年,即偽滿洲國大同二年偽國文教部總長鄭孝胥《文教部訓令第103號》:“奉天文溯閣所藏四庫全書為國家重要典籍,應加意保護,以免疏虞,近因故宮后面倉庫失火,與文瀾閣近在咫尺,殊堪隱慮,合行令仰該省長妥籌四庫全書防火辦法,并將辦理情形具報。切切,此令!”
《國立沈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工作及復原概況(1947年8-10月)》:“自‘八一五光復后,長春二館(國立中央博物館長春分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長春分館——聶注)迭為蘇聯軍、共產軍暴民所劫掠,故藏品悉蕩然無存,沈陽館因中國人員較多,力加保護,損失較小。……圖書館因設于舊城內,無軍隊之占據,且因典守人盡責尚稱完整,損失無幾。……圖書館藏書數目統計表:一、善本書。甲、宋元明善本,1450冊;乙、文溯閣四庫全書,36313冊。……本館原藏圖書館皆為漢文圖籍,偽滿時代,不甚公開……文溯閣四庫全書……抄寫校勘,皆極精到,以視江南三閣稍不同。今江南三閣,僅余文淵(當為文瀾——聶注),其巍然現存于華北者,惟此文溯與文津兩閣而已。今者文溯閣四庫全書,雖幾易滄桑,猶完整無闕,不特為本會之厚幸,亦東北之魯殿靈光也。”
在金毓黼主管四庫全書相關事務期間,對文溯閣四庫全進行了徹底檢查、建新書庫等工作,如金氏自稱:“于康德二年,請準文教部,批準巨款,重建二層樓房之新書庫于院之西南,內部結構皆依照現代之藏書庫,門窗悉包鐵葉,以期萬全,外部則飛閣雕墻,仍仿舊制,已仿舊制,已于四年季夏,將全書移入,意必為關心國寶之士所贊許也。”
盡管如此,但偽滿洲國是傀儡政權,且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產物,因此其文化措施的政治合法性常被人詬病,筆者在民國期刊數據庫中發現有人以《我們文化上的喪失——在敵人手里的四庫全書》為題報道了文溯閣的相關信息,并配發多幅圖片,盡管客觀上為讀者提供了文溯閣在當時的收藏情況,但是其充滿戰爭年代固有之飽含對立情緒的標題,無不讓讀者有更大的觸動——務必要收復失地,務必要收回瑰寶!
無獨有偶,在民國期刊數據庫中還發現一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夫婦于1946年底在沈陽視察文溯閣四庫全書后的照片(見文末附),這可能是唯一發現的領導人及其夫人同時關注、觀覽四庫全書的照片,彌足珍貴,亦增意義!
三、抗戰期間圍繞閣書之文化掠奪給今人之啟示
(一)對于文獻之保護宜未雨綢繆,確保萬無一失
稍有常識者皆應知道文獻為文化信息傳承之最重要載體,故必須代代相承,方能實現守先待后,不負先賢為萬世開太平,為往圣繼絕學之良苦用心與遠大抱負!《四庫全書》是中國封建時代鼎盛時期,傳統文化集大成的國家工程,代表了中華文化海涵負的大國氣象,盡管其中不無微瑕,但此書在手,對于國族觀念認同,對于民族文化傳承,對于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之打造,功莫大焉!
但是無論是戰時還是和平時期,總有部分人士對于此書之重要性,有相當多人還認識不到位,甚至鬧出令人哭笑不得的尷尬,如陳訓慈《運書日記》(1938年2月15日)所記:“據林秘書談,二月一日(浙江)省府會議議及《四庫》書遷運費事,因適在教部來電主運黔之后,黃主席頗起反感。討論之初,即述及部電,謂土地人民危險,何靳靳于一書,似可索性不動。”按,此時之浙江省主席為黃紹竑,字季寬,廣西容縣人,與李宗仁、白崇禧同學,桂系三巨頭之一,以其一省之最高長官的地位居然不知曉《四庫全書》的重要性,反而對教育部發出“何靳靳于一書”的驚詫之論;其對于保存文化態度之消極,“似可索性不動”,令人聞之不免哀其不智,怒其不爭!
相較之下,對于故宮文淵閣藏書,雖關山萬里,多受曲折,但至少是在主政者關注、推動下及時從戰區撤出,未受到炮火侵襲之擾;而對于文溯閣,雖然因其處于日本人控制下,但是事實上主其事者為愛國學者金毓黼,其在職期間積極加以改善收藏條件,為此書避免遭受火災蟲蝕等創造了條件;而文瀾閣在貴陽保存期間,教育部以及浙江大學多次下派人員前往視察,并對防潮、防火等提出改進意見,結合當地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以及工作人員的工作起居條件等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建議和布置,而當時的教育部主要負責人陳立夫等也非常重視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人員提出的增加維護經費、提高待遇等請求并及時解決。
(二)對于文獻之使用于保存、開放與開發應結合
中國是文獻大國,文獻之為用,大矣,多矣!然很多部門守其書,不守其學;愛書之表,不愛書之魂,此種所謂保護,為孤立、消極的保護;未能做到積極,全面的真正的保護,這對文化資源來說也是一種浪費。以文瀾閣《四庫全書》為例,如果不是其他閣書開放允許傳抄,那么文瀾閣書在太平天國戰火之后是根本無法重新抄補配齊的,有這種文化擔當精神的浙江士人值得敬佩;而這份對文獻傳承的責任感也是我國文化之所以經歷千回百轉之磨難而終究屹立不倒的強大精神支柱;無獨有偶,如果不是文淵閣的開放,文溯閣的配置完整也是不可能的,《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復記》曾敘之:“傭二十人補抄,以董眾、譚峻山董其事,盛夏揮汗,浹背沾衣,嚴冬恒寒,爐火無溫,龜手瑟縮,而伏案校錄,未嘗稍輟,僅七十二卷,閱一載而始成。”至今如在眼前,可見文獻保存之不易,處此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之現代,我們一方面感恩前賢的文化苦心,也更應該有此文化自覺,推動四庫全書文化在新技術條件下的開發、拓展、深化、創新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更能理解民國時期的《文淵閣四庫珍本叢刊》等影印工作,因為在當時的戰火紛飛年代中,如果只是孤立的保存而不想法開放復制,開發出更多的文化產品,如一旦原本毀損,至少從內容來說,可能將永難找回這些文獻史料。所以影印原本、選印善本、影印未刊本,都值得點贊,不應有意氣之爭或派別之爭或為出風頭而強人以就我。姑且不論當時戰爭年代,是否有足夠充裕的時間、精力去探究珍稀版本等,但是只要出于公心,都應該支持和肯定這種有利于豐富文化產品,提高文化自信的文化工程。所以,筆者也特別理解當時貴州大學校長上書懇求借文瀾閣《四庫全書》就地抄繕的請求:“今日猶幸文淵之精本及文瀾之全帙,得內移安順、貴陽等地,藏之名山,此在遠省實為千載難逢之盛事。又自軍興以后,秘笈珍本散佚殆盡,對此稀世文物彌增兢兢業業之感”、“為此仰懇鈞座賜頒功令,乘此良機,以文淵為底本,不足則配以文瀾閣本,就近傳抄全帙,留庋貴州,永廣傳布。今國立貴州大學已慶成立,所屬研究機構正當策劃次第完成,倘傳抄竣事,即以之存貯黌舍,任人觀閱,則莘莘學子仰體鈞座右文至意,鉆研探討,感激奮發,蓋可預卜。……倘因此次播遷而使貴州之地得永寶巨帙,誠開亙古未有之紀錄。”
當下對于各種載體、形式翻印、影印乃至原樣制作《四庫全書》的壯舉,或認為勞民傷財,或認為重復勞動,或認為惡意炒作,筆者檢閱相關史料越來越感受到,今日之中國社會固然安定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體領導下致力于中國夢之偉大理想;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問題因素也值得我們警惕,這些因素在某些時候甚至會激活或演化成為對目前存世的各種《四庫全書》存本的重大不利影響,如在此時能多一點文化自覺性,多制一份文獻拷貝,對于因應未來之各種文化危機,未必是杞人憂天之思吧!
(三)對《四庫全書》之類國之瑰寶的庋藏應提高規格
目前而言,對于存世《四庫全書》閣本的庋藏重視力度、宣傳力度都不妨進一步提高規格,原因主要是,只有全民逐漸意識到了以《四庫全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文獻載體之重要性,才能進一步學習通過這些文獻載體所傳承的有益的思想觀念,才能更好地建設今天的社會主義。目前而言,雖然有不少大學(如南京師范大學,蘭州大學,武漢大學)已有以四庫全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碩士點、博士點,也有不少單位構建了四庫全書為重要研究議題的研究中心,但是這些在學術圈內比較熱的事情,對于社會大眾,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普及和宣傳程度。
以貴陽地母洞為例,多年來,學者趙曉強清理了抗戰期間文瀾閣《四庫全書》在貴州地母洞保管、看護的歷史脈絡,值得欽佩;但是截至2016年11月筆者前往地母洞實地考察時,該地仍主要是一塊碑孤立地屹立著,而無配套設施設備,游客或考察者無法在此做深入研究、討論;且沒有任何其他碑記或說明文字,連周圍的百姓都只隱約知道有古書曾放在這里而已,更多的情況則相顧茫然而已。
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學術理論向社會普及的角度,還是從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提高旅游人氣等多種考慮,與文淵閣有關的地母洞等類似遺跡都值得認真提煉,挖掘,開發!所幸趙曉強先生告知筆者,地母洞所在的當地政府正在極力推進地母洞的相關開發,筆者期待開發出來的地母洞能讓人重溫歷史、激活記憶,通過這一遺址的相關展示和項目體驗,如帶給我們更多強勁、持久、深沉、溫暖、大氣的文化感悟和精神動力,那將是《四庫全書》閣書傳播和弘揚文化史上的又一極具意義的嶄新篇章!
附:
抗戰時期存藏文津閣四庫全書之書架書盒均系楠木所制鐫刻說明書
(圖片來自,[民國]蔣漢澄 攝影,據《時報》第三張,NO.531.)
蔣介石夫婦于文溯閣翻閱《四庫》全書后步出時留影(1946年5月下旬)
(圖片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毛春翔等在貴陽地母洞藏庫攝影
(1942年5月10日,圖片來自網絡)
曾保存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地母洞
(圖片來源:2016年11月,貴陽現場拍攝)
【注釋】
①記載一,宣統元年七月大事記[J].東方雜志,第九號.
②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一)[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7:380.
③胡昌健.巴蜀史地與文物研究[M].滄州: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305-316.
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4:609.
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4:610.
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4:611.
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4:612.
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4:599-603.
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一)[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7:368.
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三編(文化)[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9:371.
圖書展望,1949(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五輯第三編文化(文化)[M].南京:鳳凰出版集團,1999:331.
金毓黼.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M].四庫全書要略,中華書局,2014:4249.
金毓黼.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M].北京:中華書局,2014:4256-4257.
作者簡介:聶樹平(1978-),重慶長壽人,重慶工商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講師,主要研究巴渝古代文學與文化以及古典文獻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