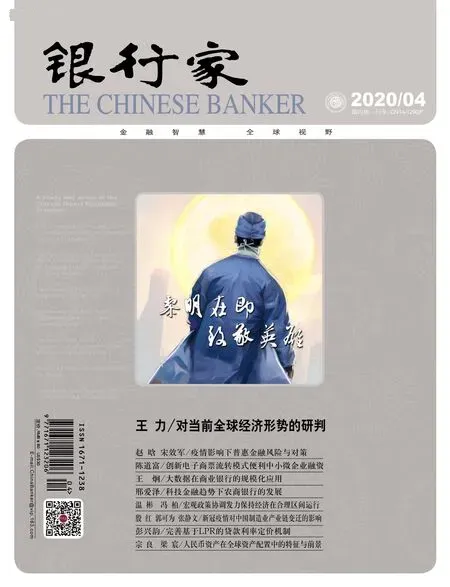父子集(35)
王松奇書法
社會學碎碎念
(一)雜記
“我上節課布置的錄像研究你做了嗎?”
“沒。”
“沒?”
“沒做。”
社會學老教授以一種每位老師看壞學生時獨有的譴責目光看著我,仿佛等我繼續解釋或是道歉。可我沒有,只是坐在那里看著他,沒心沒肺一般。
我不是真沒心沒肺,只是太久沒被老師譴責過了,突然遭遇這出兒,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回應而已。
“你的論文寫得很好。”看我沒有再表示什么,老教授決定以一句迫使我自責的表揚打破沉默。
然而我也沒有自責,只覺得自己通體散發的呆滯似乎令這位老人很尷尬,于是趕緊將對話收尾。
“謝謝,我回去會把錄像研究補上的。”
其實從開學到現在這節社會學課只講了一個概念:成年人在社交中所有的行為特點都是對兒時社交模式的互動。自我社會形象的樹立是對兒時監護者形象的重塑,虔誠投身信仰是對兒時所感知的父愛母愛的追溯,人格中的頻頻不安或過于冷漠來自于兒時父母對自己不安或是冷漠的撫養方式,云云。
是的,教授原話即“所有的行為特點”,非常絕對,不是部分,不是大多,所有。
所有使我們自甘被動的交流對象都是父母的替代品,所有使我們愈發主動的交流對象都是子女的替代品,人生只是一場對家庭關系的無盡復制,他如是說。
聽來極端,套到實際現象上發現道理還是有幾分的,比如為何同齡美國人看待朋友往往輕于中國人看待朋友?以前文邏輯,獨生子女一代的我們把無血緣關系的同齡伙伴視作了兄弟姊妹的替代品,才會形成朋友間相互的高度依賴關系。
當然,并非所有朋友都會變成手足替代品。每個人的朋友一般分三層,最外層是見面皮笑肉不笑的表面朋友、交往意義僅在于玩耍的酒肉朋友,與尚未深層溝通的其余熟人;中間層則屬于有過深入交流并相互較為理解的聊友,以及曾肩并肩共同經歷過低谷或變故的革命友誼;至于最近一層,不會超過三個人。因為這一層的朋友看過、接受并支持一個精神與思想上一絲不掛、毫無保留的你,這樣的朋友才是兄弟姊妹的替代品。或許你與他們不常聯系,但當生活狀態孤立無援、精神狀態陷入不穩定時,只有他們會對你伸出援手。
不巧的是,大概也因我們過于輕易將初相識的陌生人視為骨肉,閨蜜和兄弟成了日益廉價的詞匯,人們也愈發劃分不清這三層朋友的界限。有些人看你受傷會心疼,你卻將酒肉朋友與對你吹牛拍馬的抱腿俠視作至親,這種情況在我身邊似乎一日比一日更常見了。
我在羅村的一個小兄弟是經濟系的一朵花,不僅成績優異,種種學術概念也倒背如流,很得教授青睞。順理成章,就有很多人來向他請教學術問題,大多是出于考試時想多拿點分的心態,但他也一一解答,從不抱怨。直到后來一天,他突然和我說,現在的人真虛偽。我說怎么了,他說他以為那幾個人認真和他交朋友,不料都是趁考前來找他講題、考完試就高冷走開的貨色。我聽完也覺心寒,只得拍拍他肩膀,勸他理性接受自己作為學霸的社會角色,雖然這種遭遇其實本應在預料之中。
另一種劃分不清朋友界限的方式,來自兒時沒有從家庭關系里得到充分愛護、或者剛剛脫離親密家庭關系轉去陌生環境生存的成年人。這兩個人群往往對無血緣伙伴產生更大的依賴傾向,也更粘人一些。然而粘人是頗有貶義的,也確實令人厭煩;除非兩個人都缺愛,互粘,皆大歡喜,否則指向有誤的依賴很容易使另一方產生對親近本身的恐懼感(Fear ofIntimacy)。
幾年前有個男性朋友,因偶然的原因和我關系相處得不錯后,就開始愈發不計細節地向我親近。漸漸地,我們的關系變成了由他單方面促成的形影不離,甚至到了上廁所也要一起的地步。然而這種距離過近讓我很不舒服,久而久之他也沒有辨別出我的反感,我只好找理由抽身出來、冷處理他,千方百計地一次次拒絕他的社交提議。雖然這樣看來很不地道,但不然自己難受;大概,是我自私成癮。
后來想想,他真的什么也沒做錯,只是當時才來我們學校,心里比較沒底,才對身邊的人產生了自然的依賴欲,僅此而已。
有些人雖然看似孤獨,但每每陷入孤獨其實都會心中暗爽,自得其樂,比如我。有些人雖然看起來心思簡單,不需要太多復雜養分就能活,也從不抱怨生活的寂寞,但一旦脫離人群,就會系統性喪失意義、生理上自我混亂、生活徹底崩潰。
統而言之,老教授認為這一切現象都是一個人對他成長階段中家庭關系的折射,并執意如此認為。以上大概可以conclude我在初接觸社會學這門學科后的一些筆記。
后記
每次當老教授講到這理論時都會一反穩重寡言的形象,語氣變得異常慷慨激昂,眼神堅定不移,讓我又想起《白鯨記》里的Ahab船長。我不禁好奇地想知道,他曾經經歷過什么樣的人生際遇,以至于對于學術與生活的態度如此截然不同呢。
我曾同幾個心理系的朋友就此事交流了一番,他們一致認為這位老人的確很固執,固執于幾十年學術經驗在他心中建構起的那一套雷打不動的理論,固執于老年人通常熱衷于傳授晚輩的所謂智慧。我想,這理論是他不能舍離的信仰與精神寄托,并非理論本身的合理性不能被推翻,而是一旦推翻,老教授的生活也不再有意義,大概也會系統性崩潰了。
再往深了想,大概,人在老去、父母不在后,會把事業的回饋當做父母的替代品吧。
也可能只是我腦洞大開。
2016.10.30
(二)人就是作
羅切斯特二月的夜晚,偶爾也會月明星稀,方才下車后潘俊威調侃說:“石頭,我們去看星星吧。”我說:“沒那個心氣了。”雖然距離上次觀星過了也就一年多。
現在的我認為,帶著對生活的不滿或盲目期待去仰望星空,是一種“一作到底”的行為。作當然本非罪孽,年少不作,枉為少年,但成長即作著作著,就累了。說得冠冕堂皇些,是謂妥協;說得直白明了些,是謂人一大臉皮就厚了,腦子也鈍了。
社會學老教授的招牌理論就是他的Hype r s t r u c t u r e,我不知怎般翻譯最恰當,遂不輕舉妄動。大意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的社交行為都是依照Hyperstructure的:在兩個俱備感情基礎的人之間,離合是一種周期性運動,且該傾向屬于人腦與生俱來的激素周期,而非后天所生。
人基于Hyperstructure的社交行為最早可見于嬰兒對于母親。假定一開始母親是抱著嬰兒的,那抱久了嬰兒自然會厭煩懷抱,遂哭鬧著要去地上自由奔跑、探索世界,于是母親放他下去,任他自己玩;然而歡騰久了嬰兒自己又怕了:我離開我媽媽太久了,這讓人心慌啊,于是又哭鬧著要媽媽抱抱,回到這個運動的起始點,由此循環。這個例子很通俗,卻足矣套到所有成人社交問題上了。
為什么突然說這個,因此理論不僅通用于各種人際瑣事,且很大程度上詮釋了“人就是作”。若可以理性地接受“人就是作”,那大多利益糾紛之外的人際矛盾也迎刃而解了。
記得初二時學校曾請來一位自稱有心理學學位的體育老師,至今難忘他在年級大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講,開場一句話已然煽瞎了我:“不要以為我這個年齡的人不懂你們這個年齡的人。我清楚得很,你們心里只有兩件事:一,我愛的人在哪里?二,我愛的人,他愛不愛我?”此話一落,臺下頃刻掌聲雷動,一眾青春期少男少女紛紛起立叫好,再一看演講臺后,幾位古典學究派、一看面相就知是反早戀的年級主任站得愈發不自然,一臉三觀破滅的驚恐。
多年后想起這件事,不由歸出兩個結論:一,情愛問題對于很多人的困擾在初中時代后不但不會偃息,反而會愈發惡化,宛若腫瘤伴人一生;二,煽動一群初中生其實真的用不到心理學學位。事實上,這篇演講只要換幾個更高明的措辭,把一群成年人煽動到淚流滿面也是易如反掌,沒有自我省過能力的人都是越活越作的,這種作體現在頻頻令旁人感慨“你的腦子呢?”之上。
如何解釋有人愈發心態安定,有人愈發焦躁脆弱?我通過個人愚笨的觀察,認為形成“作”之本質的一大因素即作為一種社會遺傳物的家庭環境更迭,與基因無關,而是通過相似家庭環境的代代傳遞而生。不難理解,成長時的家庭環境對人之影響舉足輕重,依稀記得在先前的社會學筆記里有寫,一個成年人的社交行為大抵是對兒時在家庭里社交習性的復制與花式衍生。換句話講,如果小明爺爺與小明奶奶婚姻不幸福,那小明爸爸會有更大幾率和小明媽媽關系不好,而小明成家后同樣會有更高幾率背離婚姻道德。
當然,話都不是說死的,但成長中的兒童與少年不可能對客觀因素的影響免疫。
所以愈發感到,許多犯罪之人之所以三觀有問題,并非在某一時刻他們就從善病變為惡了,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成長期間所接觸的環境已不可逆地塑造了深植入心的病態三觀。這些病態觀念縱然可在社會準則之下被隱藏,但若偶然雨水充沛,仍難免破土而出。
在所有社會關系里,情愛又恰好是最逃不脫的牢籠。“遇見個好男孩/女孩真難啊”這種感慨我已聽同齡人講到耳朵生繭,這個問題何嘗不是個社會問題。成長中家庭存在矛盾的朋友,他們的hyperstructure作用往往會被夸張地放大或縮減,于是導致他們患得患失、也擅得擅失,最終往往與關系密切的人或重或輕地暴露出交流障礙。我無意從主觀角度對任何身邊人開炮,這個現象有相當的理論支持。
我自己的家庭氛圍一直較為和諧,在少年時代便產生了“家庭幸福理應是民生常態”的錯覺。大了后才發現不是,父母不和諧是這一代年輕人家庭生活的主基調之一,當中不乏諸多家庭支離破碎者。在各種實例中我親眼所見,后者的兩性觀念與社會準則往往有幾分格格不入,而他們的數量意外龐大,以至于已有形成自己的獨立文化的傾向。
以上概括了近期的一些想法。再一次,話都不是說死的,尤其,人的理性是個好東西,可以把成長環境所給予的一些負面作用力踩在腳下,從而維持健康的社交狀態。我寫這么一篇主要也是總結一下本雜亂無章的各種論文讀后感,槍口不對準任何人,自己別迎槍口而上。
科學理論大多都只是參考物,而非自然規律的真實面目。在“人就是作”這個問題上,諸位還是應當培養強大的理智約束力,畢竟人不能一輩子都看著星星掉眼淚,更充分地了解自己和人性特征總體來講是件積極的事兒。
2017.3.7
(三)社交的兩重意義
M u r r a y B o w e n博士在學術論文Chronic Anxiety and Defining a Self里提到一個名為Level of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此詞目前并無標準的中文翻譯,直譯為“分化度”,我將之更通俗地譯為“獨立抗壓性”。顧名思義,獨立抗壓性即一個人獨自消化壓力的能力。人最尋常的解壓方式分兩種:一種是向一個或多個傾聽者傾訴,以達到疏導負面情緒的作用;另一種是通過一些刺激阿片肽釋放的活動來達到自我調節的效果,其中后者涵蓋的活動形式包括運動、飲酒、進食、打游戲等。此類解壓活動在應對正常水平的壓力時通常不會極為劇烈,但若個體承受的壓力過大,亦或是傾聽對象過少或效果不佳,它們則可能進一步惡化為自虐性劇烈運動、酗酒、暴食、沉迷游戲等,久而久之,往往會對身體與個人生活造成不可逆的危害。
人,尤其是剛剛脫離家庭溫室、步入成年社交圈的年輕人,都會面對諸多壓力山大、瀕臨崩潰的時刻,而一個人的獨立抗壓性決定的是他的臨界點在哪里。換句話講,獨立抗壓性強的人興許可承受千斤之重,然后在一千零一之際心理防線崩潰,而獨立抗壓性弱的人可能幾百斤的負擔就能將之壓垮、令其哭爹喊娘了。
基于獨立抗壓性這一概念,我個人得出社交的兩重意義:一為積累社會資本,直白講叫搞關系,即維持一個盡可能龐大的人際網,以在事業或生活有不備之需時有貴人可及時相助。二則為維持心理健康,即人們所言的深交,為的是悲戚時有根壯碩大腿可以趴在上面哭。
介于前者更貼近于所謂“功利型”社交,其所形成的人際鏈接必然比后者要弱許多。這種關系放在中國人里面類似于點贊之交,就是朋友圈互點贊、心情好時甚至評論你幾句,然而一旦線下見面,雙方立馬是果斷而默契地低頭不語、擦肩而過。每每這種情況出現,你甚至希望當初沒給對方點過贊,否則也不會如此難言緣由地尷尬。
經營微信朋友圈其實深有講究。人與人互不了解時往往會有偏見,若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別人口中的自己身上,最好方法就是給朋友圈里所有人點贊。點贊這一功能看似沒什么含金量,實際上極為關鍵:你不點一個人的贊,而那個人如果又恰好對你第一印象不佳,且你還點別的他認識的人的贊,那他八成就會覺得你看不慣他,哪怕事實并非如此。反之,若你把所有看見的朋友圈都贊一遍,至少沒有人會懷疑你討厭他,由此可避免偏見的誕生以及其“滾雪球”。對于此現象我不只是說說,因為親眼見到一些八卦一傳十、十傳百時不知不覺就被傳播者依個人口味添油加醋了,而有時人一多疑、再一大嘴巴,就能滾出殺傷力很強的雪球來,尤其在一個封閉性較強的偏僻校園里,更是惡劣。
嘗試跟通訊錄里所有人成為點贊之交不能阻止丑事外揚,但能有效抑制它在傳播中被惡意夸大,直至最后你跳進黃河洗不清。
回到社交的第一重意義,有時會聽到一些人批評這種廣泛建立人際弱鏈接的行為,稱這種為積累社會資本的社交為“虛情假意”、“跪舔”等。我個人認為能說出這種話的人,一半是出于嫉恨。其實任何社交都是雙向的資源交換,你弱貼你的人少,你強貼你的人多,豈不是很合情合理的社會法則?以這一現象論證人心虛偽的成功人士,通常對人際交往時的強鏈接、弱鏈接之別認識不夠充分。“別看我平時朋友那么多,真遭遇重大挫折時,有幾個愿意關心我呢?”這句常聽到的怨言放在一個強弱鏈接分明的社會學思維框架里去看,于是就顯得異常膚淺。
事實上,社會學家Ronald S. Burt在Brokerage and Closure一書中介紹道,大多有成效的資源交換都是通過人際弱鏈接,而非強鏈接產生的。為什么?因為關系屬于強鏈接的兩個人往往有大量的交集,你朋友就是我朋友,最后大家都是好朋友,由此逐漸形成封閉的人際圈子。而圈子這一社交概念,其最大特點就是高頻度資源共享,導致一個圈子內大家能互相提供的很快就全提供過一遍了,于是達到資源交換的上限,很難快速擦出新的火花來。這種情況下,一旦圈子內某位成員產生了其余圈內成員無法滿足的社交需求,成員們所擁有的圈外弱鏈接的價值就凸顯出來了:“雖然我不能幫你,但有個以前和我一起上過暑校的同學好像能幫到你,我去問問他看。”于是乎,弱鏈接在兩個封閉社交圈子間創造了資源傳導的新橋梁,也同時提高了兩個圈子資源整合的上限。
統而言之,朋友是要多交的,而即便是弱鏈接的朋友也要真誠對待。以上是近期讀過的一些社會學文獻的再整理。
201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