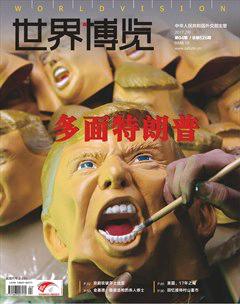發(fā)短信是否有損實際交往?
楊連春
電話發(fā)明時曾引起人們的疑惑,怕影響人們的正常交往。現在,發(fā)短信也引起同樣的問題。
短信使我們離得越來越遠了?我們每天都會收發(fā)許多條短信,美國一天收發(fā)短信就有60億條,通過WhatsAPP和Facebook編發(fā)的信息還有幾十億條。
麻省理工學院的臨床心理專家在學生中開展調查,學生們認為,發(fā)短信與面對面交流有沖突,朋友們一起外出時都在發(fā)短信,偶爾會假裝用眼睛交流,但是心在別處。毋庸置疑,新的交流方式有趣,但給舊的交流方式帶來了沖擊和損害。
學生們講,通過短信交流替代面對面對話挺好。但另一種觀點認為,短信交流還是比不上面對面交流,短信太容易引起誤解,特別是在表達情感時更差,如果不改正,我們只是相互連接的孤島,即便人在一起,還是孤獨的。
電話曾制造了新的粗魯?
當然,新技術不可能固定人們的交流模式,但短信引起社會破裂的反響與一百年前相似。那是一種新發(fā)明,給大眾帶來了新的交流方式,它就是電話。
1876年3月,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展示電話時,因驅動附近一條電器線路的電池正在泄漏酸液,使得電話聲音嘈雜混亂,通話質量受到影響,但它仍然給人一種全新的體驗:第一次人們能與幾個街區(qū)或幾哩之外的人進行即時會話。當時的使用者驚奇地形容:“就象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聲音”。隨后,貝爾對電話機進行了改進,從而客戶盈門,當年售出3000部,1900年底,美國擁有一百萬電話用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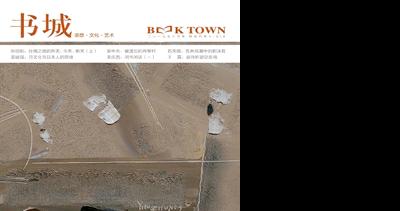
電話首先用于商業(yè),藥商、藥店用來處理訂單,商人能及時聯系到客戶,廣泛宣傳商品,電話變成了商人開展廣泛業(yè)務的處理突發(fā)事件的“第六感”。
電話在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尤其是扯閑篇的家庭婦女更不能使用,商人不讓自己的老婆用電話,除非她們參與了商業(yè)活動。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榮譽教授米歇兒·馬丁說:“一開始,不準夫人們使用電話,商務活動第一”。
但是很快發(fā)現人們希望相互講話,愿意交際。1909年,一家電話公司經理在做電話使用調查時發(fā)現,30%的電話是“閑聊”,且每通電話平均持續(xù)7.5分鐘。他不喜歡這種閑聊,但電話公司最終發(fā)現,將電話賣給找樂、閑聊或搞交際的人能夠賺錢。若干年間,電話公司都做這樣的宣傳:電話可以減少孤獨,可以把朋友聚在一起。1911年,加州一家電話公司宣稱,電話是“家庭主婦的福音,讓家庭生活不再單調,貝爾電話使你不再孤單”。
婦女很快成了使用電話的主力,馬丁教授認為“電話使家庭婦女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解放”,擴大了社會交際面,減少了不必要的面對面的交流。
另一方面,電話的使用者們也在努力地尋找一種得體的電話交流禮儀,看不到人,會話怎么開始才是合適的?托馬斯·愛迪生建議人們以“你好”開始,但禮儀專家認為不妥。有人認為“那樣就像是兩只船在打招呼”,太粗魯,不顧禮儀,和野蠻人沒有兩樣,“你能闖進一間辦公室或一居民家中大聲叫嚷‘你好,你好,我是在給誰講話嗎?”還有人認為,電話對一些事情來說可能是好的,但在處理比如請朋友吃飯等一些微妙的事情上可能就不合適。
然而,電話還是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交方式,打電話的人通過電話每周都與家里交流最新情況,正如1921年貝爾公司廣告詞:“距離沒了,每周四晚上幾分鐘,小家庭成員定時進行兩邊都樂意聽到的閑聊。”
有的電話公司甚至吹噓,電話是對呆板、信任度低的交流方式?——信件交流的改進。1931年貝爾公司銷售指南寫到:“寫信交流只能幫助一時,但友誼不能只靠信件開花結果,當你不能親自訪問客戶時,要定期通過電話溝通,電話溝通讓人感到更加親密。”
不久,一些社會評論家開始擔心:電話上的喋喋不休對我們好嗎?與舊的方法相比,這是一種不完備的交流形態(tài)?美國慈善組織哥倫布騎士會1926年會上提出:“電話讓人更積極還是更懶散?電話是不是非法闖入了人們的家庭生活和訪友的傳統(tǒng)實踐?”其他人則認為,電話讓人交流起來更容易,不再讓人們孤獨,也會帶來負面效應。1929年一位教授就曾報怨,“就是因為有了電話、小汽車和類似的發(fā)明,鄰居們才擁有了可能不斷打擾他人安逸生活的能力”。誠然,相互講太多的確不健康,那樣信息量豈不是太大了?
1897年,倫敦一位作家哀嘆,“不久的將來,人們相互間只不過是一堆堆透明的果凍”。有人煩躁地認為,電話要求人們迅速應對,加快了生活的節(jié)奏。1899年英國一張報紙上寫到,“電話的使用使人們幾乎沒有了應對的思考時間,它沒有使人們的脾氣有所改善,相反使人們在生活中變得狂燥,沒有給家庭帶來幸福和安逸”。
也許最奇特的是待在同一間屋子里,一個朋友給不在這間屋里的朋友通電話。1880年,馬克·吐溫在《一次電話通話》的諷刺文中寫到,聽夫人打電話,他就能了解一半的談話內容。該文指出,對旁聽者來說,電話通話就像是斷斷續(xù)續(xù)的廢話,甚至電話公司也擔心電話創(chuàng)造了新的粗魯行為。
本質上,電話是心靈運輸的工具,能將其他人,包括陌生人突然召集到一人家中,一些焦躁的年輕女性可能就面臨出軌的風險。民謠歌手喜歡在電話上吟唱,騙子們也喜愛用電話騙人。
交流引發(fā)了更多的交流
電話改變了人們的社交信任度,人們不再通過對方的面部表情判斷對方的想法。實際上也有人相信電話改善了人們的社交行為,通話者不得不認真傾聽對方的談話。1915年,一位評論員說,雖然看不到,但必須“耳朵和記憶要全部集中”,“不能走神”。
現在,打電話顯得有些復古,有一位女記者回憶當年約會時,小伙堅持給她打電話,她感到溫暖,愉悅,可她的朋友們則認為這種做法有些奇怪。
學術界認為,通過短信互動的轉變并沒有降低人們的互動,調查發(fā)現,到20世紀中期,電話的出現并沒有損害人們的實際社會交往,有研究發(fā)現那些持有電話的人比沒有電話的人寫了更多的老式信件。皮尤研究中心在當代的調查中得出近似的結論,皮尤發(fā)現發(fā)短信最多的青少年同時也是與朋友見面最多的。交流引發(fā)了更多的交流,因為發(fā)短信并不意味著沒有意義。
卡爾頓大學的米歇兒·馬丁認為我們生活在電話重播的時代,即時交流使電話變得有價值,同時也變得煩人。馬丁說,“因為隨身攜帶移動電話,人們獲得了解放,但是也變成了它們的奴隸”。
詩人卡爾·桑德伯格1916年寫了一首關于電話內容包羅萬象的小詩,他想象著電話被用于各種不同的用途,深刻的和無聊的講話同時迅速傳遞。“愛情、金錢和戰(zhàn)爭,工作、淚水、爭吵聲,大笑、欲望與死亡,由我同時來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