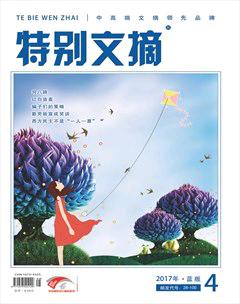臺灣有正宗老北京
2017-04-19 14:33:14龔顯耀
特別文摘 2017年8期
龔顯耀
在臺灣,講的普通話和現在大陸所說的普通話不同。那時臺灣剛剛光復,回到中國的懷抱,可是自己的語言已經生疏很久了,因此為了讓臺灣人民盡快學習普通話,教育部門就把原來在北平(今北京)辦的《國語日報》連設備帶人遷到臺灣,希望能夠推廣普通話。沒想到過去以后就回不來了,臺灣這邊反而因此保住了1949年以前的文化,現在我們學的注音符號都是那時候留下來的。
《國語日報》的那幾位編者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真正胡同里頭的老北京人講話用語非常謹慎,謙恭有禮,祝詞祝語非常多。和我們現在所知的北京人說話不同,市井之間講話非常通俗。1949年以后北京擠進了很多外來人口,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他們定居北京城后,就成了我們現在所謂的老北京人。而且進來之后,原來的胡同就毀掉了,四合院成了大雜院,語言也混了,反而會講純正北京話的很少了。
現在北京人口頭上總是帶著的粗話是原來東北土話。當時土匪們就是這樣講話,雖然后來稀釋掉了,但影響還在。包括現在北京人為什么要喝白干,喝二鍋頭,以前的老北京人喝的好酒是黃酒——浙江紹興產黃酒,但當地反而沒有好黃酒出售,因為所有黃酒一出來,就往南北兩邊走,叫京裝和廣裝,北上京城或南下廣州。所謂“出處不如聚處”,去紹興反而喝不到好黃酒,往南北兩頭運,廣州富裕,北京城多皇親國戚,上流社會他們喝的好酒就是黃酒。
臺灣的老北京人回憶體面的北京人是喝黃酒的。然后到了夏天喝綠茵陳、蓮花白、玫瑰露,這是當年北京有名的幾種酒,是用花蒸出來的。很多老北京人的習慣反而在臺灣保留了下來。
(摘自《我在寶島長大》九州出版社 圖/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