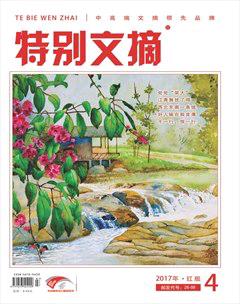處處“裝大”
王文
在首爾仁川機場,一走出機艙,我很快就發現許多“世界之最”式的宣傳標語,比如,在墻上的電視屏幕反復閃現著“仁川:世界最好的機場、最便捷的機場”;在韓國料理的大幅宣傳畫上,赫然寫著“世界最美味的食物”,連機場手推車的內褲廣告詞也是“最好的內褲”。
在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前,我問首爾市的陪同官員:“青瓦臺用英文怎么說?”對方立刻回答:“Blue House(藍宮)。”再問:“為什么這么翻譯,而不直譯?”這位官員很驕傲地說:“因為美國是White House(白宮),韓國當然是藍宮啊。”
喜歡與世界強國比較,或貼上世界級標簽,仿佛是韓國官員的口頭禪。在青瓦臺前一個叫“舍廊房”的韓國全貌展覽廳,首爾官員介紹道,“首爾是擁有最前衛、最美建筑的城市”,“韓國傳統新娘的服飾是最漂亮的裝扮”……這些“最”說多了,有時連隨行的中文翻譯都覺得難為情了。當韓國官員講到“濟州島是世界七大自然遺產之一”時,一同參觀的中國記者團里發出疑慮的噓聲,中文翻譯連忙說:“不好意思啊,這個‘七大是騙人的。”追問后,翻譯透露:“可能是某個國際組織為了迎合韓國人的‘大國心理,在評比‘七大自然遺產前,要濟州島地方政府的錢,然后給了濟州島這個‘美麗的頭銜。”
在舍廊房,最熱鬧的莫過于G20會議的模擬會場。2010年韓國首次舉辦了二十國峰會,接著又在2012年舉辦了核安全峰會。世界最強國家的領導人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在韓國聚首,這被李明博政府視為“歷史性的偉大外交成就”。在模擬會場,大屏幕翻放著G20峰會現場的實況,許多孩子排隊坐在各個首腦的座位合影留念。現場一位韓國小學生對我驕傲地說:“我以后也要成為大國領袖。”
我在首爾先后與十幾位韓國媒體高層交流,發覺韓國同行們開始用“發達國家”來形容韓國。韓國人歷史上一直期望自己是大國,所以有“大韓民國”、“大韓航空”等許多“大”的命名。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發展迅猛,自認為向東雖比不上日本,但卻比西邊的所有亞洲諸國都強。
韓國的許多地理圖標都有與其西部的亞洲大陸試比高、求均等的暗示。那些地理圖案、圖標都有意把朝鮮半島畫得很大,目測的面積足與中國大陸的面積相近。一位自稱是韓國自由派的學者說,其實整個韓國面積與中國浙江省差不多,韓國政府卻在給韓國老百姓“洗腦”,天天灌輸他們韓國的“大”。高麗大學政治系教授金炳局也說,早在盧武鉉政府時期,就一直想發揮韓國的東亞經濟中心作用,而且想“馴化”崛起的中國,但是這種“對意圖和能力的誤讀導致韓國錯誤的角色身份”。
除了比“大”,韓國還志在“獨立”。 在韓國的“故宮”景福宮內,許多參觀者在世宗大王(1397-1450年)的研讀殿前駐足。韓國龍仁大學中國學科教授金善雅說,在韓國,最受尊敬的人、唯一在姓名后加上“大王”的,就是世宗(原名:李祹)。一萬韓幣上的頭像就是世宗。因為是世宗發明了韓文,仿制了韓式的“六禮”,是讓朝鮮民族自主意識的象征,因此,世宗逝世后也被稱為“海東禹舜”。
對于歷史,韓國思想界、史學界使命似乎更緊迫。最近十多年,韓國最重大的研究課題就是,重寫韓國史,勾勒韓國歷史中的大國國運。2010年,高麗大學韓國史研究室出版了權威的《新編韓國史》一書,其中第一章就是“什么是韓國史”,開篇就講道:“要擺脫以統治者為中心的歷史觀和中華文化圈,嘗試把韓國歷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進行研究”。因為韓國的古代史基本上被中華朝貢體系所籠罩,近代又被日本帝國所殖民,“韓國史”多數是被中國與日本所書寫,現在,韓國學術界要從遠古開始,將韓國歷史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比如,講到冰川期,《新編韓國史》第二章寫道:“隨著黃海和大韓海峽的形成,中國大陸、日本列島與韓半島分離”,儼然將韓國視為東亞的中心。
(摘自《大國的幻象》 東方出版社 圖/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