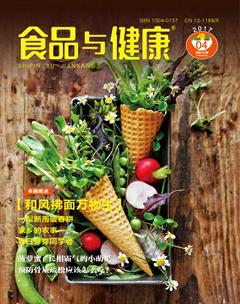家鄉的農事
楊小魚
我出生在東北的一個小村子,因為四面環山,交通不便利,到現在還沒有通動車。我每次從北京回家都要坐19個小時的綠皮火車。盡管春運時臥鋪一票難求,春節我們還是會樂此不疲地趕回家。但相聚的時光終究短暫,雖然能看見厚厚的積雪、美麗的冰燈和家鄉的親人,卻難有時間趕上家里的春種秋收。
家鄉是農業大省。我的姥姥家以務農為生,一家人都是農民。媽媽是大姐,很小就輟學幫助家里種田,養育弟弟妹妹。婚后,因為那時舅舅、姨媽都還小,媽媽也經常會幫助姥姥家種地。家里種植的主要作物包括玉米、大豆、高粱等等。為了給冬天儲備蔬菜,也會種些土豆和地瓜。
媽媽是農業戶口,所以自小我也有幾分田地。小學以后,漸漸對春耕有了更多的認識。現在想想,我們東北的春天來得真是特別晚,四月底五月初,溫暖的陽光才會叩響東北初春的大門。當冰雪逐漸消融,黑土地泥土的芬芳再次被喚醒的時候,燕子從南方飛回來,到我家的房梁上來筑巢。此時,一年一度的春耕就開始了。記憶里的春耕,似乎遍尋不到耕牛的身影,后來專門問過媽媽,她說那個時候不是家家都有牛的,用的時候需要向鄰居租借。
春耕時節,田間地頭到處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快樂身影。田地臨近一條大河,田地與河之間有堤壩。我們一群小孩兒就在堤壩上奔跑玩耍,空氣中也回蕩著我們的歡聲笑語。那時還小,什么都不懂,即使沒有新奇昂貴的玩具也很自在快樂。大人們則“吭哧吭哧”地整地、施肥、播種,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把汗水灑播在土地里,在田埂上種下希望的種子,等待金秋最美好的收獲。
都說“春不種秋不收”“人哄地一天,地哄人一年”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種地的人都是很實誠的,都知道通過勞動才能換來收成。
水稻、玉米、高粱、土豆和地瓜,不同的作物種法不太一樣,有的簡單,有的麻煩些。玉米就很簡單,直接播種就好了。種土豆則要先將發芽的土豆切塊兒,大土豆可以多切幾塊,每塊上面保證有2~3處芽眼,然后放入土中,相互之間還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種水稻得先選擇好稻種,用冷水發泡,水稻出芽之后,再將芽種播撒到苗床上,蓋上土,澆足水,鋪上地膜,等待其長成秧苗。當秧苗長到一定長度的時候,要在田里面注水,拿出來培育好的秧苗,然后開始插秧。
小時候,農耕主要靠人力,插秧只能人工完成。這插秧可是一個技術活兒,不僅要保證每一棵秧苗之間的距離都均等,還要保證插的秧在一條直線上,這活兒才算干得漂亮,沒有幾年的功夫還真做不好。只有真正種過田的人才知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艱辛,才能深刻體會古人說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耕的日子,陽光雨露都是大自然的恩賜,一場春雨一場綠。農民一般會在雨后播種。那時候,真的是靠老天爺賞飯吃,所以農民更加懂得感恩,感謝自然的饋贈。
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我長大了,媽媽也老了,我們都搬進了城里。今年春天,我在家里搞起陽臺菜園準備春播。媽媽說她來種,自己種了一輩子地,最擅長播種了。也許不能全然體會媽媽的春耕故事,但我猜想那里面一定是滿滿的青春和汗水。
對我而言,雖已長大,見慣了大江南北的美好風物,但是依舊懷念家鄉的藍天、白云和黑土,那是令人難忘的童年故事和割舍不斷的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