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倫理的法律邊界
吳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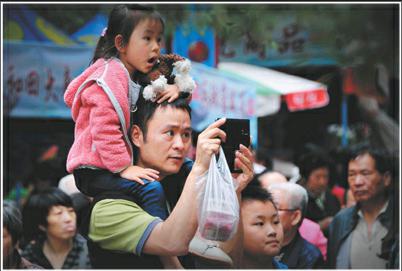
從鄉土社會到轉型的大時代,家庭倫理發生了巨大變化。家庭倫理的法律邊界在哪里?社會的法律邊界又在哪里?一個現代意義的人,在家庭和社會中處于怎樣的位置?
家庭倫理變遷:從鄉土性到現代性
1948年,費孝通在《所謂家庭中心說》中說,從中國鄉土社會看,總是“男歸男的在一起,女歸女的在一起”,小孩也湊一塊兒玩,“性別和年齡劃分著鄉間的日常團體生活”。所以一個家庭里,夫妻雖然共同勞作,共同撫育子女,但“重要在經濟和生育上,而不是重要在個人的社會生活上”。
相比之下,“在英美,家庭才真是他們的生活壁壘”,“他們在家外是競爭、爭斗、講利害;一回到家里,他們享受著感情的共同生活”。因此費孝通把中國家庭稱為鄉土性,而西洋家庭稱為非鄉土性。
數十年后的當下,中國家庭處于一個特別糾結的狀態,鄉土性與非鄉土性混雜在一起,當事者和旁觀者都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一般來說,老一輩熟悉鄉土性邏輯,新一代追求非鄉土性,其間必然產生矛盾。
傳統中國社會講究了多少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在大家都認可同一種價值體系的時代,至少兩代人追求的目標(或口頭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而社會也會創造出制度與特例,來為各人的私欲轉圜。
而到了轉型的大時代,這套法則一定會被沖決。科舉廢除,斷了從仕的道路,國弱民貧,青年又沒有了上升的空間,憤怒引發的革命往往就從家庭開始,因為一個人遭受的束縛體驗必然首先來自家庭。五四時顧頡剛、傅斯年高喊“家庭是萬惡之原”,施存統力倡“非孝”,魯迅則讓子君在《傷逝》里說出那句鏗鏘有力的話: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20世紀中國革命之于社會的改造,乃是由對鄉村基層社會的改造達至人的靈魂的改造,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起,首當其沖的就是“家族制度”,即等級制的父子關系和非平等化的婚姻制度。代表一代人對傳統社會、家庭制度認知與想象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實際上就是對傳統家庭倫理的一次反動,覺醒了的“覺新們”,都是傳統倫理的叛逆者與反抗者。
《家》改編的電影中,有幾個片頭大字:“家,寶蓋底下一群豬。”
上世紀80年代后的家族歷史敘事,可以看做是五四時期矯枉過正的宗族觀的一個回應,此時再提“家族”“宗法”或者“倫理”,就像學者趙園先生所說,“包含于其中的情懷卻大有不同”,它們不再是帶有負面意義的符號了。
當下的家庭之混亂,在于單位化社會已經蕩然,鄉土社會邏輯,因為父母失去了對子女經濟的控制權,也只能在情感層面上進行捆綁。在中國社會的“西方式家庭”就能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嗎?習慣的力量仍然存在,能夠真正劃地絕交的兒女才是極端個案。
然而,當家庭倫理遭遇社會沖擊,又會是什么結果呢?
談一個具體的案例:2014年,打工者楊九在東莞市厚街鎮一出租屋內,揮刀砍向癱瘓的母親,后用剃須刀片割腕自殺。所幸母子二人均無生命危險。東莞第二市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人員經調查認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為,考慮到楊九只身打零工照顧病母多年,對其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
有專家指出,道德上的偉岸和生活上的慘淡,僅僅在法律上適度原諒弒母的孝子還遠遠不夠,真正能避免“弒母孝子”這種“黑色幽默”再次出現的方法只有一個——完善社會的養老體制。
歷史學家孫隆基著有一本《美國的弒母文化》的書,他指出,一百年前,美國的母親與中國母親一樣,發展到后來的女權運動,美國母親想通過對男孩子管制、限制,表達對丈夫的管制,這樣無形中扼殺了男孩子的陽剛之氣,于是男孩們開始反抗,心理上仇恨母親,出現一系列弒母殺母的慘案。這種面臨難以克服的家庭沖突、心理變態的文化危機,稱為“弒母文化”。
西方的“弒母文化”,在中國卻沒有其生存的土壤。這得益于自孟母三遷以來,幾千年的文化滋養。但是,不得不看到,在從鄉土性到非鄉土性轉移的過程中,一系列新的因素呈現出來,中國的家庭關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俠客與青天“黑白配”
由家庭推廣到社會,維系的向度有何變化?
金庸在談及“當代人最需要繼承和提高的是什么”這個問題時,說:“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俠義二字。中央電視臺做‘感動中國的專題節目,要我推薦‘感動中國的年度人選,我選擇的人物都是有俠義精神的人。現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俠義精神。”
對于金庸先生的這句話,有人表示不可理解,認為“俠義精神”是歷史產物,已經過時,就像美國西部牛仔一樣,鼓勵的不是按正常的邏輯思考,按正常的道德規范和法律做事。
過去,法律制度不健全,很多弱勢群體無法得到及時救助,“青天”和“俠客”這兩種一“白”一“黑”的形象應運而出。他們抱打不平、救危解困,無疑受到人們的愛戴,不管是東方社會的“江湖大俠”還是西方的“佐羅”,都是在尋求社會的公正和弱勢群體的幫助。
包括波斯納在內的一些法律認為,法律是起源于復仇的,作為“永恒”主題的“復仇—公平”由此成為吸引讀者的文學作品的重要部分之一。在西方的一些經典作品中,復仇往往也是其主題之一,如《 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作品中都存在著復仇的主線。在文學作品中,由于脫離現實,人們更愿意看到個人俠義精神 。
“俠義精神”并非挑戰或者推翻現有的社會制度或者法制裁判,而是對國家制度出現空白后的一種民間力量的補救。單個的“俠義精神”體現在救助困難群體,而放大了的“俠義精神”則是民間力量對國家的一種責任和態度,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古代司法解決問題的要訣是以抽象的方針為主,即:“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表現在司法方面有兩個特點,一是司法從屬于行政,二是法律服從于道德。以一般讀書人為法官,這也是以道德統法律的一個制度上的前提。”
可以說,“青天”和“俠客”亦是鄉土時代和當時的家庭關系所匹配的元素。隨著法治時代的來臨,兩者生存的土壤逐漸縮小,但并未消失。我們不是需要某一個青天,也不是某一個俠客,而是青天精神和俠客精神。唯有道德與法律相互映襯,共同護佑,才能抵達我們想要的家庭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