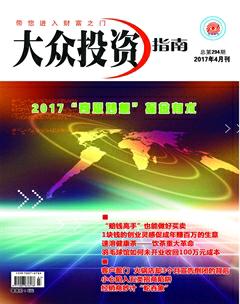淺議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
沈云星
【摘要】著作權制度隨著技術的發展而隨之變化,信息網絡傳播權納入立法正是最好的體現。但是新技術的發展也引起產業模式的變化,并且不斷的影響著網絡著作權利益的平衡。由此滋生的侵犯權利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案件也頻繁發生。從我國現有的立法情況來看,對信息網絡傳播權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立法,但是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就侵權認定的適用標準和適用法律的選擇來看,仍然存在適用混亂的現象。
【關鍵詞】信息網絡傳播權 侵權認定標準 適用法律
一、引言
信息網絡傳播是指著作權人采用有限或無線的方式,在互聯網上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使公眾可以自由選擇欣賞作品的時間和地點的權利。信息網絡傳播權是著作權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著作權人享有的一種專有性權利。例如著作權利人享有利用網絡分享自己作品的權利、有授予他人利用網絡分享自己作品并獲得報酬的權利、也有禁止他人沒有經過許可利用網絡傳播自己作品的權利。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確立不但保護了著作權人的權利和權益,而且實現了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人、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以及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使用標準的混亂和適用法律的不同,導致同案不同判、上訴率高居不下的現狀產生。
二、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司法適用標準之爭
查看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類案件,對侵權案件中適用何種標準在理論上和司法實務中存在很大的爭議。現筆者就幾種觀點進行評述。
1.服務器標準
“服務器標準”是現有理論上略占優勢的“主流”觀點。這種標準主要從現有的技術角度,從客觀上來認定連接行為是否侵害權利人權利。換句話說,侵權的認定應當從信息網絡傳播權認的服務器上來判定深度鏈接行為的法律性質,即以該鏈接內容是容是否存在于設否由設鏈者“提供”為侵權判斷的依據。在理論爭議的過程中,服務器標準的支持者為了證明該標準的可適用性,他們試圖從擴寬適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和傳播主體的范圍來解決服務器標準的缺陷。筆者認為,“服務器標準”雖然從客觀上來判定行為人的提供行為是否侵權,但是對于一種純技術標準,一方面它存在的前提是技術的存在,當這類技術被淘汰后,則會喪失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面對多樣化的提供行為,它并不能全部予以覆蓋。因此,“服務標準”并不是解決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侵權認定標準的最終方法。
2.用戶感知標準
“用戶感知標準”認為設鏈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來作為深度鏈接行為侵權的判斷標準。換句話說,用戶感知標準主要是以普通用戶的主觀感受作為判斷標準。從用戶感知標準的構成來討論,其范圍并沒有突破直接侵權認定的法學邏輯,即只有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才是構成侵權的“行為”要件,而且只可能構成直接侵權,當該行為被認定為搜索技術服務提供行為時,則只可能構成共同侵權或者通過不正當競爭法來予以解決。筆者認為,用戶感知標準即使是從事實出發,但是因其系從用戶主觀出發,且主觀標準沒有具體的把握尺度、隨意性大、對侵權的過錯認定過于寬松等不足,使得信息網絡傳播權權利限制等相關制度無法適用。所以,對于一種不具備法律價值的“工具”仍將其作為侵權認定的標準顯然不具備實際意義。
3.法律標準
“法律標準”即立法的角度出發,在適用的過程中通過對特定事實的評價作為侵權行為的認定。從對事實的認定時同時適用評價因素時,評價因素可以作為事實因素擴張和限縮的依據,這就解決了認定“提供”范圍受限等等問題。正如李穎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挺法官王艷芳認為,對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認定還要考察信息網絡傳播權得真正含義,不能僅看我國著作權法的中文字面含義,而必須追根溯源,考察國際公約對信息網絡傳播權定義的英文含義——“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確定“使之處于公眾可獲取的狀態”是界定“提供”行為的結果。筆者認為,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侵權認定采取服務器這種純技術標準并不能應對科技發展的變化,在復雜多變的信息技術面前總是表現了它力不從心的一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再者,如果以用戶感知標準來認定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侵權,也過于不能對復雜多變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進行完整的評價 ;因此,為了實現著作權人、權利相關人以及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應當支持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行為認定從事實標準向法律標準的回歸。
三、信息網絡傳播權適用法律之爭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與信息網絡傳播權有關的案件存在兩種不同的法律適用的現象。如一些案件中,法院選擇《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作為判決適用的法律,而另外一部分判決中則適用《著作權法》、《侵權責任法》。從法律保護的對象來看,《著作權法》、《侵權責任法》的核心在于保護權利人對其著作權作品的控制,具體到信息網絡傳播權來看,則是對作品的網絡傳播行為的控制。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角度則是對權利人權益的保護,其重點在于權利人經濟利益的保護,屬于一種事后規制。因此,在這類案件中直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解決的只能是個案,且這種判例不具備太大的參照價值,如果在其他案件中直接適用這種判決,則會有法官造法之嫌。筆者認為,雖然在司法實踐中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可在涉案鏈接行為不能被《著作權法》保護時,以回避侵權認定標準的方式時所采用的權宜之計,但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從其作用上來看只是權利人權益保護的兜底性條款,若要解決信息網絡傳播過程中的侵權問題,還需要將鏈接行為放置《著作權法》體系內進行規制。
小結:科技的日新月異,產業模式的變革和法律政策變化,導致著作權法的變遷,使得人們需要跟隨技術發展的步調不斷地審視著作權內容保護的新形勢,并且調整相應的法律法規適用的合理性。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保護權利信息網絡傳播權,平衡權利人、權利相關人、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以促進網絡著作權產業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孟兆平.網絡環境中著作權保護體系的重構.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6.
[2]孔祥俊.網絡著作權保護法律理念與裁判方法.中國法制
出版社,2015.
[3]石必勝.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侵害知識產權的基本思路.
科技與法律,2013(5).
[4]李穎.快看影視APP盜鏈侵權案審理思路和相關思考.中
國版權,2016(4).
[5]韓志宇.快播播放器的經營方式及其法律責任解讀.中國
版權,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