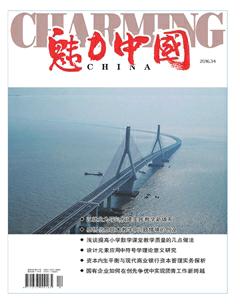趙春華非法持有槍支案的法律分析
崔展豪
【摘要】趙春華非法持有槍支案曾轟動一時,因此案行為人在街頭擺攤經營射擊攤,具有無違法行認識可能性、行為無法益侵害性、判決依據合法性存疑等法律特征,以及動機純良、行為克制、時間短暫且其為弱勢群體等事實特征,引起輿論熱烈討論。本文認為趙春華依法不構成犯罪,更不需討論其量刑問題。
【關鍵詞】槍支鑒定規定;槍支管理法;法益侵害性;違法行認識可能性
一、案件事實梳理
2016年8月至10月期間,趙春華在天津市某街道,擺攤經營一個從別人手中用兩千多元收來的射擊攤位,攤位上共有9支“槍”,使用的是塑料子彈,被射擊的是她每天早上起來吹的氣球。
同年10月,趙春華被巡查民警抓獲,查獲了這九支槍,經過公安機關鑒定,其中六支是能正常發射的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一審判處趙春華有期徒刑3年6個月,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
二、涉案所謂“槍支”不是槍支
我國刑法第128條規定的非法持有槍支罪,是簡單罪狀,法條中并沒有直接規定或解釋何為“槍支”。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要對“槍支”一詞作合理解釋,另一方面又必須遵守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為此,筆者從法律依據、社會觀念和事實依據三方面對涉案“槍支”的性質進行闡述,得出其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槍支的結論。
(一)法律依據
在本案中,法院認定趙春華持有的槍形物是槍支,依據的是公安部《槍支鑒定規定》和《槍支致傷力的法庭科學鑒定判據》。前者對槍支的類型進行了區分,明確將槍支分為制式槍支和非制式槍支,其中對非制式槍支的鑒定需要按照后者來進行,參照的標準是槍口比動能為1.8焦耳/平方厘米,當非制式槍支的鑒定結果在該數據之上時,公安機關一律認定為槍支。
首先需要明確上述兩部規范性文件的性質,作為公安部對下級公安機關的槍支鑒定工作開展指導和規范的內部文件,公安部門在處理行政案件時可以依照該規范性文件對槍支進行鑒定,但是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在處理刑事案件時,關系到刑法典規定的多個涉槍罪名的成立與否,不應當將公安部門的內部規定作為裁判的依據。
其次,關注目前我國對槍支的認定標準問題,技術標準也即形式標準和實質標準也即性能標準二者缺一不可。從技術標準的角度來說,上文所述公安機關的槍支鑒定內部規定可以作為認定刑法意義上槍支的形式標準,則本案中的槍支經鑒定符合了比動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要求;但是從實質標準來說,我國《槍支管理法》對槍支的動力來源、發射器形狀、發射物質和性能特征均作為了規定,而其中性能特征是界定槍形物是否是槍支的關鍵要素,本案中,涉案槍形物雖比動能達到標準,但是其殺傷力遠不及“足以致人傷亡或者喪失知覺”,曾經有人實驗過,所謂的玩具假槍近距離對人射擊時,人最多是有點痛覺,不會出血。
因此,在此就產生兩方面問題,一方面1.8焦耳/平方厘米的標準根本不足以對人產生危險,其是否規定的過低有待考查,另一方面即使該標準規定的不低,司法機關也不能忽視槍支認定的實質標準。如若按照本案的標準來判斷,一顆高速飛行的乒乓球都可能被認定為槍支。
(二)社會觀念和事實依據
本案中,法官對社會狀況了解的匱乏也成為認定趙春華有罪的關鍵因素。在我國,像趙春華這樣的依靠晚間數小時經營玩具槍射擊攤的經濟形式廣泛存在,社會大眾都不會對這種日常所見的玩具槍產生違法行認識。
三、趙春華依法應當無罪
根據大陸法系國家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理論,一個行為要構成犯罪,要經過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階層,下文即為筆者從該理論出發所作分析。
(一)行為不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
本案中涉及刑法罪名為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在本罪中,違反槍支管理規定和涉案槍形物是槍支這兩點是定罪關鍵。如前文所述,本案中的九支“槍”均不是槍支,也沒有違反我國《槍支管理法》的規定,因此不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
(二)行為沒有法益侵害性
在客觀違法階層,趙春華并沒有實施違法行為,更沒有產生法益侵害的危險或結果。被告人從沒有用這些玩具槍對人射擊,也從沒有人用這些玩具槍對人造成危險;社會大眾都不會認為這種遍及全中國的射擊氣球的生意是非法行為,所用的槍是國家禁止的。因此在客觀層面,趙春華的行為事實上并沒有侵害任何法益。
(三)主觀上沒有犯罪意圖
在主觀有責性階層,趙春華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有的九支槍形物屬于國家禁止使用的槍支,而且如前文所述,在事實上趙春華并不具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因此,認定其為有罪的判決一方面無視了趙春華沒有可罰的主觀意思,
另一方面無視了其沒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突破了刑法的主觀有責性階層的要求。
綜上,趙春華依法不構成犯罪,因而也無需討論其量刑適當與否的問題。
四、反思和結語
霍姆斯曾經有言,一部法律如果懲罰了社會大眾都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那法律就太嚴苛了,社會將難以承受。每有類似轟動社會的案件發生時,總會存在司法機關的裁判不符合社會大眾和輿論觀點的情況,誠然,司法機關裁判案件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即使可以考慮社會輿論,也必然要遵守罪刑法定。但是在本案中,且不說司法機關的裁判對罪刑法定的理解是否正確,適用公安部門的內部規定而置槍支管理法規定的槍支鑒定實質性要求于不顧是否合理,當法律法規與大多數民眾的呼聲完全相反時,司法機關在個案中頂住壓力堅守法律,更加需要我們思考的是之后立法機關的行動。法治的進步往往需要犧牲個案正義,那么在個案正義犧牲之后,所謂無法可依也好,惡法也罷,比起案件的轟動一時,更應該受到立法者的重視,避免悲劇在發生。
參考文獻:
[1]劉艷紅.“司法無良知”抑或“刑法無底線”——以“擺攤打氣球案”入刑為視角的分析[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9(1)
[2]張健一,成權.對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的理解[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