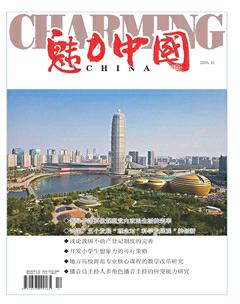“凈化”說與“心齋”說
摘 要:“凈化”說是亞里士多德論及悲劇的藝術效果而提出的,這一理論對西方后世文藝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莊子的“心齋”理論既是一種人生哲學,又對中國古典藝術的欣賞和創作具有指導意義。本文通過對比這兩個理論,找到中西審美心理的異同處和它們分別對中西方藝術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凈化”說; “心齋”說;審美心理
亞里士多德和莊子分別是中西方美學的集大成者,對后世藝術理論的形成產生很大作用。兩人雖生活在不同地域、文明中,卻在闡釋思想時不約而同論及審美心理,即亞氏的“凈化”說和莊子的“心齋”理論,兩者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各自的特點。
“凈化”說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論述上,他認為悲劇是最高級的藝術形式,是一種綜合的摩仿,它貼近人的生活,“憐憫是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恐懼是由這個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而引起的”。[1]觀眾被悲劇中的人物或情節激起這種情感,又通過悲劇發泄這種情緒,這種無害的快感使心靈得到了凈化。后來的“凈化”說運用到音樂和其他藝術當中,強調通過藝術形式使某種過分強烈的情緒因宣泄而達到平靜,保持心理健康。
莊子倡導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追求出世的生命哲學,所以提出了“心齋”的處世方法。《莊子·人世間》有寓言說:顏回向孔子請教游說專橫獨斷的衛國國君的方法,孔子叫他先做到“心齋”,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可以看出,“心齋”的要義就是要,摒除雜念,使心境虛靜純一。在審美活動中,“心齋”就是指排除知識和欲望,用至純的心進行藝術創造與欣賞。
通過對概念的梳理發現,“凈化”說與“心齋”說都強調對心靈的凈化。亞氏主張通過具體的藝術形式排除心理情緒,放下不穩定情感,使心境豁達平和,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他在論述音樂的效用時說了一段話,“有一些人很容易陷入宗教狂熱的沖動,每當他們聽了那種使靈魂激動、狂熱的音調時,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這種神圣的樂調的影響之下恢復正常的狀態,就好像是得到醫治和凈化。”[2]梵高曾經談到過自己在創作過程中時常陷入痛苦,但是內心是很平靜的,這與我們熟知他的瘋魔狀態大相徑庭,可見,藝術對心理情緒確實具有凈化作用。
莊子的“心齋”說本身就強調拋棄雜念,它一方面要求對審美對象的超越,應虛而待物,不持目的性的、功利性的欲望去觀照;另一方面還要求對審美主體的超越,審美主體要超越五官的具體感知,形成系統的整體感受,以忘我的虛無之境融入到審美對象中。其要義在于審美觀照前期的心理準備,達到了莊子所說的“心齋”要求就與亞氏的“凈化”說效用不謀而合。如果說亞氏的“凈化”是藝術對審美心理產生的效果,那么莊子的“凈化”則是藝術產生效果前的審美心理準備,雖然兩者的理論在審美活動中產生效用的節點不同,但是他們都強調了藝術對人的心靈具有凈化作用。
從如今高喊的口號“藝術無國界”中可以體會到“凈化”說與“心齋”說兩種理論的相通之處。但畢竟中西文化差異明顯,因此兩種理論的具體內涵有所不同。
(一)審美主體的創造程度
在論及悲劇的“凈化”功用時,亞里士多德將悲劇看做一個獨立于審美主體的藝術形式,它是一個完整的結構。從設置和觀眾相似的“中等人”為悲劇主角開始,觀眾便產生代入感,并隨情節的一步步發展產生如上所述的恐懼或憐憫,劇情高潮,情感發揮到極致,待整部劇結束,觀眾恍如一夢,心靈得到了洗滌。這個過程里,審美主體處于被動狀態,隨情節的發展產生情感的變化,主體發揮能動性的空間很小。
而莊子將“道”作為基本美學范疇,道無形卻蘊于世間萬物中,因此他提出要超越形式,以“氣”破除物我之間的界限,從而達到“不待于物”的人生境界,要到達這樣的境界首先就要做到“心齋”,這為中國古代審美心理發展奠定了基礎,同“凈化”說被動的審美心理不同,它要求人主動和審美對象進行交流,在審美觀照時審美主體首先要對內心進行整理,排除知識、欲望等,然后在“虛靜”的狀態下同審美對象進行精神對話,最后審美主體通過這一主觀感知過程獲得審美體驗。后來,在這種審美心理的基礎上出現如“留白”“意境”等傳統美學命題,對中國傳統藝術影響很大。
(二)審美移情與物我相融
布洛認為:除了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外,美學還存在著另一種距離,即“心理距離”或“審美距離”。而這種距離是欣賞任何一種美所必需的。悲劇正是如此,悲劇作為舞臺藝術的性質決定了“審美距離”的產生,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需要歌曲、臺詞、情景這三方面客觀因素的參與,觀眾會因為歌曲的渲染產生憐憫或恐懼之情,或因為特定的臺詞產生情感的變化,或舞臺的布景、演員的驚人表現獲得審美體驗,這與觀眾的現實生活之間存在“審美距離”,就像在生活中,沒有背景音樂一次浪漫的求婚顯得有些蒼白,沒有彩排一場婚禮會有些慌亂,觀眾把對生活的期許帶到劇中,用這種完整的舞臺藝術激發出現實生活中的情感,并通過情節的發展達到頂峰,完成一次洗禮。
另一方面,在主觀的情節設置上,悲劇與觀眾也存在“審美距離”。觀眾通過虛構的情節參照自己的人生經歷引起共鳴,但是情節與現實生活的區別讓觀眾保持一定距離,使其既能體會到悲劇主角的情感,又不至于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在眾多巧合下俄狄浦斯弒父娶母,沒有逃脫預言,觀眾可以感受到主角的痛苦,但是也能輕易意識到情節的荒誕,保持理智。
而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強調體悟,強調“物我相融”。“心齋”說最核心的觀念就是要人們從內心徹底排除厲害觀念達到“無我”的境界,從而在進行審美觀照的時候才可以“齊以靜心”,獲得高度自由,與審美對象融為一體。在《莊子·養生主》里,莊子對“庖丁解牛”的故事作了很詳細的解釋,他認為庖丁從解牛中得到快感,產生愉悅的情感,這是因為這是一個超功利的創造,因為技藝的嫻熟達到了“道”的高度,進入自由的境界,庖丁對牛的機體感知已經不用靠眼睛看、頭腦記,而是從心里體悟牛的骨骼紋理,從而使解牛的過程合乎自然規律。
后世發展“心齋”說的理論很多,郭熙提出的“林泉之心”。他強調不管是畫家還是欣賞者都要有審美的心胸,這樣才能發現審美對象的價值,他要求“萬慮消沉”,即莊子所說的“心齋”。蘇軾提出的“成竹在胸”和“身與竹化”的命題繼承了郭熙的思想,重點從審美意象來闡釋,他認為畫家在動筆前首先要將審美對象轉化為審美意象,即“成竹在胸”,把意象完整的表達出來則需要“身與竹化”的精神狀態,這是“忘我”境界在藝術中的體現,給后人在文藝創作中以啟發。
“凈化”說和“心齋”說都涉及了審美心理的問題,并對后世的審美行為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為中西方藝術傳統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如果“心齋”說能體現中國傳統思想中含蓄的特點,那么“凈化”說則體現了西方文化里的實用主義。亞里士多德和莊子兩位美學家提出這兩個命題既受各自文化影響也影響著后世中西方文化的建立。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注.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政治論[A].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作者簡介:
葉帆( 1991 —),女,漢族,四川德陽人,就讀于四川省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傳播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歷,主要研究中國古典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