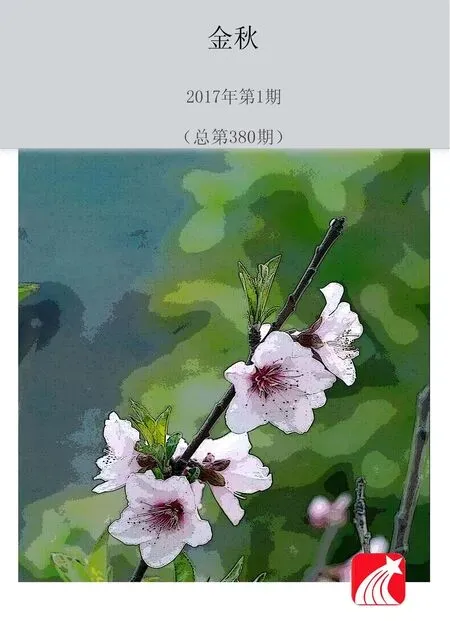看年戲
◎文/山東·半塘月
看年戲
◎文/山東·半塘月

在我小時候,故鄉的年戲總是一臺接著一臺,這可樂壞了村里的大小人兒。鑼鼓家伙一響,像集結號似的,人們都本著那聲音去了。
村子后面的大路上,人很多,接連不斷,都如搬食的螞蟻般,急慌慌地朝前趕。一個胖胖的大嫂,用手拖著一個嘴唇上掛著鼻涕、往后打著墜兒、撒嬌賣癡不想走路的小男孩,嘴里罵罵叨叨:小爹,快點走吧,再不走,好戲可就開場了!是呀,再磨蹭好位置就要被占領,好戲真的就要開場了。
在村子東頭,有一天然形成的高土壩子,上面早被村里的年青人拉著石滾子碾壓了數遍,看起來溜光四平,三面栽好了木桿,掛好了青黑布幔子,圍成了一個大舞臺。舞臺當中,放了一張八仙桌子,村子里的民兵連長鋼蛋,正指揮著人搬運著演戲所需的道具,跑前跑后地布置舞臺。在戲臺左后側,坐著幾個干巴巴的鄉村老者,他們各自手拿二胡、梆子、鑼、笛子等樂器,顯然是伴奏者。其中有個抱著板胡的老頭,眼睛微閉,緊著絲弦,他外號叫大禿子,稍微有點耳聾,人雖是大老粗,但一手板胡拉得無人能比,其曲調或婉轉悠揚或激昂高亢,令人銷魂。
這時,一個須發皆白、面貌威嚴的老者,從布幔子后面站出來,大聲咋呼道:開戲!原來他是劇團團長。大禿子咳嗽了一聲,手把板胡弓子,往高處猛地一挑,再往下一落,一聲勾人的脆響聲響起,緊接著梆子、鼓、鑼、缽齊鳴,頓時,樂曲如渠水般泄出,流暢、光滑、調皮,一會兒,又好似從上空云彩里滑下來的綢緞般,流向舞臺下面擁擠的觀眾群。舞臺下,先前還是人頭攢動,聲音吵吵,聽不見一句人言語,及聽到舞臺上的絲弦鑼鼓聲,人群立馬靜了下來,齊揚起頭來,定格住,舞臺下面的臉,瞬間就連成了一片黃白。
這時,絲弦的聲音高昂起來,鑼鼓的節奏急促起來,鏗鏘鏗鏘鏗鏗鏘,如雨打屋檐,如群雞啄米,舞臺后面的布幔子一動,一個長須的武生,踱著方步從幔子后面出來了,他在臺上左右走了一遭,放聲大唱:高懷德來秉性烈,隨身帶來三尺鐵。邁虎步朝廊愜,但等昏王把頭切。聲音渾厚,抖著腔,花著調,聲震四野,穿云裂帛,最后的音成了鼻音,落在一個“啊”字上,雖沒有麥克風、擴音器等現代化的玩意兒,但激昂的聲音,連遠處村莊不來看戲躺在被窩里撓癢癢睡覺的村民都能聽到,臺下轟然一聲,爆發出一聲雷鳴般的“好”來。武生此時正抖著手腕子,手中的竹馬鞭,有力地抽打著胯下那匹虛無的烈馬,“咴兒咴兒”虛無的馬前跳后躍,武生也隨之前俯后仰。漸漸地,武生不再按尋常的戲路表演了,他巧妙地加入了本地的方言與村俚動作,感情表達豪放夸張,情感表露淋漓盡致,眾人的脖子伸直,眼里放光,嘴巴大張,臉上現出如飲醇酒般的癡醉神情。
哐咣哐咣,舞臺上的人舒展長袖演繹現世人生,而戲臺子下的人們,卻沉浸在歷史的忠佞良奸、悲歡離合中,忘記了時間的飛逝,及等到吹起了謝幕的喇叭聲,演員全都隱于幕后,戲臺上空無一人了,似大夢初醒的人們才嗡嗡地散去,回家睡覺。
今天的一幕戲在與猶未盡中結束了,明天又會上演哪一出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