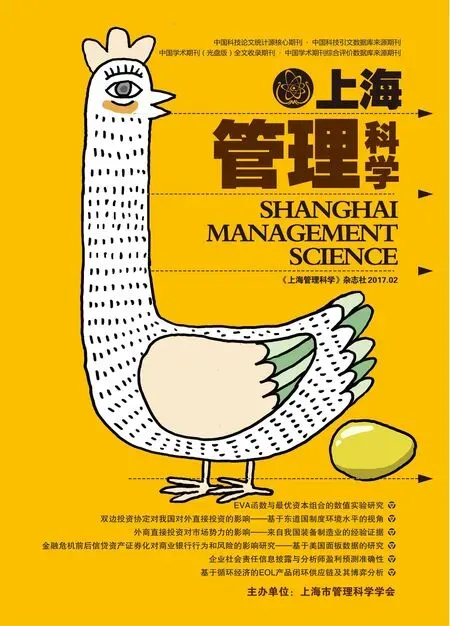巴黎氣候大會“碳減排”對我國能源政策的啟示
程春育 宋 偉 趙樹良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合肥 230026)
巴黎氣候大會“碳減排”對我國能源政策的啟示
程春育 宋 偉 趙樹良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合肥 230026)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簡稱巴黎氣候大會)于巴黎舉行,經過多次談判達成的《巴黎氣候協議》較之前的氣候協議而言具有強制力,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介紹了巴黎氣候大會的主題及《巴黎氣候協議》的主要內容,對我國對巴黎氣候大會作出的貢獻進行了簡單的總結。論述了我國目前的能源政策,運用成本——收益法對其進行評價。通過具體闡述能源政策中的博弈過程,提出從加強國際合作、加強對地方的監管、征收碳稅、改革能源消費結構以及發展碳計量技術等方面對我國能源政策作出調整,以期我國的能源政策更好地適應巴黎氣候大會提出的目標與要求。
巴黎氣候大會;能源政策;博弈;適應
1 巴黎氣候大會概況
1.1 巴黎氣候大會及巴黎協議的主要內容
巴黎氣候大會的主題仍然是“碳減排,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大會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指出,此次大會具體目標是:①動員196個締約國共同簽署一項協議,使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2℃以內;②在大會召開之前,遵循“共同但有區別”、各自能力和公平原則,督促各國提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③要解決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融資渠道和技術問題,希望在2020年前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綠色基金;④通過地方政府、企業和非政府人員的努力,展示其解決方案,作為“國家自主貢獻”的補充[2-3]。
《巴黎氣候協議》案文共有12頁,列有29個大條目,其中包括目標、減緩、適應、損失損害、資金、技術、透明度、總體盤點等內容[4-5];《協議》的核心內容主要體現在:一是到2050年,全球平均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內,并力爭將溫升控制在1.5℃以內,敦促各國要盡快達到溫室氣體排放峰值以確保能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二是發達國家將繼續在節能減排中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節能技術和能力建設的支持,爭取每年資助發展中國家1000萬美元。三是確立了每5年對減排成果進行審查的機制。
1.2 中國的承諾
巴黎氣候大會主席曾說:“大會的成功與否主要看中國”,中國的積極配合是大會得以成功召開的關鍵。截至2015年11月,中國已分別與美國、歐盟、印度、巴西等發達國家(地區)以及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對相關領域的減排做出了承諾,并已經實現了部分減排目標。
《京都議定書》多哈修正案中,中國確定的2020年行動目標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hm2,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m3。
2015年6月提交的《中國國家自主貢獻》對我國2030年的自主行動目標也做出了明確的承諾: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約45億m3左右;中國還將繼續主動適應氣候變化,在農業、林業、水資源等重點領域和城市、沿海、生態脆弱地區形成有效抵御氣候變化風險的機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預測預警和防災減災體系”[7]。
2 我國的能源政策
近10年,全球氣候變化引起了普遍的關注,為了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我國不僅積極地發展國內能源市場,同時還充分挖掘國際能源市場的潛能,加強國際能源合作,一些國外能源企業也陸續被我國兼并或重組。在國內最明顯的變化是,政府積極倡導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同時注重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鼓勵和引導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的變革。

表1 近十年中國氣候及能源發展相關政策
2.1 我國能源政策簡介
表1顯示了近10年來我國氣候和能源有關的主要政策,目前我國已經制定實施的能源政策主要分為強制性政策、經濟性政策(激勵型和處罰型)、技術研發政策以及能源管理政策,其中強制性政策所占比重最大。
2.2對我國能源政策的評價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是“強政府—弱社會”的社會結構形式,“政策的制定者、監督者、執行者都由政府來扮演,政府擁有干預我國能源供需的巨大權力;目前我國的能源政策大多為強制性政策,一般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達,地方無法根據自身環境特點來變通執行,例如對企業污染減排的強制要求就使得在實踐中政策難以落實,弱執行力和強手段的矛盾是能源政策執行低效的原因之一”。政府對環境友好型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等激勵,又會造成其他企業蜂擁而至,最終導致供過于求。總體來看,政府行政引導過多是我國能源政策的明顯特征,導致的結果是資源不能優化配置,節能減排的目標也無法實現,正如圖1所示。

圖1 碳排放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
圖1 中MR表示生產碳排量大的產品的邊際收益,MSC表示其邊際社會成本,MPC1和MPC2表示邊際私人成本。如果生產者根據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來投入生產,Q0即為最優的產品提供量,大氣環境資源也將得到合理的配置。對于生產者來說,在政府監管不嚴格的情況下,企業出于理性經濟人考慮,自由地排放溫室氣體,其邊際私人成本往往遠低于邊際社會成本,生產利潤也隨之提高。如圖1中MPC2<MSC,生產者為了使MR=MPC2,會增加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即Q2),Q2>Q0,大于社會碳排放量的均衡值。
相反如果政府制定非常嚴格的碳減排法規并嚴格執行,生產者所承擔治污成本將大于污染損失,排污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將上升為圖中MPC1的位置,而MPC1>MSC,生產單位產品的私人邊際成本大于其邊際社會成本,生產者獲得利潤降低,出于理性考慮生產者為了不虧損,會按照MPC1=MR來投入生產,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為Q1,此時Q1<Q0,生產者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低于市場的均衡數量,導致該產品市場供給不足,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以上兩種偏離市場均衡點的情況都說明政府如果對環境污染企業的規制力度過大或過小,都不能使環境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分配效率低下。因此,對于我國的能源政策,政府要把握好政策的嚴格程度和可執行性,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3 巴黎氣候大會“碳減排”的政策博弈
在“囚徒困境”下,不論對方選擇如何,背叛都是占優策略,所以博弈的納什均衡是雙方都坦白,所得總收益是所有策略組合中的最低收益。因此,在囚徒困境中,個體出于理性考慮最終選擇不利于集體的策略,納什均衡的達成并不意味著帕累托最優得以實現。
3.1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博弈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開始就存在著“人均不公平”與“代際不公平”的矛盾,各自的碳排量限額始終是二者博弈的焦點之一。以單個國家為例,假定發達國家為甲,發展中國家為乙,在缺乏外部管制的情況下,兩個國家為了經濟發展都對碳排量不加以控制,那么環境惡化就會超過最優排碳限度,兩國的利益都會受損,此時每個國家的收益為a;反之,如果兩個都不排碳,每個國家的收益為b;另外如果一個國家碳排量為零,另一國家排碳,則前者的收益小于后者,排碳方獲得的收益為c,不排碳方的收益為d。假定d<a<b<c,則上述博弈的支付矩陣如圖2所示。

圖2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碳減排”博弈矩陣
對于甲來說,乙是否排碳是未知的。假設乙排碳,甲也會選擇排碳(a>d),假設乙不排碳,甲仍會選擇排碳(c>d);同理,對乙而言,為確保自己處于優勢,無論甲是否排碳乙都會選擇排碳。其結果是兩國都選擇總體最差的策略(即都排碳),最終形成納什均衡(a,a),二者都將獲得較低的收益。在缺乏管制的情況下,假定有n個排碳者,每家國家都有排碳的沖動,這n個國家相互之間形成博弈,并最終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3.2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
在我國的行政組織結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是上下級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但在實際的政策執行中二者更多的體現為委托與代理關系,中央制定政策后下達地方執行,地方作為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會“變通”執行委托人的指示。
中央政府在這個博弈中有制定和不制定兩種策略。地方政府也有兩種策略:嚴格執行和敷衍了事。假設中央政府制定碳減排政策的成本為A(A>0);而不制定碳減排政策,則將會引起環境污染的惡化,由此導致的副效應為-B(A<B)。假定地方政府正常收益為C(C>0,比如稅收等),同時“敷衍了事”則會給地方政府增加額外收益D(D>0);但敷衍了事也存在被上級查處的風險,此時的負效應為-E(E>0)。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矩陣如圖3所示。

圖3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矩陣
該博弈矩陣顯示:如果中央政府對碳排放不作為,不制定碳減排政策,為了地方經濟的增長,地方政府會選擇敷衍了事,縱容環境污染的行為,這樣地方政府收益最大。地方政府執行了政策中“利己”的部分,最終與中央政府之間形成非零和博弈。在中央與地方關于碳減排治理的博弈中,策略性的納什均衡將無法達成。
3.3 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正如哈丁的“公有地悲劇”,如果一種資源的所有權不具有排他性,人們就會傾向于對這種資源過度使用,最終導致這種公共資源無法承載而趨于毀壞。氣候環境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明顯的跨界性和流動性,減排需要地方投入大量的成本,依據公共經濟學的觀點,此時增加碳排放的邊際成本會開始下降,并隨著CO2排量的繼續擴大迅速減少。巨大的減排成本,使得任何單一的地方政府都無法承擔如此大的投入。地方政府之間為了短期經濟利益開始相互推諉,所以,減排也就成為“公有地”的悲劇。
從表1可以看出,A組使用“千聊”平臺作為學習工具,學習效果顯著,尤其是對于MOOC學習平臺課程結課率的提升,以及對優秀生的個性化培優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3.4 政府與企業的博弈
氣候的公共資源性質決定了必須依靠政府這種公共權力來監管。在政府不制定相應的環境保護政策的情況下,企業將會自由的排放溫室氣體,環境污染的惡化將是不可逆轉的。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不可能完全對立,也會出現合作型博弈:一方面,地方政府迫于上級政府的壓力,負責監管和處罰當地企業的排污行為;另一方面,由于污染企業的排碳行為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可能驅使地方政府為了經濟利益而消極執行中央的政策,與污染企業“合謀”,不監管或者提供虛假信息,以應對中央政府的環境監管。
在現實中,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更類似于具有不完全信息特征的混合策略博弈,由于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政府和企業對彼此將要選擇的策略事先都是未知的,二者都以一定的概率選擇某種策略以達到博弈制勝的目的,因此這種情況的結果是,二者都不能增加任何利益,無論雙方中哪一方選擇哪種行動策略。

圖4 中央、地方政府與企業博弈關系
4 我國能源政策的適應性調整
氣候環境作為“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個體對氣候環境的消費不會將其他人排斥在外,同時氣候環境由一個消費者消費不影響其他個人從產品中獲利。個人、廠商在氣候環境的使用過程中也存在著“搭便車”的現象,因此,減排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調整我國的能源政策:
4.1 加強國際能源合作
由于帕累托最優以至少增加一人福利的同時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因此公眾的帕累托最優碳排量是小于個體最優狀態的納什均衡碳排量的,也就是說,實現污染治理的帕累托最優成本大于實現納什均衡的成本,當參與的人數越多時二者之間的差距開始拉大。而各博弈方在碳減排中的充分合作是減少二者差距的最佳方法,因此要對違反協議的國家進行處罰,對遵守協議的國家進行補償,變一次博弈為永久博弈。
在氣候問題博弈中中國應在嚴格控制碳排量的同時努力尋求國際合作,通過達成的巴黎氣候協議來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并敦促發達國家就資金問題早日達成一致。此外要利用協議規定,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以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率,尋求發達國家的碳匯合作,充分發揮已建成的碳交易市場的貿易作用。
4.2 加強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監管
4.3 適時征收碳排放稅
相對于碳交易,碳稅的征收透明度高且實施成本較低,征收碳排放稅是激勵企業減污活動的一種較好的政策工具,它通過增加生產者碳排放成本來引導企業控制碳排量,同時大幅度減少人為資源的浪費。假定現有生產效率不變,對每單位產量的產品征收碳排放稅,碳排量高的產品的凈利潤將會降低,生產者提高該產品產量的沖動也隨之降低;如果提高碳排放稅,生產者對污染較高的產品的生產性資料投入減少,而使用減污資源增加。正如圖5所示,當政府征收碳排放稅T時,生產者的邊際成本就會由MC1上升為MC2,為了保持盈利,生產者會減少向社會提供的產品數量,碳排量隨之由Q1降為Q2。因此,在壟斷條件下,碳排放稅的征收能夠起到節能減排的刺激作用。

圖5 稅收對碳排放的影響
4.4 改革能源消費結構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一條倒U型的環境發展路徑,正如圖6所示,“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呈正相關關系,但存在一個經濟收入水平(即拐點),它改變了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使得二者在此之后呈現負相關關系”。然而,目前我國的環境污染仍然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惡化,二者出于正相關關系階段。因此必須發展低碳經濟,降低碳排放中的經濟效應,促使其拐點提前。
我國煤炭儲量豐富,煤炭長期占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總量的65%以上,由于煤炭碳排放系數高,這就造成我國的碳排量長期穩居世界前列。因此要大力發展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內的清潔能源,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能源產業,逐步降低煤炭消費量所占比重,目前我國的太陽能產業發展已漸趨成熟,后期應更注重引進石油天然氣,逐步提高核能的比重,以實現從過度依賴煤炭向多種能源高效利用的能源消費結構的轉變。

圖6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4.5 發展碳計量技術,細化減排目標
關于碳排放的測量技術、碳匯的標準與計量方法等,大多由發達國家提出,發展中國家在相關領域處于被動接受和學習的狀態。應注重發展相關技術,注重相關數據庫的建立維護與更新,以掌握碳計量等方面的主動性,參與國際相關方法與標準的制定,為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要實現碳排放大幅度降低,這就要求我國的能源政策逐步由倡導激勵型向有限強制性減排的轉變。因此,中央政府要適時地引入碳排量預算,細化每年的總體碳排量限額和人均碳排量限額。由于發達國家人均碳排量較大,我國可以與發達國家進行碳排量交易,讓發達國家因為碳排量透支而購買碳排放空間和權利。
[1]史丹.“十二五”節能減排的成效與“十三五”的任務[J].中國能源,2015(9):4-10.
[2]薛俊寧.中國能源價格、技術進步和碳排放關系研究[D].山東大學,2015.
[3]盧文剛,劉鴻燕.完善我國能源政策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3(2):56-59.
[4]孫愛軍,房靜濤,王群偉.2000-2012年中國出口貿易的碳排放效率時空演變[J].資源科學,2015,37(6):1230-1238.
[5]張躍勝,袁曉玲.環境污染防治機理分析:政企合謀視角[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62-68.
[6]王冰.濮陽市環境庫茲涅茨特征分析[J].中國科技信息,2015(1):48-49.
[7]梁琳琳,盧啟程.基于碳夾點分析的中國能源結構優化研究[J].資源科學,2105,37(2):291-298.
Implications of the “Carbon Reduction” of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on China’s Energy Policy
Cheng Chunyu Song Wei Ren Wanzhu Zhao Shuliang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From November 30, 2015 to December 12th,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the twenty-fir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referred to as the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Paris.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reached a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climate agreement it has force, it provides a legal basis fo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 2020.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theme of the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China to the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The current energy policy in our country is discussed in detail, using the cost - incom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nergy policy in Chin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the main body of the energy policy, propose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imposing carbon taxes, reform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develop carb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to make adjustments to our energy policy, so that China’s energy policy to better adapt to 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energy policy; game; adaptation
C939
A
1005-9679(2017)02-0108-05
2016-12-07
程春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制定與管理;宋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與創新管理;趙樹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與創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