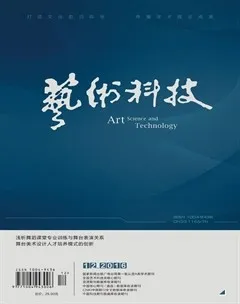淺談莎劇形式化與思想性的關聯
陶晶
摘 要:莎劇產生于特定的時代并受著不同時代的影響,當莎劇進入思想活躍的現代社會,由于受到現代藝術風格的影響,引發了多種戲劇流派交錯紛呈的局面。與此同時,如何對莎劇這樣的歷史劇目在服裝形式上進行保留與創新、用什么樣的服裝造型語言來表達莎劇的內蘊精神,把握特定時代的服飾特征,成為現當代導演尤其是舞臺造型設計領域創作者們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從莎劇服裝設計手法與理念兩個部分來分析和研究現代莎劇服裝造型。文章的結論通過分析莎劇演出服裝造型的發展概況,總結服裝造型的創作方式,要求創作者要找到適合展現現代的服飾樣式的視覺語言,對莎劇進行全新的詮釋。莎劇的演出形式并不是不可改變的,在藝術創作中應該在保留莎劇精髓的同時,又時刻不忘記自己作為后人創新演變的權利,當然一定要尊重莎劇主旨,尊重它所帶給我們的真實感受。
關鍵詞:莎劇;服裝造型;形式化;思想性
從戲劇形式上分析,語言作為交流的必備因素,在溝通與表達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準確貼切的語言描述可以在溝通的過程中使信息得以更順利的流通,錯誤的表達往往令事情適得其反。莎劇藝術也有它自己的語言,這種語言以一種特殊的視聽形式存在,它多樣且富有變化,從視覺部分而言,可以簡要概括為服裝樣式、角色形象氣質以及舞臺場景效果等方面,從聽覺部分大概分為角色的對白、語氣,背景音樂和環境音等。視覺與聽覺所采用的形式千差萬別,所傳達的效果也各有不同,與語言異曲同工的是,這些形式的目的是傳達出創作者的藝術思想與情感,讓觀眾能夠更加清晰甚至深刻地領會到作者的意圖,為了更好地去表達,是需要創作者具有一定的技巧的。
與常見的形式所不同的一種形式叫做極簡主義,英文名是“Milimalism”,也稱為極簡派藝術,或簡約主義。它的含義較為廣泛,不單是指一種藝術流派,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或服裝風格。這是一種采用“極端”方式進行藝術處理的形式,它在最大限度內將藝術形式的內容進行簡化或刪減,只保留最核心的部分,從而彰顯藝術的本質。過程中它去掉了很多輔助性的修飾內容,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最基本、最必要的創作手法來追求藝術最本質、最精華的部分。長期以來,這種藝術形式被很多設計師推崇,它像短小精悍的詩句,常常起到讓人過目不忘的效果,也更容易引發讓人震撼的藝術沖擊力,用極小的內容給人們極大的想象空間。這種“以小見大”的魅力令很多藝術家樂此不疲,他們將自己的藝術思想理念壓縮然后傳達給觀眾后再次釋放,每個觀眾有不同的自我解讀,有時不必追求固定的答案,每個人的理解都是合理的,這給藝術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在傳播的速率上也占有極大的優勢,甚至成為了當今藝術界的主流趨勢。
“經過逐漸消除被證明是多余的東西,我們發現沒有化裝,沒有別出心裁的服裝和布景,沒有隔離的表演區(舞臺),沒有燈光和音響效果,戲劇是能夠存在的。沒有演員與觀眾中間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關系,戲劇是不能存在的。”[1]現代戲劇已經走得更加遙遠、前衛、“反戲劇”。“反戲劇”或者說后劇場藝術仍然是一種戲劇,只不過它強調的是敘述性而非戲劇性。主張以身體為創作的主體,作為在劇場表達藝術觀念的主要工具。即便沒有任何其他的舞臺元素,只有表演,戲劇還是可以成為戲劇。讓演員的肢體語言和運動應該成為關注的重點轉移,行為開始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它和戲劇的藝術形式結合成一個用來體驗世界、了解人生和自我的過程。彼得·布魯克“空的空間”、梅耶荷德“假定性戲劇”、葛羅托斯基“質樸劇場”等,他們一致認為劇場是一種透過自我發現去感受生命的方法,把觀眾的視點集中于演員的演繹上,回到戲劇表演的源頭。
2012年“說書版”《泰特斯2.0》導演鄧樹榮夸張了血腥與暴力的元素效果,巧妙地借助了演員的肢體語言,講出了一個精彩的復仇故事,深深地印在了觀眾的心里。劇中的角色穿著日常服裝演出,當他們脫下日常服裝后竟然露出了戲服,這一設計使人十分難忘,印證了“一脫下日常生活的衣服,其實我們就是一個說書人”。演員一橫排端坐在舞臺里側倒的椅子上,在現場樂師制造的各種雜音中,開始了他們的敘述與表演。整場演出演員只是通過聲音、呼吸、面部表情、肢體動作和空間移位來塑造角色。他們時而敘述,時而扮演,時而評議,在不固定的角色之間來回轉換,跳進跳出,并伴以飽含張力的身體動作和面部表情,來探討人類最原始的5種表達元素的表達能力。7個演員7把椅子,燈光極簡,現場音樂極簡,唯一突出的是演員作為人體的存在。將戲劇變成由一群扮演者在舞臺上表演如何講述一個故事的戲劇。隱匿的暴力沒有削弱泰勒斯的性格,對于制度的理解他有自己的誤區,也因此悲劇不斷,以暴制暴。導演所要表達的深層意思應該是說暴力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一部分,暴力發生于一念之間,如果消除暴力,就需要做到內心的平靜。在冷漠的現代社會中,非理性的狂暴場面所帶來的情感與道德淪陷,將觀眾引入對暴力的體驗,這是一個微妙且復雜的課題。
以“感覺”觸碰戲劇的本質,以“表現”代替“描述”。[2]這句話貼切地形容了形式與思想的關系,弄清楚這一關系對于莎劇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戲劇的本質是思想,思想是無形的、抽象的、無法觸碰的,但思想可以以視聽的形式非常直接地從一方傳達到另外一方,進而去影響或改變對方的思想,這就是視聽感覺如何觸碰到了戲劇的本質。與此同時,為了更有說服力地去影響別人的思想,戲劇的表達形式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手段,有時候像是不同的人在講同樣的一個故事,有的人只是平淡的描述,而有的人則在講述的時候投入自己的情感、情緒,采用的語言形象而生動,甚至配上肢體語言來立體地去表現,這兩種表達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對于戲劇而言,好的設計形式能夠為戲劇的思想錦上添花,也更具有生命力。
在筆者看來,一部好的莎劇作品的影響力,首先在于其精神特質是否完善,其次是承載這種精神的形式是否便于傳播。要做到這些就要著重于自我精神的塑造與強化。對于戲劇演出而言,過度的重復和照搬會使其變得形式僵化,也容易使觀眾審美疲勞。莎劇本身已經具有極強的精神表達力,想要超越極其困難,創作者應當懂得巧妙地“借力打力”,把它的精神力量根據自身的理解與體會進行重塑,傳統與當代的文化差距便可以化作這種重塑過程中的強大動力。推陳出新的過程中仍需要先深入地研究莎劇的精神精髓,同時也要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精神特質,兩方面能夠客觀的接納才會吸收后轉化成自我精神。沒有自己的特質便容易在研究莎劇傳統的過程中迷失自己,陷入無盡的傳統文化之中找不到出路。只有站在一定的角度進行自我精神剖析后,堅定對自己的認識后再去接納傳統,有選擇地去吸收和運用,方能激化戲劇文化的沖突并推動其發展。
參考文獻:
[1]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波蘭).邁向質樸戲劇[M].魏時,譯.
[2] 黃莎莉.當代英國社會與文化背景下的拉爾夫科爾泰作品研究[Z].第28頁.
[3] 曹樹鈞,孫福良.莎士比亞在中國舞臺上[M].哈爾濱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