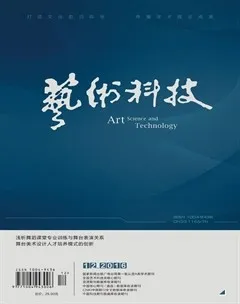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的因素分析
文光錫
摘 要:圍繞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種種現(xiàn)狀,學(xué)術(shù)界不斷進(jìn)行著分析和探討。無(wú)論是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還是必須要面對(duì)的對(duì)于現(xiàn)代性的探討,都是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目前研究的核心問(wèn)題。本文將以藝術(shù)家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型為研究對(duì)象,深入剖析其形成的主客觀因素。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現(xiàn)代;轉(zhuǎn)型
1 從形式和表現(xiàn)語(yǔ)言上看,傳統(tǒng)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無(wú)法超越
走過(guò)輝煌燦爛的古典主義時(shí)期,無(wú)論是在歐洲還是東方,藝術(shù)都曾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無(wú)法超越的巔峰狀態(tài)。前輩藝術(shù)家們塑造了一座藝術(shù)的豐碑停留在曾走過(guò)的歲月中,永遠(yuǎn)地成為了一代經(jīng)典。當(dāng)我們提到雕塑,總無(wú)法將思緒從米開朗琪羅塑造的美妙的人體結(jié)構(gòu)上轉(zhuǎn)移;當(dāng)我們提到經(jīng)典,也無(wú)法將目光從達(dá)·芬奇的《蒙娜麗莎》上移走;當(dāng)提及中國(guó)畫,我們?nèi)詿o(wú)法超越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站在當(dāng)下,回眸過(guò)去,那些曾經(jīng)燦爛的歷史將成為我們豐厚的藝術(shù)積淀。那是多少藝術(shù)家們不斷探索、不斷質(zhì)疑、不斷創(chuàng)造、執(zhí)著前行所走過(guò)來(lái)的路。我們今天,面對(duì)他們?nèi)匀粺o(wú)法抑制這穿越千年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給內(nèi)心帶來(lái)的震撼;我們不斷學(xué)習(xí),頂禮膜拜。然而,駐足和回望不僅僅是讓我們認(rèn)識(shí)來(lái)時(shí)的路,歷史的價(jià)值不僅存在于對(duì)過(guò)往的收藏,更在于其相對(duì)于現(xiàn)在給我們帶來(lái)的啟發(fā)和導(dǎo)向性作用。如果總停留在對(duì)經(jīng)典的不斷復(fù)制和模仿上,那將意味著當(dāng)代藝術(shù)意義的消減。因此,在形式和表現(xiàn)語(yǔ)言上,仍然停留在對(duì)經(jīng)典的復(fù)制甚至模仿上,已經(jīng)不足以支撐當(dāng)代藝術(shù)繼續(xù)前行。而當(dāng)代藝術(shù)繼續(xù)前行的動(dòng)力將存在于意識(shí)形態(tài)中,作為藝術(shù)品的內(nèi)在驅(qū)動(dòng)力引導(dǎo)著當(dāng)代藝術(shù)不斷向前探索和發(fā)展。也就是說(shuō),思考要在創(chuàng)作之前,形式要與內(nèi)涵融合。
2 從歷史的維度和社會(huì)價(jià)值上看,客觀的再現(xiàn)已經(jīng)成為過(guò)去
當(dāng)代藝術(shù)從對(duì)形式的細(xì)致追求走向?qū)?nèi)涵的反思與批判,又將思想上的反思與批判以更加夸張的表現(xiàn)形式物化為藝術(shù)作品。這些都與歷史發(fā)展至今的多角度的客觀因素密切相關(guān)。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后,大機(jī)器實(shí)現(xiàn)的批量化生產(chǎn)推動(dòng)了市場(chǎng)的進(jìn)化,促進(jìn)了當(dāng)下社會(huì)大消費(fèi)時(shí)代的到來(lái)。當(dāng)消費(fèi)輻射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時(shí),它已經(jīng)使我們的生活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對(duì)于人類生活所發(fā)生的變革,可以用“現(xiàn)代化”一詞來(lái)概括。當(dāng)整個(gè)人類的社會(huì)走進(jìn)現(xiàn)代化,人類生活中所衍生出來(lái)的藝術(shù)則不可避免地進(jìn)行著現(xiàn)代化的演進(jìn)。無(wú)法忽視的是,將藝術(shù)推向現(xiàn)代化的客觀處境是矛盾而辯證的,這導(dǎo)致隨著歷史的演進(jìn)、社會(huì)的發(fā)展,藝術(shù)將不可避免地被推向這樣一個(gè)結(jié)點(diǎn),即面臨著現(xiàn)代與反現(xiàn)代、當(dāng)代與反當(dāng)代的糾葛。從這一現(xiàn)象上看,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在大環(huán)境中的角色和職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內(nèi)心的復(fù)雜、焦慮、迷失和渴望,引導(dǎo)20世紀(jì)70年代末的中國(guó)人從盲目崇拜過(guò)于樂(lè)觀、只看到光明的狀態(tài)中逐漸走出來(lái),開始關(guān)注人生的灰暗面。
藝術(shù)作品也從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轉(zhuǎn)而出現(xiàn)了悲劇性的色彩。對(duì)于苦難的關(guān)注,引發(fā)了人們對(duì)苦難的思考。藝術(shù)家對(duì)于苦難源頭的思索和追尋,讓他們逐漸地走向了藝術(shù)的真實(shí)。藝術(shù)家們關(guān)注視角的轉(zhuǎn)變形成了20世紀(jì)70年代末至20世紀(jì)80年代初的“傷痕藝術(shù)”。經(jīng)歷了傷痕藝術(shù)的過(guò)渡,人們渴望新生活和新藝術(shù)的念頭終于在1985年得到了逐步的印證,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藝術(shù)領(lǐng)域的“85思潮”。自1978年以來(lái),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全面實(shí)施改革開放重大舉措,至此,人們的生活也開始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時(shí)期人們?cè)谒枷肷辖?jīng)歷了一個(gè)緩慢的過(guò)渡階段,對(duì)新事物及藝術(shù)等上層建筑領(lǐng)域有了一個(gè)逐漸接納、開化的過(guò)程。但是,許多畫家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還在束縛中沒(méi)有蘇醒;直至1985年,其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種種可能性才逐漸顯露出來(lái)。“85思潮”打破了藝術(shù)刻板模式化的僵局,藝術(shù)家們提出“創(chuàng)作必須是自由的,作家必須用自己的頭腦來(lái)思維,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shù)表現(xiàn)方法的充分自由。”這一時(shí)期藝術(shù)家們開始了對(duì)藝術(shù)形式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開啟了對(duì)于傳統(tǒng)和秩序的反思。他們以辨證的眼光思索藝術(shù)的現(xiàn)實(shí);藝術(shù)的現(xiàn)實(shí)不應(yīng)該是客觀表象的現(xiàn)實(shí),而客觀的現(xiàn)實(shí)并不一定是真實(shí)。由此,藝術(shù)創(chuàng)作開始探討藝術(shù)的真實(shí)。藝術(shù)的真實(shí)源于藝術(shù)家對(duì)客觀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理解、思索和批判;藝術(shù)的真實(shí)不應(yīng)該拘泥于對(duì)客觀現(xiàn)實(shí)的刻畫,而應(yīng)該側(cè)重于人物對(duì)客觀現(xiàn)實(shí)的洞察與真實(shí)感受的表現(xiàn)。“85思潮”引發(fā)了許多藝術(shù)家對(duì)自我存在的關(guān)注及其自我意識(shí)的覺醒。如袁慶一的油畫作品《春天來(lái)了》,著實(shí)強(qiáng)調(diào)了畫家的自我存在意識(shí)及其對(duì)存在的感受和領(lǐng)悟。
藝術(shù)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的重要分支,受到客觀環(huán)境的影響,迫使藝術(shù)以更加激進(jìn)的方式或者說(shuō)更具表現(xiàn)性的語(yǔ)言來(lái)闡釋。這與曾經(jīng)的經(jīng)典、客觀地再現(xiàn)過(guò)去,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gè)時(shí)期的問(wèn)題。
3 藝術(shù)家批判意識(shí)的覺醒
站在這樣一個(gè)歷史結(jié)點(diǎn)和藝術(shù)發(fā)展結(jié)點(diǎn)上的藝術(shù)家們,不得不對(duì)藝術(shù)進(jìn)行現(xiàn)代性的思索。其中,若干藝術(shù)家出現(xiàn)了描繪現(xiàn)實(shí)卻又以空虛的形象來(lái)表現(xiàn)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于問(wèn)題的逃避態(tài)度。女畫家喻紅以寫實(shí)的手法刻畫人物形象,同時(shí)賦予每一個(gè)人物形象以空虛的表情,以示人們內(nèi)心的麻木和逃避。例如,其作品《烈日當(dāng)空》中重復(fù)僵化的女人的臉。而在畫家岳敏君的畫面中,不斷重復(fù)出現(xiàn)的是張著大嘴笑的臉。這種面部動(dòng)作夸張的笑容反映出人物思考的停滯,以麻木的笑容獲取情緒上的平復(fù),實(shí)際在于掩蓋內(nèi)心的破碎,表現(xiàn)了人物逃避的心理動(dòng)態(tài)。同時(shí),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偶爾還能夠看到其對(duì)政治上的諷刺,如其作品《處決》《自由引導(dǎo)人民》。而他們的思索將會(huì)受到他們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人在社會(huì)中所感應(yīng)到的力的影響,以及他們作為一個(gè)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應(yīng)該有的藝術(shù)敏感,這種藝術(shù)敏感讓他們站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思索人類最根本性的問(wèn)題。藝術(shù)家們普遍遵循以“新人物”為創(chuàng)作主體,以“新思想”為創(chuàng)作題材的創(chuàng)作法則。這一時(shí)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人物主體形象主要為高大的領(lǐng)袖形象以及工農(nóng)兵的形象;而創(chuàng)作的思想則圍繞著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實(shí)行的全面專政展開。藝術(shù)家對(duì)于藝術(shù)現(xiàn)代性的思索引發(fā)了當(dāng)代藝術(shù)在思想上的批判和形式上的表現(xiàn)。可以說(shuō),現(xiàn)代化的到來(lái)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引發(fā)了藝術(shù)家批判藝術(shù)的覺醒。
當(dāng)然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在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shí),不應(yīng)該僅僅強(qiáng)調(diào)在意識(shí)上過(guò)于狂躁的批判和形式上過(guò)于夸張的表現(xiàn)。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不是對(duì)傳統(tǒng)的遺棄和排斥,更不是對(duì)現(xiàn)代的單一批判。因此,藝術(shù)的現(xiàn)代性應(yīng)該在于其對(duì)于當(dāng)下的判斷和思索。藝術(shù)無(wú)法逃避其現(xiàn)代化的出現(xiàn),也無(wú)法排斥其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面對(duì)這樣現(xiàn)代化,藝術(shù)家更應(yīng)該進(jìn)行的是對(duì)藝術(shù)現(xiàn)代性的思辨和對(duì)藝術(shù)表現(xiàn)語(yǔ)言的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