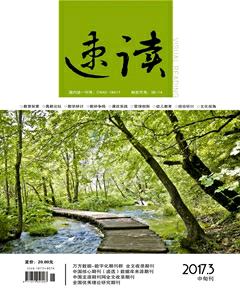陶淵明詩歌意象的張力
遼寧大學文學院 遼寧 沈陽 110136
摘 要: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的詩歌、散文從古到今被人們所稱贊與研究。新批評的“張力論”是新批評學派的重要發現,由最初對文本內部結構規律的研究,經過發展上升到一種系統的文學批評方法,采取一種哲學的態度發展成為一種方法論。這一重大發現,在西方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借鑒“張力論”去研究陶淵明的詩歌或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新發現。
關鍵詞:文學張力;陶詩;意象
一、文學張力淵源
“文學張力”的提出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發展演變過來的。“文學張力”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美國意象派詩人龐德的理論。龐德提出他的“好詩”理論,他指出好詩是一種“意象的復合體”,一種“在瞬息間呈現出的一個理性和感情的復合體”。[1]這個定義內在的包含著意象結構的兩個層面。意象的內層是“意”,是詩人的內在世界,也就是詩人理性與感情的復合。在一定程度上,龐德受到了表現主義的某些觀點的影響,他把詩看成思想感情的表現。另一方面,龐德不僅關注情感,也注意到思想理性。他說,“藝術給予我們有心理學的資料,有關人的內心,有關人的思想與其情感之比等的人的資料”。[2]
二、陶淵明詩歌意象的張力
(一)陶詩中的松、菊
陶淵明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他象許多封建士大夫一樣,懷有大濟天下天下蒼生于水火之中的理想,比如他的詩歌《雜詩》:“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那個“殺奪而濫賞”、朝不保夕、人命低賤的社會里,陶淵明自愿投進社會政治斗爭的洪流之中,希冀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救人民于水火,救社稷于懸崖。但是,現實的生活并不如他所愿,奸佞當道,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這種心情體現在陶淵明詩歌中的松樹的意象。如他的詩《飲酒》其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古代的詩歌常常把眾草比喻成奸佞小人,“眾草沒其姿”形象地描述出當時的社會面貌,社會黑暗,小人當道,忠良被害,百姓民不聊生。雖然陶淵明痛恨當時的統治者,但他仍然相信眾草雖然現在生活的繁盛,氣勢洶洶,但是當嚴寒到臨,寒霜降臨,眾草的生命力抵擋不住寒冷,最終會衰退死去。“卓然見高枝”,不畏嚴寒的松樹即使處于酷寒的環境仍然始終保持住自我挺立的身姿,保持住本我的真心。松樹這一形象是當時陶淵明身處復雜政治斗爭人格立場的寫照,處于自己的理想愿望不被認可的朝堂中,陶淵明也躊躇過、痛苦過、抱怨過,但是經過自我一番復雜的斗爭之后,對于出世與入世的深刻沉思后,他大概被松樹挺立與風雪之中的身姿所感動,陶淵明選擇退守,選擇疏離社會的主流群體,他從松樹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諦,即尋找心中的“自我”,松樹卓立于凝霜之中的姿態給了他奮進人生的勇氣。此后陶淵明歸隱田園,他的心態是平和的、寧靜的。“菊花”的形象是他放棄了官場上爾虞我詐之后,由松樹的寄托過度為菊花的寄托。實際上,陶淵明寫菊花的句子不多,袁行霈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所提到:“但因‘采菊東籬下,悠然現南山這兩句太著名了,菊便成為他的化身”。這一句話也是陶淵明回歸田園的生活的升華寫照。田園生活正是他在無數的寒夜之中苦苦尋找的靈魂的歸宿。在那里他的心與身皆釋然。一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久在樊籠里,復得反自然”,可見詩人回歸田園是極其快樂的。他快樂的心境具體體現在他的菊花的意象之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其五)詩人已經融化于大自然之中,人、山、鳥成為一體,一切自然而然。這成為詩人高情遠志的象征。
(二)陶詩中的酒
其實更能表現陶淵明一生的變動,他的人格象征的意象便是“酒”。在蕭統所編寫的《陶淵明集序》中提到:“有疑陶淵明篇篇有酒”。正如袁行霈所說:“酒,已成為其人生藝術化的媒介”。陶淵明以酒寄情。首先,他的飲酒是多多少少與當時的時局和世道有關。就像阮籍飲酒是為了麻痹自己的敏感神經,疏離政治的黑暗,陶淵明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比如他的詩歌《飲酒》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陶淵明借酒命題的政治詩,這是其中一首,詩中對于時局的感嘆,失望之情躍然紙上,但是陶淵明的政治態度并不是積極地抵抗,而是作為一名冷眼旁觀者,盡量遠離斗爭,過自己的生活。再次,陶淵明的飲酒詩雖然會與政治有關,但是基于他的政治態度,可以得到他的飲酒詩的真諦更多地表現在抒發心中喜悅的心情,飲酒詩是他田園舒適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他的《飲酒》之十四:“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深味呢?結合陶淵明的經歷和人生觀看。這種深味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在之味;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童真之味;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的真摯之味,是陶淵明經過無數次的思考,抉擇之后對自己人生的大徹大悟,對生死的釋然,泯去后天經過世俗熏陶的,浴火重生的“真我”。這是陶淵明飲酒的可貴之處,這也是后世無數詩人受其影響、受其鼓勵激發的感動之處。
在中國古典文論中,如虛實結合的創作原則,也就是追求文本超越字面意義的多層含義,是一種言外之意的效果。所以,陶淵明詩歌中象征意象的運用,以實寫虛,寄托陶淵明不同的人生情感。比如在分析松樹的意象時,《飲酒》其八寫道:“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以“青松”和“眾草”兩個意象進行對比,“青松”喻高潔的品行,指君子;“眾草”喻小人,前后差異對比,差異的程度便體現張力的程度,從而產生出奇跡性的力量和思想。新批評派認為這點正是詩歌本質所在,也是詩歌張力的表現之處。
參考文獻:
[1]艾倫·退特.論詩的張力.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121,130.
[2]羅杰·福勒編.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354.
作者簡介:
周凱悅(1993—),女,漢族,山東臨沂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6級文藝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