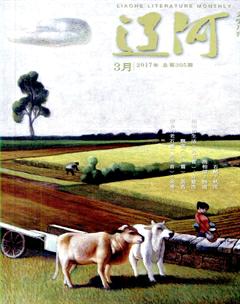讓我抱抱你 (外一篇)
王霞
那年冬天,我參加黑龍江省文聯的筆會,從雞西乘車返寧。他一直相伴左右。我們并不同路,他是繞道相送。
十天的筆會,我們相識。同是寫詩,風格也相近,還在幾家雜志上數次同刊。此次得見,除了感慨人世間的機緣外,還頗有惺惺相惜之意。由于年齡相近,又同是來自南方。有幾位大哥大姐就生出了撮合之意。言語間逗趣不說,還在筆會結束時的聯歡會上,讓我們合出一個節目。他會唱,我善舞,倒也配合得默契,贏得滿堂彩。
我本不同意他陪送,之前的交往我也處于避讓。面對他熱烈的追求,也明確地婉拒。可是上了車,才發現他也在。車已開動,我也無奈。
一路上的細心照顧不待言述,令人感動,就是今天想來,心中尚有微微的潮熱。可是兩地遙遙,少年失怙的我,還有年邁的母親需要奉養。面對愛情,我理智得冷酷。
一路多是無言相對,他除了輕聲哼唱晚會上的那一曲,就是讀詩,從萊蒙托夫到泰戈爾,從李商隱到納蘭性德。
當那綠皮火車穿越了長長的幾個白晝與黑夜,抵達南京站時,是一個未明的黎明。寒冷的車站,我要等候5點第一班郊區通勤車,而他要重新購票啟程。他執意要先送我上車。時間在靜默中悄然流逝,4點45,通勤車如期到站。他把我的行李送上空無一人的車廂,定睛看著我,那目光中掠過一道道痛楚的波紋。
“可以抱抱你嗎?”他說。
我無言,不知如何回答。
他俯下高大的身軀,輕輕將我擁在懷中。我的頭只抵到他的胸前,那心跳隔著薄呢風衣清晰可辨。一路不安的我,突然心定,腦海一片空白的澄澈。仰起頭,看到那面龐似乎也是釋然的平靜。
這是第一次來自異性的擁抱。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用這樣一個擁抱平復了自己。但我卻從那個擁抱中,感受到一種憐惜和尊重。雖然還未萌芽的愛情就這樣無疾而終。然而這個溫暖的擁抱卻讓我堅信了愛情的純潔美好。
生活中,有很多時刻,語言并不能替我們準確地傳遞心意。因此,我們常常說,語言是蒼白無力的。而一個簡單的肢體動作,卻表達了我們復雜的內心情感。
好友莉的丈夫患癌去世時,他們的兒子才5歲。殯儀館追悼會上,看滿目的黑底黃帳、聽哀樂伴著陣陣哭聲,一股寒冷刺穿心臟。那個5歲的小男孩。他還什么都不懂,著一身黑衣,高高舉著爸爸的遺像,奔來跑去。我把他攏在懷中,那小小的身子不安地扭動著,不由得我就淚流滿面。我想起自己的當年失怙,還比他大著幾歲,那種經歷已不堪回顧。如今,這小小的身軀,就失去了山一般父愛的呵護,怎不讓人痛斷肝腸!
那哭干眼淚的未亡人,站在冰冷的遺體旁,接受親朋好友的各種問候與安慰。我看到她的眼神其實是僵冷的空洞的。當我走到她的面前時,什么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張開雙臂抱住她瘦弱的肩,輕輕拍著她的后背。我感覺到她的身體慢慢從僵硬中松弛下來。我的肩頭感受到她淚水的潮濕。我就這樣擁著她和孩子,把孩子的小手塞進她的手中。以后,這將是支撐她走過艱難的最主要的勇氣。
后來,當她走出傷痛,曾在一次相聚時對我說過,葬禮上我的懷抱是她在整個喪事過程中,唯一感受到放松軟弱的時刻。也正是那短短的幾分鐘擁抱,使她滑下了即將崩潰的巔峰。
2006年的夏天,87歲的母親猝然離世。之前因為老人家身體尚好,又或許從小父親離世,唯母子相依,所以在心底就屏蔽了母親也有一天會離去的概念。當那一刻突然來臨時,我的心中一片空白,在鄰家大姐的指揮下,機械地做著當作之事。唯有一件,我堅持自己為母親凈身換衣。我把母親抱在懷里,母親的身體冰涼而柔軟,軟軟地依在我的懷里。我屏住滿眶的淚水,細細體會著母親軀體的印象。童年那個溫暖的懷抱,是我最明媚的天堂。我的印象中,母親很少說過教導和指責的話。無論日子多么艱難,我做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我所有的疼痛、不安或者驚懼,都消失在夜晚:母親把我攬在懷中,不是講著那些古老的故事,就是輕聲哼唱著戲曲。我在溫暖和寧靜中進入一個又一個美妙的夢境,這讓我能用明媚的眼睛和面龐開啟新一天的生活。可是什么時候,我離開了母親的懷抱?我又什么時候,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地給過她同樣的擁抱?我可曾想到過,日漸老邁的她,面對遲暮的歲月,可曾有過我年幼時同樣的擔憂與害怕?母親呵母親,你依然的恬然淡笑背后,在對女兒的理解和寬容之外,有沒有一絲絲期待?如今,你這不肯僵硬的身體,是不是還在用最后的氣力滿足女兒最后的心愿:讓我還你一個擁抱,此生無憾?
那之后,我常常在兒子出門的那一刻,突然從后面抱住他,把臉龐貼在那寬厚的肩背。偶爾他會調皮地躬起身,把我背了起來,惹得我大聲驚叫,才把我放下來。然后,我看著他高大的身影走出門去,心中是無比的篤定。
是的,我喜歡上了擁抱。上天讓我們擁有雙手,絕不只是為了勞作或者鞭打。它更應該是愛的傳遞工具,將我們和親人、朋友緊緊地融為一體。
每一個我珍視的時刻,每一個我珍重的人,當我無法表達我繁復的心情時,那敞開的雙臂是我最真摯的表達。
艾香如夢
這兩天貪涼,受了寒,胃部隱隱不適,吃了藥也不見好。飯后,倦倦地躺在沙發上,疼痛變得越來越劇烈。于是起身,拿出艾灸盒,插上艾條,點燃,放在中脘穴上。一會兒,熱氣透過艾灸盒的細孔,滲入肌膚,同時,那草木的藥香也漸漸彌散。漸漸地,絞痛減輕,人也隨之朦朧起來……就覺得是在小時候的家里,地上熏蚊子的艾草正在冒煙,好大的煙霧,嗆得我直咳嗽。媽媽拉著我,一邊用蒲扇扇著煙,一邊往外走。突然驚醒,原來是睡著了。這才覺得,屋內煙氣有些嗆,胃卻是不那么疼了。
細細嗅嗅,煙氣中艾香夾著些微的辣氣,這必是艾條所用材質不純。推開陽臺窗,初夏時微涼散了進來,已是燈火闌珊時了。
又想起了母親。母親出身中醫世家,通曉些醫理。我們兄弟姐妹小時候,有點小毛小病,都是媽媽中醫偏方對付,倒也健健康康。當時不覺得什么,如今回想起來,除了那一份智慧,還要多付出多少的辛勞,滿滿的,都是愛。
就說這艾灸吧,小時候肚子痛,都是媽媽親手料理。先切姜片,一元硬幣那么厚,放在肚臍上四指的位置,然后把艾絨捻成圓錐型的柱,放在上面,點燃頂部。媽媽必是守在旁邊,給我講古兒。她是怕我耐不住性子亂動,燙傷了自己。媽媽講的古很多,有一個和艾灸有關的,我印象特別深。說是古時候有一個江洋大盜,作案無數,可就是逮他不著,有一次寒冬臘月,官兵把他逼進了深山。大家想這回他非凍餓而死了。沒曾想,來年春天,他又作案。直到九十多歲才被抓到。那時,他還精神飽滿,肌膚潤澤,健步如飛呢。由于案情重大,他被判了死刑。臨刑前,監官問他:你這么高的年齡,還有這么好的身體,有什么養生秘術嗎?他回答說:秘術我沒有,只是年輕時師傅教我在每年的夏秋之交,在小腹部的關元穴,用艾條施灸千炷。久而久之,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熱,幾日不吃飯也不覺得餓,臍下總是像有一團火那樣溫暖。他被處死后,刑官讓人將他的肚腹剖開,看見一塊非肉非骨之物,凝然如石,這就是長期用艾火灸出來的。
母親是個心細之人,也追求完美。她用的艾絨都是自己做的,沒有雜質,燃起來就是純粹的艾草香氛。
我和母親一起做過艾絨。盛夏時,哥哥們會到門前河灘上割艾草回來,母親就把艾葉打下來晾曬,粗梗部分就拿來熏蚊子了。
曬干的艾葉,我幫媽媽搓碎。然后,媽媽用木臼來搗。臼下墊著厚厚的抹布,先放一些碎艾,搗一會子加一點,慢慢地多起來,最后成了毛絨絨軟綿綿一坨。而后,把搗好的倒入篩面的細羅里篩,篩出細細的灰塵樣的雜質,然后放到臼里再搗,再篩。這樣大概四五次,就沒什么粉塵了,艾絨也只有不多的一團了。母親把艾絨包在紙包里,第二天還要這樣再曬一曬,然后收起了,備用。
每年媽媽都做這樣幾包,大大一堆艾葉,只能做出一小團,雖不值什么錢,可卻需要耐心和辛苦。也許正是這樣,鄰居們少有做的。常有人來向媽媽討要,或是孩子鬧肚子,或是大人扭了腰等等,都來要一點回去灸。媽媽每次都還細心地指點穴位,比較復雜點的,還會親自去幫忙灸。
記得那年居家動遷,臨行前有半個多月沒在家吃飯,鄰居們排隊約請,飯食簡單,其心火熱。
啟程是在一個晚上,那么冷的夜,好些叔叔嬸子都在我們空蕩蕩的家里呆著,陪伴著我們,還有他們帶來的桌子、凳子和茶,最后一直送上車。
當我多年以后,回到這里時,老鄰居們最愛嘮叨的是母親的熱心腸。那些母親不經意間的星星點點的小事,人們還都記得。感喟之余,深深覺得,那些年,鄰里之間的情誼,一如艾草的香氛,樸素而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