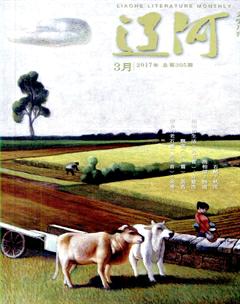醉在你的春天里 (外一篇)
楊巧麗
一條干凈敞亮的大道,把我送入群山環繞之中。涼風習習,車窗外閃過遠處近處的綠意朦朧,讓心一直浸淫在“聞道春還未相識”的意境中。這是一次頗有深意的采風,我不想癡迷于城市假山中的流水淙淙、住宅小區里的花團錦簇,我要到這大山深處尋找春景別樣的氣息,別樣的風姿。
車在一個岔路口拐彎,駛進一個村子,這個村子名叫上射垛,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山村不大,一條主街道,幾條小巷,三十來戶人家,一家一戶的院落依著山勢規劃而建。路面是鋪過的,水泥地;房屋用青磚或者紅磚做墻,紅瓦蓋頂;也有用石頭做墻基的,這是就地取材,既方便又牢固。村西南新修的大路寬闊平整,從此經過,遠處的山體,近處的房舍,身旁的小水庫,盡收眼中。村東北路口最寬敞的地方,可以同時停放兩輛面包車、一輛小汽車,中心主街道也寬到能通過一來一往兩輛車,這里是村子的繁華地段。早在行程的路上,朋友就向我們隆重介紹這個山村的歷史,他說村口有石碑為證。石碑上“大清”二字及四周花紋清晰可見;很多人家都有這樣一種款式的桌子——帶抽屜和底箱,這些帶有晚清和民國印跡的家居用品,把時間的光釬拉得很遙遠,讓我深為感嘆。再往遠古看,這個叫做上射垛的地方,曾經是被賦予另一段歷史印跡的里程碑。唐太宗李世民為收復疆土,在此山中屯兵安營,設靶練兵。而后,在有霸垛的地方,聚集了一些靠耕作度日的農人,這些農人用他們的汗珠子耕種著貧瘠的深山薄地,造屋立家,養育后代,把原本只有自然生態的世界演繹成富有鮮活動態的人類活動,戰爭、災荒、生老病死,讓這些頑強的生命在不斷擠壓的重負中滋長延伸,最后定格成我眼前的這樣一座美麗的小山村。
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對農村有一種天然的親切和依戀感。如今踏進這農家小院,便有種歸家的感覺呢。時光仿佛倒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那個讓我打小就熟悉了的黃土高坡上的家園。那木制的小圓桌,我家不也有一個嗎?當著民辦教師的父親算半個農民,休息的日子里,不但要干農活,也要理家,他憑自己的聰明和勤謹,添置家居用品,緩解家計的窘迫和艱難。那時家里的許多物件都是父親親手制作,想來眼前這藍漆的小圓桌也是這小院主人親手做的吧。咱樸實的農家人,哪個不會著幾樣極簡單極家常的手工活兒呢?幾節小木料,幾塊舊磚頭,幾把錘子啊斧子啊的小工具,拿在手里這么一擺弄,一件小物件就成了。吃飯的小桌子、坐著的小杌子、冬天生火取暖的小爐子,就是這么來的。小院主人是位年過七十的古稀老人,身板兒硬朗,腳步兒穩健,具備了山里人那種典型的樸實、敦厚、爽朗、好客的品格。見到來人,男主人把他那天空藍的小圓桌拾掇干凈,擺開馬扎,招呼大家坐下,又喊女主人沏茶倒水招待客人。可是話音剛落,他又等不及腿腳不夠利索的女主人進屋,自己一溜煙從屋里取出茶壺和茶杯,那是一整套嶄新的家什,想必平時自家人舍不得用,只等有貴客上門才拿出來的。端起茶杯,淺淺地啜一口,一股茉莉花的清香沁入心脾,五臟六腑頓時熨帖起來。
品著香茶,聊著話題,我又細細打量一番這普普通通的山村院落。一溜北房,石塊做墻基,窗臺下面幾層是用紅磚砌起,上面是土坯墻;土坯墻上的石灰墻面大部分已脫落,門窗上的格子是用塑料紙蒙著的,有風的時候便發出瑟瑟聲響。兩間東屋,都是一磚到頂蓋成,比北屋要新,一間上鎖,看樣子是住人的,一間敞著的,沒門,是廚房。西邊是搭起的棚子,放些農具等雜物,北墻根的窗戶下堆著柴火……哦,這格局和我曾經的家園是多么的相似啊!唯一的缺憾是,院落的布局局促,不像我記憶中的小院那般寬敞,總在院子的一角留塊空地種草養花。記得那時我和姐姐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種雞冠花、美人蕉和指甲草,然后等指甲花開,染紅了手指,在風一樣的年齡渲染自己的五彩夢。已經好多年沒有做這樣的事了,生活遺忘了很多也許不該遺忘的東西。不過我很快就明白過來,山里人家的家里是不需要養這些花花草草的,這些花呀草的都在外面的山上呢,抬眼一望,滿是啊!走吧,我們爬山去!走吧,我們賞花去,我們看風景去!
山里人家出門即是山,而我因為從小生長在高原,爬過的山屈指可數,爬山的次數也寥若星辰,自然對每一次爬山都非常期待,并保持高度熱情。今天的爬山是一個“天賜良機”,除了有意氣相投的文友,還有一位熟知地理地形的向導彭大爺。有了向導,我的肚子里便裝了滿滿的山野知識,光野菜的名字就記住了一大串,什么米布袋面布袋,什么哨子殼溜溜嘴,還有那螞蚱菜、艾葉子、車前子、菊花芽、薺薺菜,更不用說那山間的傳聞,山村的建設史,讓我聽后竟有了樂不思蜀的想法。若是以后有人向我討教,我一定如數家珍一一道來。我們一邊行走,賞心悅目,拍照留影,一邊辨認身邊的花草、野菜。每每看到有新苗簇擁,總有一番爭辯,同伴中有說這是鳶尾草,有說是別的什么花草,正在爭執不下,彭大爺過來說,這個是金針菜。旁邊不知誰說了句,山里人不養觀賞花草,這話讓我感慨萬千,是啊,山里人的生活還是清苦的,他們哪有閑功夫賞花賞草的,他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一輩,勤勞一生,雙手長滿了老繭,雙肩壓出了紅印,他們用一生的信念守護在這里,使這里的一山一脈、一草一木都有了靈氣,有了生命的活力,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山之魂!
爬山途中,我的心情是雀躍的,緩坡陡坡上裝滿了喜悅,花草樹叢間蕩漾著笑語。“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我們來得正是時候。草綠了,樹綠了,滿山滿坡綠得逼人的眼!還有那紅的、黃的、紫的,各色的花兒競相開放,更有那漫山遍野的山桃、山核桃、野連翹,這都是這山野里的無價珍寶啊!山桃花、野連翹花已盛開,那粉粉的桃花呀,一朵一朵,似在向你招手笑呢,把人的魂勾住了不讓走。野連翹長在極高的峰頂,海一般地連成一片,金黃金黃的,彰顯著生命的活力。有人把寫菊的句子改動一下,用“滿山盡披黃金甲”來形容連翹花開的盛景,有人吟詠“千步連翹不染塵,降香懶畫蛾眉春”而贊嘆連翹花的嬌嬈。我也曾用拙筆贊美它的傲然挺立:“四瓣一花展嬌顏,叢枝向天欲爭俏”。而眼前此情此景,美輪美奐,春意盎然的長西山,初綻綠意的山坡,橙黃的連翹花星星點點,與粉紅的山桃花交相輝映,構成一幅唯美的春景長卷。
平整出來的田地里,青油油的麥苗如給這山坡披上了綠地毯,把農人的希望裝在里面。常聽人說窮山惡水,這個詞用在這里不合適。瞧,那邊是口井,井里的山泉水常年不干涸。彭大爺手指遠方對我說,他說這樣的山泉井有十多個,供應著全村人的吃喝、牲畜的飲用水、還能保證地里莊稼的定期澆水。他又說,用山泉水和我們自己種的優質黃豆做出的漿豆腐,營養豐富、滑嫩爽口、豆香濃郁,十里八鄉的人都愛吃,這是我們上射垛村的招牌呢。彭大爺的話就像那甘甜的山泉水一樣,汩汩滔滔,流進我的心底,沁馨我的肺腑。
上射垛的春天,真美!你長在了我心里。我呢喃低語,發自內心的贊嘆。
夏天也美啊。山桃熟了,紅紅的、甜甜的,入口生津,滿嘴沁香。金黃的麥子收割了,磨出的面粉香噴噴,吃上新麥面的人們呀,甜在心里,笑在眉梢。
上射垛的秋天才美呢。秋天是收獲的季節,高粱紅了,玉米老了,連翹結籽了,山核桃熟了,村民的腰包鼓了。
還有冬天呢。飛雪漫天,覆蓋山野,銀裝素裹,分外妖嬈,長西山就如仙境一般的美啦!
身旁的同伴七嘴八舌,快語如珠,吐出一串串贊美之詞,用各自的心聲描述上射垛的美。
站在山坡,回頭遙望村莊,紅磚建起的房子整齊地掩映在山坳里。綠的草、紅的花包圍著它,一泓碧水像明亮的眼睛,默默守候著山村的祥和和寧靜。
而我,只為這春天而醉。
請你綁定我的愛
那天一上班,就接到王永老師的邀請電話。參加一個文學筆會,對我來說,總是那么有誘惑力,于是,在一個明媚冬日的特定時刻,放逐了自己疲憊的心,享受了一次醉人的文化洗禮。
我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喜歡把自己綁定在某一處,用一種執著的熱愛來詮釋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一旦綁定,終生視為一體,休戚相關,榮辱與共。十多年前,當我把自己變成章丘人,就越來越感受到這塊熱土的魅力無窮、燦爛厚重。章丘,這一顆鑲嵌在齊魯腹地、泰岱之陰的明珠,她承載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她成就了無數文人墨客的精彩與輝煌,她是華夏子民智慧的凝聚和見證。龍山黑陶的冠絕古今,危山兵馬俑的舉世驚鴻,百脈泉群的譽滿天下,千古才女李清照的精美詞賦,都在華夏文明文化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我都以敬仰和崇拜的心情,或傾耳聆聽,或流連瞻仰,或傾情抒懷,雖筆拙心鈍,不能夠十分之一甚或百分之一感受那種酣暢淋漓、震懾心魄的美的意境,卻也樂于修身養性,陶冶心靈,以熾烈的情懷體會那每一時一刻帶來的精神愉悅。
自以為對歷史人文感興趣,幼時即受古老文化的熏陶,聆聽過諸如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而這些來自遙遠天邊的故事,總是給人一種神話般的魅力和不可想象的神秘感。也不曾想到某一天,來自眼前的真實會揭開那層不可預知的面紗。
第一次與章丘文學接地氣就是文祖,和文友一起登攀鳳凰山,欣賞漫山遍野芳草萋萋、林木蔥郁的秀美秋景,聽他們用地道章丘話侃大山,飆山歌,描繪白云洞的神奇傳說。雖然常常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但從他們爽朗的笑聲中,我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驚喜和收獲。而再一次踏進文祖,那種濃郁的古鎮文化氣息,又使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震撼。
文祖、錦陽關、三槐樹村、三德范村,這些熟知的名字如今在我心里顯得特別的不一般。這些地名,可不只是一個地域的標志性符號,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地方名詞,它們都有著很深厚的歷史淵源,是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歷史解碼器。據《山東通志·通記》記載:“丙辰七十有三載,舜受終于文祖。”文祖一名由此而來。鴻蒙之初,開天辟地,泰沂大山,拔地而起。堯禪讓舜,舜耕歷山,罷武興文,穩定一方。千年古鎮,文德祖廟,青山傲骨,人杰地靈。這里,有叱咤疆場、躍馬揮鞭的英雄豪杰馬元;有行俠仗義、義薄云天的俠客靳載璋;有孝敬公婆、勤儉持家,被清朝道光帝欽點樹牌坊的好媳婦郭氏;有唱腔優美動聽、語言生動風趣、表演樸實細膩、地方特色濃郁的五音戲和具有上千年優秀歷史的民間藝術三德范芯子。眾多的碑刻和傳說、古遺址、古建筑、古山寨、古墓葬、古樹名木,無一不是歷史沉淀的證見,無一不是文明文化的印跡。
車出文祖鎮向南,前行約十數公里,崇山峻嶺間,一座高閣凌空飛現,使原本蕭瑟酷冷的寒日頓時生動起來。聽前來陪同的鎮領導侃侃而談,我才知道,這就是著名的錦陽關,它是春秋戰國齊長城的一個重要關隘,既是交通要道,也是軍事要寨。齊人為了抵御魯人的侵襲,在周圍的險峻山峰或制高點上修筑城堡、烽燧,居高臨下,扼其咽喉,為固守家園的安寧和諧做出了最大努力。
佇立關口,極目東眺,齊長城蜿蜒匍匐,向前延伸,雖風蝕雨侵已失去了雄姿,依然能讓人想象當年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勢!
那個膾炙人口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嗎?它離我的生活竟然是這么近,于是,兒時聽到的那些神奇傳說仿佛就在眼前發生一樣真切。相傳孟姜女和她的丈夫是一對恩愛夫妻,她的丈夫被拉去修長城,久久未歸,孟姜女身背寒衣,不辭辛苦,千里尋夫,來到了錦陽關,才得知她的丈夫早已累死,尸骨無尋。孟姜女被這噩耗打倒,跪在關前哀嚎痛哭,其聲悲切,感動上蒼,驚雷激雨,竟然震開一截城墻,露出其夫尸骸,孟姜女悲不自已,跳入斷裂處與其夫合葬而亡,成為一段亙古永恒的愛情佳話!
錦陽關關口就在三槐樹村。三槐樹村,顧名思義。名字本身不奇,由此衍義而來的故事傳說卻很有嚼頭,勾勒出一個風流皇帝寡情薄意的形象。癡情的夏姑娘為這不值一文的風流債佛堂孤燈下苦等十多年后,懷著怨恨香消魂散。同樣是悲劇,這個故事凄而不美。自古以來,平民與帝王之間的愛情雖轟轟烈烈,卻往往因他們的地位懸殊、利益沖突等現實問題難以善始善終。孟姜女和她的夫君雖出身貧寒,卻相濡以沫,不棄不離,生死相依,才有著感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美傳。
行走在文祖這塊歷史文明文化寶地,咀嚼著這些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就像是和一位歷史老人在做心靈的交流。漫步章萊古道抒思古之幽,登游玄帝閣發憂今之慨,賞錦屏奇秀贊江山多嬌,觀新村新貌嘆時代巨變。2015年8月25日,省政府針對章丘市部分行政區劃的調整申請,進行批復,同意“撤鎮設辦”,成立文祖街道辦事處,在機制上促進了新文祖E時代的領先發展。
如今,在我綁定的愛之歌上,文祖、三德范、齊長城、錦陽關的歷史意義,給我的機體注入新的精神營養,也讓這片熱土又多了一顆熱愛她的赤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