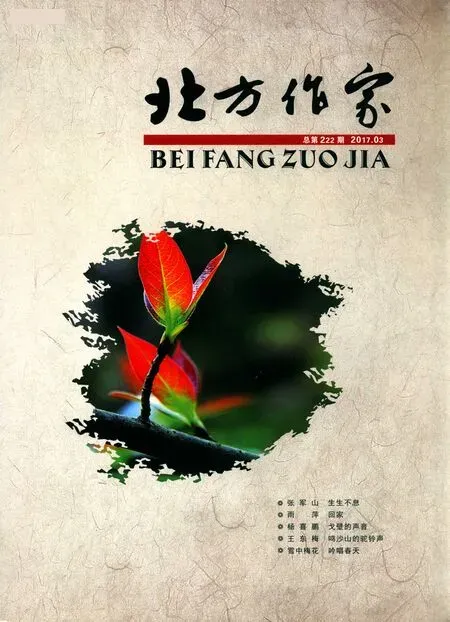春日小記
木門長子
春日小記
木門長子

花箋
每個春天,我都會打開書箋袋看一看,那里邊有許多用花葉做成了書箋,很是漂亮。我叫它們花箋。這些花箋是春、夏、秋三季采集的一些花葉做成的,各種形狀,各種亮麗。有一枚用杏花做成的書箋很有意思,小小的枝上連了兩朵花,一大一小,是淺黃色的,偶爾還能在花心里看到細細的蕊。這些花都是干花,在喪失了水分的情況下依舊不失風華,的確讓人驚奇。這是我收藏它們的原因,也是許多年來我一直不愿意將它們丟棄的最大理由。
做花箋是從一位兒時朋友那里開始的,她人長得漂亮,花箋也做得好,精致些的還會用紙袋包裹了存于木盒或信封之內。我收集的一些書箋,則夾在書里或者散落在相冊里。記得一本2005年買的《紅樓夢》里存放得最多,有楓葉做的,也有用花瓣做的。這些書箋有的是動物圖形,有的是樹木圖形,有的則簡單到只是一兩片花瓣。樣子細細長長,花瓣玲瓏剔透。總之,每一枚都有自己的俏與好。
有一枚用桃花做的書箋我最喜愛。讀書的時候一邊嗅食花香,一邊在字里行間尋找人文的魅力,累了還可以將桃花瓣拿在手心里把玩,輕輕的,像捏住一只蜜蜂。那一刻,花箋的形狀美不美,色彩艷不艷都是存于思想中的好東西。倘如將花箋放在陽光底下映照,更是別有一番韻味——花的脈絡縱橫交錯,花的質地清透薄亮,簡直如蝴蝶的翼一般。
后來,大概是太小心了,竟然不知道將那枚桃花箋放在了哪里,總之找了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找到,反而失落了好幾天。再后來,我又收集了一些小的梧桐樹葉子做書箋。這種書箋初春時節長成的最好,形狀美,色澤俏,有一種獨特的潤澤感含在里邊。但三月的葉子畢竟少,又比較嬌嫩,采擷起來不太容易,所以到手的并不多。
最好的花箋要等到暮春或者秋后收藏,那時候地上的落花、落葉很多,有時候純粹就是鋪天蓋地。撿形態完整尚不失水分的花、葉沖洗干凈,置于陰涼的地方晾干、壓扁,一張漂亮的花箋就制好了。大一點的葉子箋可以夾在厚重的書本里,小一點的花瓣箋可以放置在較薄的書籍里,只等閑時打開,再睹一番季節的芳香。
做花箋大概是女孩子們都喜歡做的事了。小的時候能用來玩耍的東西不多,能去的地方也很少,既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但纖纖玉指是不能閑著的,女兒家的小活計也是不能少了的。所以,做花箋這種事兒在女孩子之間很是風靡了一段時間。我們像崇拜張愛玲一樣崇拜花箋,像膜拜瓊瑤一樣膜拜我們的小制作,更有聯想豐富的女生獨辟蹊徑,用毛線或者碎布片做書箋,只不過這種書箋要用膠水粘貼,然后存放到透明的硬塑料袋里。毛線、布片一類的小玩意我也做過不少,一邊做一邊送,到現在竟然是一件無存了。
春來。屋里暖暖的,我突然又有了做花箋的心情,想再收集一些漂亮的花箋做紀念。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的手藝是否尚好,時間是否充足,是否還會有我的女兒和我一塊忙碌這件事,但思想畢竟因此活躍了起來,如剛剛走過冬季的心情一樣,要的就是一份清新和三月里才有的誘人春意。
生活很精彩。我的花箋,也許并不只是花箋。
細柳
也許是姓氏的原因,對于柳這種植物我有著莫大的喜愛。在春天,我看著它早早地青綠,在秋天我看著它遲遲地落葉,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冬季,我也會仔細地端詳上它片刻,如同讀一本書一樣思想它的存在。我居住和辦公的地方都植有柳樹,是那種常見的垂柳,細細長長的葉子,細細長長的枝,淡淡的如一抹不去的詩意。
唐代詩人賀知章說:“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是描寫柳樹的,也是對柳最好的刻畫。細細想來,柳這種植物真是絕妙,樹枝兒婆娑,樹桿兒略有彎曲,如一位妖嬈的女人站在陽光下輕擺秀發一般。絲絳,又是多么恰當的比喻,讓人的眼前忽然就有了柳的碧綠,柳的質感,心境舒暢竟如綠浸染過一般。
柳樹的樣子總讓我想起河邊浣紗的西施,如見她一邊吟唱,一邊將紗在水里輕輕地擺動,既享受著春天的美好,又在感受清香的氣息。
春,這個溫暖的季節讓柳有了非凡的品質。
私下里,我以為用“綠”來形容柳樹是最好的。在冬的灰黑色沒有褪盡之前,綠就悄悄地跑來了,像個魔女似的一邊舞蹈,一邊唱歌,偶爾還在風里打個滾兒說說調皮話。綠色,是三原色之一,本就是大地的顏色,綠與柳巧妙的結合更讓世界增添了韻味,令人忍不住賦它于詩,寄它于情,贊它每一枝條上的色彩和絢麗。
有雨的日子最好。柳在雨里就是一位婉約的小姑娘,著綠衣,披長發,裊裊婷婷。雨點輕輕地落在它的葉子上,發出“沙沙”的聲響;風柔軟地拂過,清涼之中讓你感受騰云駕霧的意境。倘若再有翠鳥兒恰好在枝杈間吟頌,那就有了更上一層樓的愜意,精言妙句會不知覺地從心里爬出來,手指也會不由自主地揮毫潑墨,由是關于春柳的故事就那么成了,于心神飛揚間書寫世之精華。
“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寫柳最好的感覺應該到河邊,所謂“七九河開,八九燕來”“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河邊的柳下正因為有了風吹,有了南歸的燕聲會顯得更加精美。
河岸上的孩子蹦蹦跳跳,大大小小的風箏蕩在空中,耳邊響起悠揚的舞曲,喜悅自心底慢慢地攀升。柳在此時是歡快的承載,幸福的象征,它歌之舞之,就那么春水向東,擾亂了人的心情。
柳色引春來!有人說。
柳的確讓人陶醉,而最入心的醉卻是于花前柳旁狂飲了。
春水
南唐詞人馮延巳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春天,是水的季節。立春的節氣一過,空氣里就開始抖動起暖暖的風來,癢癢的惹人心肺,就想推開門走向曠野走向河邊,去探尋春的消息。哪里的花開了,哪里的葉綠了,哪里又有了新氣象也會在心底惦記許久。春天,“水”這個字最誘人,因為河開,也因為河開之后的碧波蕩漾。站在岸邊,看河面上激起的層層漣漪,聽波濤拍擊堤岸的聲響,暖意會不自覺地向著心靈深處游去。
老人們走上河岸強身健體,孩子閉了眼睛傾聽天鵝的歌聲,花朵草葉于樹下綻放出青綠,姑娘們著了春裝徜徉。春水就是一位著紗衣、戴珠翠的小姑娘,裊裊娜娜地來,嬌嬌美美地在,聽取蛙聲一片的同時,觀魚兒調皮地玩耍。
《晉樂府古辭》里說:“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意思是:二三月的季節,岸邊的碧草倒映于水中,水底的藍草映襯著水色,兩者渾然一體。細想想這樣美麗的景致,如果有船,一定會在船上看到河里搖曳的水草,看到草間游動的魚苗。風輕輕地拂過耳邊,“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句子會自然而然地跳出來,成為一個季節的留想。
我不知道古人是怎么游春的,更不知道那些美好的詩詞是怎么寫成了,但他們一定和我一樣有著春色中的神情搖曳和浸于春天中的情不自禁。
這幾日讀李煜,總在為這位南唐詞人的才情陶醉,為他的命運唏噓。其實,我很希望李煜成為一個快樂的人,不為憂國,不為愁思,那句“一江春水向東流”也不是用來表達哀怨惆悵的,而僅是對春的抒情和贊美。他身邊站著的小周后也一定不會哭哭啼啼,在暴君趙光義的淫威下委曲求全。她一定歡歡笑笑地伴君而來,卿卿我我地與自己愛著的人兒秀恩愛。小菊花、碎花裙、高跟鞋妝扮著她,天空大大小小飛翔的風箏陪伴著她。她眼里有的只是笑,和對春水無限的眷戀。
但逝者如斯,這也只是我的想象,我愛的詞人他畢竟已經不在。
站在堤岸之上,遙遙地能聽到河面上飄來的歌聲,如一波春水鉆入心底。那是老年歌舞團的老人們在排練慶“三八”的節目,一首嘹亮的革命歌曲,一首時下流行的 〈小蘋果〉輪番演繹。春水伴隨著她們歌聲。絲弦輕起,撩人心扉。有人的地方就有風景,有景的地方就有春來。三月,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季節。
由不得想起了自己喜愛的花箋,如果時間充裕,我完全可以用眼下的景色組幾幅圖,山水樹木個個入畫,花色人情樣樣不缺,更有那東去的春水成就一波青幽。
“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原來,美的意境就是這樣悄然而成的。

柳萍,筆名,木門長子,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擅長小說、散文的創作,曾有作品散見于《博愛》《故事家》《新故事》《微型小說選刊》《天池小小說》《喜劇世界》《小小說月刊》《戀戀中國風》《中華傳奇.新懸疑》《文存閱刊》《天水日報》《小說月刊》《壹讀》《百家講壇(藍版)》《河南日報》《揚子晚報》等報刊雜志、文集合本和電子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