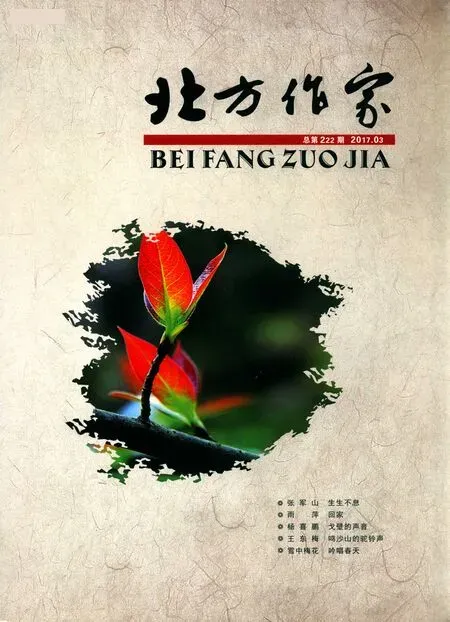戈壁的聲音
楊喜鵬
戈壁的聲音
楊喜鵬

插圖/宋星宇
久居戈壁多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戈壁的聲音。
戈壁的聲音,不單純是荒涼的沉寂。面對(duì)戈壁,沙丘連綿無際,漠風(fēng)掠嘯,沙棘疾搖,鳥鳴幽幽。細(xì)聽中,所有的聲音都尖厲而短暫,平地而起,夾著風(fēng)沙,傳過來,有的還沒聽清楚,就瞬間消失了。
戈壁的聲音,和地理環(huán)境相關(guān)。緊鄰沙海,長(zhǎng)年干旱中落得一塊綠洲。四季中,冬長(zhǎng)夏短,風(fēng)沙頻顧,降水稀少,溫差巨大,并不適合動(dòng)植物生長(zhǎng)和棲息。然而,特殊的氣候也為當(dāng)?shù)氐娜藗兲峁┝藨T看“大漠沙如雪”的豪邁。
戈壁的聲音,使之真正成為戈壁。
在多年前一次敦煌旅行中,我得知有“陽(yáng)關(guān)三疊”這一曲調(diào),十分好奇。經(jīng)講解才得知,詞曲是根據(jù)唐代詩(shī)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而寫的一首藝術(shù)歌曲,唱詞中有青柳、霜雨、城郭、離人、幽夜、感傷和思念……
大漠孤城上響起的幽幽羌笛聲。笛聲響過盈盈冷月,響過萬仞群山,響過千秋百代,心情是黯然的吧,柳色應(yīng)該還沒綠,將軍白發(fā)征夫淚。
曠野上牧羊人清脆的鞭哨聲。趕一陣子羊群,“啪啪啪”,羊鞭一長(zhǎng)兩短。只聽近旁的老農(nóng)說:“看你的羊一個(gè)個(gè)膘肥體壯,今年準(zhǔn)能賣個(gè)好價(jià)!”牧羊人沒應(yīng)答,接著又是兩記響鞭,聆聽中,動(dòng)感十足,響徹田野。
秋天沙棗紅了,在林間灑落下一片,分外惹眼。有小孩子放學(xué)經(jīng)過看見,呼朋引伴前來一陣哄搶,待吃飽裝滿后,隨后“咯咯”笑著離去,聲音悅耳得像灑落在田野上的音符。
這些聲音,每一個(gè)都隨處可見但有各具特色。
例如琵琶,如今蹤跡難覓,如果不是有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唐詩(shī)在眾多邊塞詩(shī)中獨(dú)樹一幟,歷經(jīng)朝代更替流傳下來,這種極具地域文化的樂器也將銷聲匿跡。
看似唾手可得,實(shí)則眾里難尋。如羌笛聲,只有遇到當(dāng)?shù)嘏e行重大旅游活動(dòng),方可一覽“真容”;牧羊人的鞭哨聲也幾近消失,因近幾年經(jīng)濟(jì)發(fā)展迅猛,偌大片牧場(chǎng),已被開墾殆盡,難以見到一個(gè)牧羊人……
聲音,是一種天籟,是承載想象的翅膀。揮動(dòng)著這翅膀,人們穿越種族,穿越時(shí)間,與自然和歷史同在。在它的疆域里,戈壁的聲音最獨(dú)具特色,最深邃宏遠(yuǎn),最耐人尋味,因?yàn)樗坏w了古詩(shī)詞、古建筑、古人文,還容納了現(xiàn)代民俗的一些元素。
“有一些文物,包括樂器,詞曲,詩(shī)賦,由于各種原因,有的已失傳,有的甚至絕跡。”是的,這些戈壁的聲音,實(shí)則很普通,很渺小,細(xì)微到都不足以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和重視。它們默默的產(chǎn)生,默默的消亡,正如產(chǎn)生它們的歷史和人群,正如與它們相伴相隨,并且終將隨著荒漠化的侵襲而摒棄的環(huán)境。
然而,當(dāng)它們真的消失,歷史也將殘缺不全。也許,這些曾經(jīng)和正在發(fā)生的聲音,都已歸還給了大自然,亙古無聲地滋養(yǎng)著戈壁的靜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