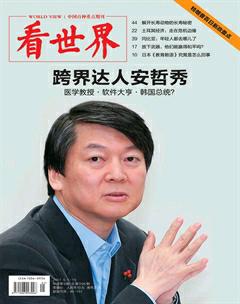放下武器,他們能贏得和平嗎?
胡安·莫雷諾
五十年來,哥倫比亞反政府武裝“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一直在叢林中與政府軍作戰。如今,FARC終于決定放下武器,哥倫比亞政府正試圖將這些戰士改造成普通公民。但對許多戰士來說,改變或許比戰爭更可怕。
每天早上10點一到,叢林中部的發電機準時啟動,前游擊隊員們連上了互聯網。哥倫比亞政府架起衛星天線,是為了將這些曾經的戰士們拉回現代世界:過去幾十年里,這些人從未接觸過網絡或電話,完全和現代文明隔離,就像未開化的土著一樣。當然,兩者之間唯一的區別是前者時不時被大火、陷阱和雷區包圍。
衛星接收器上的小燈開始閃爍,表示WiFi已經連通,戰士們可以開始刷臉書、發推特或者上YouTube看視頻。沒多久,他們就上癮了。要知道僅僅一個月前,他們還在溫度34攝氏度、濕度100%的叢林中打仗,不知道谷歌為何物。
哥倫比亞政府已經與FARC達成和平協議,游擊隊員們不再需要參加軍事演習。他們躺在木屋里,手中玩著政府贈送的二手車模。在以前的生活中,手機是一個禁忌,因為FARC擔心政府軍借此跟蹤他們。如今,他們盯著手中的新設備,學習如何給蕾哈娜(美國知名女歌手)的視頻點贊,以及在臉書上交新朋友。這是回歸普通生活的第一步。

“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戰士在叢林中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哥倫比亞正在進行一個獨特的實驗,一個大膽的和平計劃,旨在抹去其血腥的過去。這是一個馴化的過程——將野蠻的戰士變成負責任的公民。為此,全國各地的FARC士兵們都進入了再教育營。本文提及的再教育營位于哥倫比亞南部,與厄瓜多爾接壤,面積大致和一個足球場一樣大。那里聚集著80名前游擊隊員,包括爆破專家、狙擊手、偵察專家和酷刑專家。自孩童時代開始,他們就作為FARC的隊員和政府軍進行斗爭。
直到不久前,卡齊卡·阿塔瓦爾帕和埃德溫·坎諾這樣的游擊隊員還是政府軍眼中的恐怖分子。如今,他們的存在制造除了一個新問題:這些過去的游擊隊戰士能否變成善良的平民?
選舉制度和避孕方法
第一步,是派專業援助人員進入叢林。現在,這個游擊隊營地里擠滿了醫生、護士、老師、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橡膠樹下支起了綠色的小帳篷,醫生在這里進行檢查,這些放下槍的戰士們患有各種疾病:椎間盤突出、骨關節炎、風濕病、傷寒、韌帶損傷、瘧疾等等。醫生們有時會懷疑,這樣病魔纏身的身體怎么能打仗?心理學家心中的疑問也不少,比如,一個戰士怎樣才能堅持從14歲打仗到50歲?
項目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在木頭搭建的教室里,教授的課程包括哥倫比亞的選舉制度、栽種土豆的最佳方式、雜志攝影以及避孕方法。
不上網的時候,游擊隊員們會聚集在大教室里。在他們面前,一個扎著辮子的農業專家在解釋土地耕種方法。“再過幾個月這一切都要結束了,”她說,“你們會上繳武器,開始自給自足的生活。”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歐洲環保人士天馬行空的計劃,但它卻是哥倫比亞目前唯一的選擇。
去年9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和平到來了。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桑托斯和FARC領導人蒂莫倫·吉米內斯站在卡塔赫納市一個舞臺上,互相握緊雙手,簽訂了一紙結束五十年戰爭的和約。桑托斯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桑托斯曾下令向叢林中投擲了無數炸彈;哥倫比亞檢察機關則指責吉米內斯應該為100多起謀殺案負責。
哥倫比亞政府和反政府武裝之間的斗爭始于1966年,是拉美時間跨度最長的游擊戰。統計數字顯示了這場戰爭的恐怖:500萬人流離失所,20萬人死亡,1萬人失蹤或被綁架。沖突并不限于哥倫比亞政府軍和FARC兩方,還涉及右翼準軍事人員、販毒集團以及其他犯罪集團。
但這是過去,現在是屬于和平和團結的年代。根據雙方達成的和平協議,近7000名FARC戰斗人員必須在2017年6月之前上繳武器。桑托斯向他們許諾大赦、政治參與權、向想回家的人提供幫助。其他承諾還包括即將進行的土地改革以及組建和平法庭和真相委員會。FARC將成為一個普通的政黨,曾經的叛軍將參加政治生活,其中一些人可能會成為民選議員。
“我們也是人”
剛滿50歲的鮑里斯·福雷羅長著一張榮譽戰士的臉,他并沒有為這個大團圓的結局做好準備。他穿著一套寬松的黑色西裝,服務員們從他身邊匆忙掠過。一個幫助前游擊隊員融入社會的政府機構在一家豪華酒店舉辦招待會,鮑里斯應邀在會上發言。
鮑里斯過去曾是FARC成員,幾年前離開了。他告訴聽眾他的經歷:“如果我有什么要告訴你,那就是,”他說,“我們也是人。”
觀眾由公司代表組成,所有人都穿著西裝。他們不是公司的高層,可能是遵從老板的命令參加而已。政府想說服與會者為游擊隊員們提供工作,各公司雖然承諾考慮,但也有人公開表示,不知道怎樣開除一個在睡夢中都能組裝好一支槍的員工。
鮑里斯作為游擊隊員,打了近20年仗,受過幾次傷。有些時候,對于自己為何而戰他感到迷茫。11年前,他回到社會中,開始學習心理學。現在,他偶爾會代表這家機構與FARC的逃兵們對話,向他們解釋和平意味著什么。
“戰爭是你生活的全部,我猶豫了5年,終于還是離開了,”他說,“FARC是一個奇怪的團體,但對大多數游擊隊員來說,這是唯一一個類似家庭的存在。”
“每個人都有疤痕”
埃德溫是一個害羞的男人。他躺在庇護所的木板房里,向手機中保存的三個號碼發送表情。一名社會工作者曾問30歲的埃德溫以后想做什么,他說,有人說他可以當攝影師。“但不是我決定自己能否會成為攝影師,這得聽FARC領導的。”
埃德溫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和平計劃意味著FARC的消失,游擊隊員們以后可以自由地做他們喜歡的事。對埃德溫來說,這就意味著,他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做攝影師。
埃德溫還是不能理解。游擊隊幾乎照顧了他一輩子:自13歲加入FARC后,FARC教會他讀寫,給他飯吃,給他衣服穿。埃德溫的父母是農民,因為養不起就把他送走了。
還沒到中午,鮑里斯依舊坐在豪華酒店里。會議已經結束,他沒有打算做什么,明天也沒有任何日程。“FARC的集體生活意味著很多決定不需要你做主,”他說,“錯誤的決定會產生后果,你知道這點,但得忍著,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了。”
自鮑里斯離開戰場后,他的神經一直處于抽搐狀態,雙手停不下來,總是揉手指或者刮臉。“每個人都有疤痕,一些你看得到,一些你看不到。”他說。鮑里斯有兩個疤痕——一個在手臂,一個在背部,看起來像有人用刀具切掉了一塊肉,實際上是炸彈爆炸留下來的傷痕。
未受損的毒品行業
戰爭就像一個引擎,需要燃料。仇恨是最好的武器,但隨著時間推移,它會失去力量。唯一能讓戰爭持續的是金錢。對FARC的戰爭可能結束了,但只要美國和歐洲的毒品市場仍需要可卡因,毒品戰爭舊將繼續下去。
FARC自稱為“自由戰士”,用理想包裝自己。但事實上,他們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毒品集團之一,控制著哥倫比亞60%左右的毒品交易,每年至少可以掙10億美元。歐盟將該集團列為恐怖組織。
如果FARC放棄了這筆錢,其他團體肯定會伺機進入。最近,不想成為公車司機、失業攝影師或農民的FARC游擊隊員已經開始轉移。墨西哥販毒組織在哥倫比亞日益活躍,他們用現金而不是理想來召喚追隨者。
叢林中可能還有另一個雇主,即所謂的民族解放軍,也就是ELN。該組織可以說是FARC的姐妹團體。政府目前正在和ELN談判,迄今尚未成功,因為ELN的所有成員都清楚:ELN可以占領FARC丟棄的地盤,而對普通生活不感興趣的FARC游擊隊員們也可以在ELN那里找到新家園。
在新的和平協議下,哥倫比亞的可卡因行業并未受損。據專家估計,自2015年以來,哥倫比亞的可卡因供應量已經上升了三分之一,達到每年710噸。

卡齊卡·阿塔瓦爾帕(左)和丈夫拉米羅·杜恩
卡齊卡想回到孩子身邊
不過,和平確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說熱乎乎的一日三餐,以及星期日的音樂會。卡齊卡·阿塔瓦爾帕是一個長著黑眼睛的迷人女子,是少數為和平雀躍的FARC游擊隊員。她的丈夫拉米羅·杜恩目前是該組織的“宣傳部長”。
卡齊卡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說,營地學習結束后,她就會回到孩子身邊。目前,孩子們和拉米羅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兒子何塞7歲,卡齊卡自孩子出生后就沒見過他。第二個孩子只有幾個月大。她懷著第二個孩子時就知道FARC不會存在太久了。
“只要是游擊隊的成員就不可以有孩子,所以一開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懷孕6個月時,我還在參與作戰行動,”她說,“當同事們發現我懷孕在身時,他們很生氣。后來我早產了,他們不得不把我帶到一家醫院,3個隊員死在路上。”
FARC制定了規則,如果兩名戰士開始談戀愛,必須向上級報告。沒有上級的許可,戰士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吸煙,甚至不能暗戀誰。剛開始,他們只允許卡齊卡和拉米羅在一起待兩小時。卡齊卡說,一個簡單的調令,就可以讓同居多年的夫妻天人永隔。
卡齊卡想過成為一名護士。她的丈夫拉米羅在2001年加入FARC之前,曾在波哥大學習了4個學期的法律,他將來可能會從政。他的父母在太平洋沿岸有一個度假屋,每次陷入戰火時,他就會向卡齊卡講講那個度假屋。“我想去看看。”她說。
曾經是叛徒,永遠是叛徒
未來,鮑里斯·福雷羅可能不會經常出現在豪華酒店。他無法找到心理學家的正式工作,而這個機構也不再需要他了。他的個人資料不符合要求。對于在和平協議達成之前從叢林中涌出的逃兵,他是一個完美的聯系人,因為他有著同樣的過去。但如今眼前的這些FARC戰士并不是逃兵,在他們眼里,鮑里斯是一個叛徒。“他們不會跟我說話,”鮑里斯說,因為他曾經是叛徒,永遠是叛徒,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后。
鮑里斯打算回到他那個偏僻、簡陋的公寓。鮑里斯認為,和平協議達成之后會有所不同,但不會那么艱難。和平年代里,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但沒有人照顧他。他需要錢才能活下去,需要一份工作,需要食物、電、天然氣、租金和衣服;甚至必須花錢才有人幫忙處理垃圾。
自鮑里斯生活在和平之中,幾乎沒有哪一天他不會想到戰爭。他并不想念戰爭本身,只是經常想到它令人愉悅的簡單和清晰。盡管士兵終將死去,但戰爭是有確定性的:黑即是黑,白即是白,而和平是灰色的。
鮑里斯迄今所經歷的和平比戰爭更加不安定,更令他困惑。鮑里斯說,有些日子更是困難重重。和平也是一場戰斗。它不再是每天生死攸關,而是關于過什么樣的生活以及這樣的生活值不值得繼續。
曾經,鮑里斯扛起槍,如今,他在尋找一份工作,確保自己能生存下去。對于許多哥倫比亞人來說,鮑里斯和其他前游擊隊員一樣,不過是叢林里的怪胎而已。數千名游擊隊員現在回歸社會,他們擺脫了戰爭,其中許多人卻也無法贏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