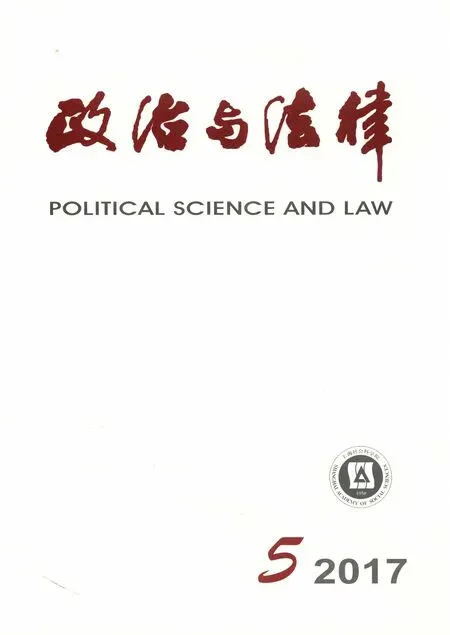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性質(zhì)*
張定淮 底高揚(yáng)
(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北武漢 430072)
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性質(zhì)*
張定淮 底高揚(yáng)
(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國兩制下研究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到底是什么性質(zhì)的授權(quán),實(shí)質(zhì)是探討香港高度自治與中央管治在授權(quán)場域中的特殊關(guān)系。準(zhǔn)確界定這種關(guān)系離不開對此種授權(quán)之歷史語境、現(xiàn)實(shí)語境和比較語境的全面剖析,其中的歷史語境包括授權(quán)環(huán)境、《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本質(zhì)及該聲明與香港基本法的關(guān)系等,現(xiàn)實(shí)語境包括我國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和香港高度自治與中央管治的互動結(jié)構(gòu)等,比較語境表現(xiàn)為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在我國授權(quán)譜系中的定位。在此基礎(chǔ)上,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可以從授權(quán)環(huán)境的雙重性、授權(quán)地位的超越性、授權(quán)變遷的復(fù)合性、授權(quán)效力的獨(dú)立性等基本維度進(jìn)行界定。
一國兩制;授權(quán);中央與香港的特殊關(guān)系
一、引言:探討中央與香港特殊關(guān)系的一個新視角
授權(quán)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高頻使用的一個法律概念。通說認(rèn)為基本法是一部授權(quán)法。*參見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香港基本法讀本》,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版,第40-42頁。許崇德先生指出基本法是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制定的特別授權(quán)法。參見許崇德主編:《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頁。授權(quán)對憲制的實(shí)施、完善和發(fā)展具有重要的試驗(yàn)性作用,正如施密特所說:“授權(quán)實(shí)踐既是憲法現(xiàn)狀的試金石,也是憲法總的發(fā)展趨勢的重要征兆。”*[德]卡爾·施密特:《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頁。基于此,授權(quán)問題是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與香港憲制關(guān)系的核心問題,是基本法的靈魂,應(yīng)當(dāng)?shù)玫綄W(xué)界的廣泛關(guān)注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與探討。
從現(xiàn)有的授權(quán)理論研究文獻(xiàn)來看,關(guān)于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授權(quán)概念的界定。主流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授權(quán)是指權(quán)力擁有者將其行使的權(quán)力授予被授權(quán)者,而使被授權(quán)者得以行使授權(quán)者權(quán)力的單方處置行為。*董立坤:《中央管治權(quán)與香港高度自治權(quán)的關(guān)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頁。而有的學(xué)者將授權(quán)的內(nèi)涵理解為一個法律概念、一種法律理念、一項(xiàng)法律制度和一種法律關(guān)系。*鄒平學(xué)等:《香港基本法實(shí)踐問題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頁。還有的學(xué)者在區(qū)分了四種語境(君權(quán)神授與人民主權(quán)授權(quán)理論、單一制下中央對地方的權(quán)力授予、宗主國對殖民地總督的授權(quán)和某種具體權(quán)力的授權(quán))下授權(quán)概念的基礎(chǔ)上,認(rèn)為基本法中存在兩種授權(quán)概念:憲法與法律等規(guī)范性文件對某個主體的權(quán)力賦予(第一次授權(quán));已經(jīng)擁有某種權(quán)力的機(jī)構(gòu)再將法律賦予自己行使的權(quán)力授權(quán)給其他機(jī)構(gòu)來行使(第二次授權(quán))。*參見王禹:《港澳基本法中有關(guān)授權(quán)的概念辨析》,《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9期。第二,授權(quán)的本質(zhì)。*蘇樂治教授總結(jié)了行政法上關(guān)于授權(quán)性質(zhì)之理論上的三種學(xué)說:轉(zhuǎn)移和轉(zhuǎn)讓說;許可說;實(shí)施轉(zhuǎn)移說。參見[葡]蘇樂治:《行政法》,馮文莊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27頁。這里的授權(quán)性質(zhì),根據(jù)原文語境應(yīng)指授權(quán)的本質(zhì),即授權(quán)的本體意義。目前我國學(xué)界對此主要有兩種觀點(diǎn)。一種觀點(diǎn)為權(quán)力本身轉(zhuǎn)移說,其認(rèn)為授權(quán)的本質(zhì)是某種國家權(quán)力在授權(quán)主體與被授權(quán)主體之間依照一定的原則和程序進(jìn)行的轉(zhuǎn)移。*參見李元起:《澳門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quán)性質(zhì)和特點(diǎn)初探》,載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編著:《記念澳門基本法實(shí)施10周年文集》,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頁。另一種觀點(diǎn)為權(quán)力行使轉(zhuǎn)移說,其從反向進(jìn)行證成,認(rèn)為如果單一制下的授權(quán)為權(quán)力本身的轉(zhuǎn)移,則中央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收回授權(quán),能否收回須取決于地方是否同意,這與單一制國家理論與實(shí)踐相悖逆。*參見王禹:《“一國兩制”架構(gòu)下的授權(quán)理論研究》,《港澳研究》2013年春季號。第三,授權(quán)的本體要素。*參見上注,王禹文;鄒平學(xué)等:《香港基本法實(shí)踐問題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3頁;黃振:《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quán)研究》,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9頁。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授權(quán)主體、授權(quán)客體、授權(quán)內(nèi)容或范圍、授權(quán)形式等。第四,授權(quán)的具體類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郭天武教授將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分為無須中央政府進(jìn)一步授權(quán)的權(quán)力、需要中央政府具體授權(quán)的權(quán)力和中央政府可能授予的其他權(quán)力等。*郭天武、陳雪珍:《論中央授權(quán)與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當(dāng)代港澳研究》2010年第2期。第五,有關(guān)授權(quán)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授權(quán)的基本原則,授權(quán)監(jiān)督,授權(quán)變更、取消、續(xù)期,等等。*參見前注⑨,黃振書,第58-62頁;張定淮:《為什么中央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權(quán)具有監(jiān)督權(quán)》,《紫荊》2014年7月號;潘俊強(qiáng):《論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quán)的法理基礎(chǔ)》,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2011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85-87頁;程潔:《中央管治權(quán)與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規(guī)定的授權(quán)關(guān)系為框架》,《法學(xué)》2007年第8期;董立坤:《中央管治權(quán)與香港高度自治權(quán)的關(guān)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8頁;王禹:《“一國兩制”架構(gòu)下的授權(quán)理論研究》,《港澳研究》2013年春季號。
從總體上看,盡管專門研究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問題的文獻(xiàn)不多,但其已初步型構(gòu)了授權(quán)理論在香港問題上的適用框架,為認(rèn)知香港政府的權(quán)力來源、明確香港的憲制地位和勾畫香港未來權(quán)力圖譜提供了理據(jù)。然而,檢視以往的授權(quán)研究成果也可以發(fā)現(xiàn),多年來,授權(quán)理論的推進(jìn)是很緩慢的,其中,對中央與香港的關(guān)系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治層面的府際關(guān)系理論,沒有在“授權(quán)”這一研究兩者關(guān)系的重要紐帶上尋求新的突破口,這就不僅導(dǎo)致了研究視野狹隘、逼仄,而且使這些研究成果難以為今后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實(shí)踐發(fā)展提供理論指引。筆者認(rèn)為,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難以用一個或兩個詞語予以高度概括,基于授權(quán)將中央與香港在法律或政治層面統(tǒng)一起來,因此,研究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到底是什么性質(zhì)的授權(quán),實(shí)質(zhì)就是探討在授權(quán)場域中兩者特殊關(guān)系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研究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對于香港政治與憲制轉(zhuǎn)型前景和避免未來香港高度自治發(fā)展陷入不確定性具有基礎(chǔ)性和前瞻性的意義。基于此,筆者在本文中主要從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對該授權(quán)性質(zhì)展開研究。第一,在歷史語境中,中央與香港的特殊關(guān)系在授權(quán)場域中是如何型構(gòu)的?英國是否基于與授權(quán)密切相關(guān)的《中英聯(lián)合聲明》而可以介入這種特殊關(guān)系,從而使其演變成一種國際化關(guān)系?第二,在現(xiàn)實(shí)語境中,我國目前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是如何影響中央與香港的特殊授權(quán)關(guān)系的?該關(guān)系在中央管治與香港高度自治的互動結(jié)構(gòu)中是如何變遷的?第三,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在我國的授權(quán)譜系中如何定位?
二、正視《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歷史語境
(一)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環(huán)境分析
一般來講,授權(quán)是國家為了滿足地方發(fā)展的實(shí)際需求和國家分區(qū)治理效果與方便而許可地方行政區(qū)域在某些事務(wù)領(lǐng)域行使國家權(quán)力。這種授權(quán)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地方層面治理需要和中央層面的國家意志,筆者稱之為自主性授權(quán);而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不同于普通的府際關(guān)系,其有著特殊的國內(nèi)外環(huán)境。
從外部環(huán)境上講,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歷史上被英國通過三個不平等的條約侵占。為了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完成祖國領(lǐng)土完整、主權(quán)統(tǒng)一大業(yè),中方同英方開展了22次艱苦卓絕的外交談判斗爭。*參見前注①,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書,第13頁。在堅(jiān)持中國對香港完整地行使主權(quán)這一原則下,中方認(rèn)為可以在香港管治方面作相對靈活的特殊政策安排。基于這種立場,為了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收回香港主權(quán)的決心、誠意,同時為了向英方爭取更大的談判主動權(quán),中方承諾在香港實(shí)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這些基本方針政策最終體現(xiàn)在《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中。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央向香港授權(quán)是追求主權(quán)回歸這一最高國家利益而向英國作出的外交妥協(xié)。從內(nèi)部環(huán)境來看,內(nèi)地與香港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生活思維方式等,就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程度而言,香港總體上優(yōu)于內(nèi)地。客觀地講,在香港回歸祖國后的較長時間里,中央管治能力還難以匹配香港社會發(fā)展現(xiàn)狀與需求,難以負(fù)擔(dān)中央對香港地方的政治責(zé)任,為了避免香港主權(quán)回歸的“硬著陸”給香港繁榮穩(wěn)定帶來不可預(yù)測的沖擊風(fēng)險(xiǎn),同時,為了繼續(xù)保持香港發(fā)展的活力以及發(fā)揮香港地方在全國一盤棋中的先鋒引領(lǐng)、改革試驗(yàn)功能,中央對香港地方作出了不同于對普通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授權(quán),給予香港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高度自治權(quán)。基于當(dāng)時的歷史語境判斷,筆者認(rèn)為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內(nèi)部和外部壓力主要來自中央自身意志之外,且外部壓力大于內(nèi)部壓力,*歷史地看,地緣政治秩序永遠(yuǎn)是第一秩序,而國內(nèi)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后者要適應(yīng)前者,否則后者就很難獲得生存與發(fā)展的能力;一旦前者受到后者的挑戰(zhàn),那么前者背后的政治力量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資源來保護(hù)這個秩序。香港問題是近代地緣政治變遷的產(chǎn)物,且其內(nèi)部秩序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的延伸。參見鄭永年、楊麗君:《臺灣和香港問題演變成國際化問題》,《經(jīng)濟(jì)導(dǎo)論》2016年第5期。另外,針對“一國兩制”的初步構(gòu)想,當(dāng)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調(diào)動整個國際輿論來對中國政府施壓,而那時國際輿論是一邊倒的。參見《魯平口述香港回歸》,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44頁。可以說,在當(dāng)時的歷史語境下,國際壓力在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上起了更大的倒逼作用。凸顯了中央在授權(quán)方面的被動性,其內(nèi)在蘊(yùn)含的授權(quán)邏輯迥異于、更復(fù)雜于中央對其他地方的授權(quán),鑒于此,我們稱此授權(quán)為“壓力性授權(quán)”。
(二)《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本質(zhì)
在香港問題談判時,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主要內(nèi)容最初由《中英聯(lián)合聲明》予以確認(rèn),這是中英兩國政府針對香港前途向全世界公開簽署的一份文件。關(guān)于其本質(zhì),歷來存在爭議,主要焦點(diǎn)在于其是否為國際協(xié)議或國際條約,而這個焦點(diǎn)在授權(quán)場域中的實(shí)質(zhì)在于,英國以及其他第三方國際社會主體是否依據(jù)該聲明獲得對中國是否實(shí)施承諾的授權(quán)以及對授權(quán)的改變進(jìn)行監(jiān)督的權(quán)力。
英國政府在中英草簽《中英聯(lián)合聲明》之前為了咨詢香港市民的意見而發(fā)表的白皮書認(rèn)為,該聲明是“一項(xiàng)雙方同意且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xié)議”。英國外相杰弗里·豪稱該協(xié)議在“國際法”上是有約束性的。*參見鄭宇碩:《從國家法觀點(diǎn)評析中英聯(lián)合聲明》,《法學(xué)評論》1988年第4期。在我國相關(guān)研究中,亦不乏將該聲明視為國際條約的文獻(xiàn)。*參見龐嘉穎:《一國兩制與澳門治理民主化》,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頁;姚魏:《特別行政區(qū)對外交往權(quán)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8頁。然而,通過歷史語境主義考察,筆者認(rèn)為將該聲明簡單視為國際條約是不妥當(dāng)?shù)模?“歷史語境主義”是一種研究政治思想的方法論,其主張對以文本或話語為載體的政治思想的研究要由哲學(xué)闡釋轉(zhuǎn)向歷史解讀,由只關(guān)注經(jīng)典文本轉(zhuǎn)向關(guān)注經(jīng)典產(chǎn)生語言語境、思想語境和社會政治語境。參見羅雪飛:《從哲學(xué)中拯救歷史——論昆廷·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云南社會科學(xué)》2015年第3期。理由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從其語言方面考察,該聲明不具備國際條約的形式要件。從文本語言來看,中英雙方各自公布的聲明名稱差異較大,*關(guān)于它的名稱,英方采用的詞匯為協(xié)議(agreement),而中方的用語為聯(lián)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且除第8款的助動詞使用“Shall”以外,其他條款均為“Will”,這意味著聲明中的行動是各自宣布準(zhǔn)備做的事情,*參見過家鼎:《〈中英關(guān)于香港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翻譯中的政治考慮》,《上海翻譯》2005年第2期。反映了一種中英雙方確定自然要發(fā)生的事實(shí),缺少國際條約所具有的剛性屬性。第二,從其內(nèi)容方面來看,該聲明不具備國際條約的實(shí)質(zhì)要件。中英聯(lián)合聲明是不是有約束性的條約,并不在乎它的名稱,而是決定于它的內(nèi)容以及內(nèi)容所反映的雙方的意圖。*參見陳弘毅:《香港法制與基本法》,廣角鏡出版社1986年版(香港),第74-80頁。考察聲明原文,筆者發(fā)現(xiàn)其存在大量不確定概念,雙方對待這些內(nèi)容的模糊態(tài)度難以反映國際條約的合意性;其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包括單方聲明和共同聲明,其中單方聲明的內(nèi)容卻存在很大差異甚至矛盾,*比如,第1條中方單方聲明使用了“對香港恢復(fù)行使主權(quán)”,而第2條英方單方聲明卻用“將香港交還給中國”。從香港主權(quán)背后的歷史語境分析,第1條確認(rèn)了中方一直擁有對香港的主權(quán),而第2條表達(dá)出了英方依“條約有效論”曾獲得對于香港的主權(quán)的觀點(diǎn)。這不符合條約一致性的要求。另外,盡管該聲明第7款即聯(lián)系條款(linking clause)將上述聲明統(tǒng)一起來,實(shí)現(xiàn)了中英雙方的互相承諾,但缺乏必要的強(qiáng)制機(jī)制,凸顯了聲明內(nèi)容的陳述性,即僅表示對某些問題的共同態(tài)度或政策,其不具有義務(wù)性質(zhì)。第三,從其社會政治語境變遷來講,《中英聯(lián)合聲明》除第3條第12項(xiàng)(即關(guān)于“50年不變”的規(guī)定)均已完成歷史使命,香港社會整體經(jīng)由過渡期逐漸從依賴英國管治轉(zhuǎn)向中央授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從主權(quán)角度講,自中央恢復(fù)行使香港主權(quán)后,包括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事務(wù)等在內(nèi)的中央和香港關(guān)系均屬于中國內(nèi)政事項(xiàng),按照國際法一般原則,該聲明應(yīng)持尊重而非干涉態(tài)度,況且基本法已深入人心,成為香港高度自治的法律依據(jù)和路徑依賴。
綜上,筆者認(rèn)為《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不是一項(xiàng)國際條約,其本質(zhì)為記錄歷史事實(shí)的政策宣示性文件,故英國沒有介入中央與香港特殊關(guān)系的空間和依據(jù),中央與香港的關(guān)系并沒有引入國際因素而成為國際化關(guān)系,其仍然是中央與其地方的關(guān)系。同時,基于主權(quán)原則,中央出于保持香港繁榮穩(wěn)定之目的對香港的授權(quán)完全屬于中國的內(nèi)政事務(wù),包括英方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均不具有干預(yù)的監(jiān)督力和強(qiáng)制力。盡管如此,在今天,每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與其他國家進(jìn)行交往與合作,信譽(yù)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立足的基石,每個國家需要建立和維持自己的國際信譽(yù)。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一份面向全世界的承諾,對其違反將使中國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從而在對臺政策等類似事務(wù)中失去相關(guān)“國際話語權(quán)”,因此需要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予以對待。
(三)《中英聯(lián)合聲明》與基本法的關(guān)系
通說認(rèn)為,依基本法序言第3段的規(guī)定,基本法是一部全國人大依據(jù)我國《憲法》整體而非其第31條制定的國內(nèi)基本法律,這一定位直接否定了《中英聯(lián)合聲明》是其制定之法律依據(jù)的認(rèn)知,即并不存在《中英聯(lián)合聲明》相對基本法擁有更高位階法律效力的問題。那么《中英聯(lián)合聲明》與基本法的關(guān)系如何定位呢?
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中英聯(lián)合聲明》是制定基本法的政策依據(jù)。*參見肖蔚云:《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288頁;宋小莊:《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關(guān)系》,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9/22/c_128254959.htm,2016年11月2日訪問。筆者認(rèn)為這是不妥的。一方面,該聲明由中英各單方聲明和共同聲明組成,涉及英方聲明的部分是國外文件內(nèi)容,基于主權(quán)原則,其不能夠直接作為我國國內(nèi)法律和政策制定的依據(jù)。另一方面,雖然不同政策之間存在位階,但是這一關(guān)系發(fā)生在縱向權(quán)力序列中,具體到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它們均是中央的意志,只是所呈現(xiàn)的載體不同而已。盡管載體背后所表達(dá)的政治意圖存在差異,但這些方針政策本身沒有依據(jù)和被依據(jù)的關(guān)系。正如饒戈平教授所言:“顯然,中國有政策在先,有國家意志和憲法在先,然后才出現(xiàn)對香港回歸后法律地位的國際承諾;基本法是以中國憲法和對港政策為依據(jù)而不是僅僅出于中國在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中承擔(dān)的國際義務(wù)來制定的,這才是《中英聯(lián)合聲明》和基本法之間真實(shí)的實(shí)質(zhì)性的邏輯聯(lián)系。”*饒戈平主編:《燕園論道看港澳》,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中英聯(lián)合聲明》既不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jù),也不是政策依據(jù),那么其對基本法的修改有無制約作用?筆者認(rèn)為,“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shí)施”是制定基本法的目的,同時,基本法第159條第4款規(guī)定了“修改不抵觸原則”,這些方針政策已在《中英聯(lián)合聲明》附件一載明。然而,“修改不抵觸”的對象是基本方針政策本身,而不是其載體——《中英聯(lián)合聲明》。基于前面的分析,筆者認(rèn)為《中英聯(lián)合聲明》僅僅是一份面向國際記錄史實(shí)的政策宣示性文件,而基本法是中方兌現(xiàn)《中英聯(lián)合聲明》第3條第12項(xiàng)承諾的具體行動,從功能主義視角來看,該聲明充其量只是制定基本法的材料來源,其對基本法如何制定、具體內(nèi)容的設(shè)定等沒有直接的強(qiáng)制約束力。當(dāng)然,香港回歸后,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屬于主權(quán)事項(xiàng),包括英方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應(yīng)當(dāng)予以尊重,決不產(chǎn)生基于《中英聯(lián)合聲明》而獲得干涉包括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等香港事務(wù)在內(nèi)的“長臂延伸力”的效果,也就是說,只要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措施、基本法的修改符合既定基本方針政策的基本精神,已完成歷史使命的《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不具有制約中央對港政策、基本法修改的法律效力。
三、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現(xiàn)實(shí)語境
分析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不僅要關(guān)注授權(quán)的歷史語境,在歷史環(huán)境中界定中央授權(quán)與其他因素的關(guān)系,更要關(guān)注授權(quán)的現(xiàn)實(shí)語境,從國情等實(shí)際環(huán)境中深度挖掘中央與香港在授權(quán)場域中的特殊關(guān)系。筆者擬從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香港與中央特殊互動結(jié)構(gòu)兩個方面對授權(quán)性質(zhì)進(jìn)行剖析。
(一)我國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對授權(quán)的影響
理論上講,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對授權(quán)的影響是顯著的,聯(lián)邦制遵循著從地方州到聯(lián)邦中央的授權(quán)邏輯,而單一制的授權(quán)邏輯沿著中央到地方的向度展開。通說認(rèn)為,我國憲法從“中央以法律授予地方權(quán)力”、“中央對地方享有完全監(jiān)督權(quán)”、“地方?jīng)]有制憲權(quán)”和“地方不享有中央?yún)⒄?quán)”等方面對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予以了確認(rèn)。*我國單一制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可由我國憲法第2條、第3條、第31條、第57條、第58條、第62條、第85條、第96條、第105條、第115條、第127條、第132條等從上述四個方面進(jìn)行證成。參見王磊:《論我國單一制的法的內(nèi)涵》,《中外法學(xué)》1997年第6期。因此,從國家權(quán)力的來源、地方是否分享有制憲修憲的動議與批準(zhǔn)權(quán)、基本法與憲法關(guān)系以及基本法的性質(zhì)、中央政府與特別行政區(qū)之間劃分管理事權(quán)的方式等方面可以明確中央對香港的單一制授權(quán)屬性。*參見杜承銘:《論特別行政區(qū)的授權(quán)性地方自治性質(zhì)及其授權(quán)機(jī)理》,《暨南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第6期。
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上,這個在理論上被抽象為“金字塔”狀的“純粹”授權(quán)式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參見張穎:《構(gòu)建單一制國家:“單一制例外”的歷史整合》,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卻在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實(shí)踐中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傾向,致使我國傳統(tǒng)單一制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在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無序化的風(fēng)險(xiǎn)。這其中有一種聲音值得重視: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統(tǒng)一主權(quán)的內(nèi)部分離,從而形成一種帶有“聯(lián)邦制”印痕的復(fù)合單一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筆者認(rèn)為,這種觀點(diǎn)(或類似觀點(diǎn))是不正確的,甚至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港獨(dú)”法理背書,打開分裂香港的“潘多拉盒子”。眾所周知,香港自古是中國固有領(lǐng)土的一部分,是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qū)域,無論在地理還是時間上從來都不是一個獨(dú)立或半獨(dú)立的政治實(shí)體。盡管我國實(shí)施“一國兩制”基本國策,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quán),尤其是司法終審權(quán),但是中央授權(quán)香港并非聯(lián)邦制國家分權(quán)所實(shí)施的制憲行為,而是中央在現(xiàn)有憲法框架下運(yùn)作管治權(quán)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換言之,香港獲得的授權(quán)并非制憲權(quán)本源性地直接賦予的地方分權(quán),而是中央基于嫁接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進(jìn)行優(yōu)勢互補(bǔ)的實(shí)用主義思路與香港推動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體制變遷和博弈的縮影。實(shí)質(zhì)上,香港的授權(quán)實(shí)踐是中央政權(quán)在授權(quán)邏輯中充分實(shí)踐理性構(gòu)建主義基礎(chǔ)上而實(shí)現(xiàn)的一種整合式的妥協(xié),從而達(dá)到一種國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秩序——“非一種從外部強(qiáng)加給社會的壓力,而是一種從內(nèi)部建立起來的平衡”。*[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鄧正來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83頁。因此,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在我國復(fù)雜單一制國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下的特殊安排,是國家統(tǒng)一主權(quán)框架下特殊價值追求,根本上迥異于聯(lián)邦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王禹教授批判性地分析了現(xiàn)有的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理論,認(rèn)為單一制分為簡單單一制、復(fù)雜單一制和復(fù)合單一制三類,而“一國兩制”下的我國單一制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為復(fù)雜單一制。參見王禹:《“一國兩制”憲法精神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9頁。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高度自治與中央管治的互動結(jié)構(gòu)


四、我國中央對地方的授權(quán)譜系: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的比較語境
在地方分權(quán)和自治改革理念全球化推進(jìn)背景下,尤其是隨著我國地方民主改革趨勢的發(fā)展,我國中央政權(quán)以憲法、法律、法規(guī)及政策等形式漸次地把部分社會公共事務(wù)管理權(quán)等賦予給地方區(qū)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央對地方的授權(quán)譜系(如表1所示)。*以特殊程度為標(biāo)準(zhǔn),筆者于本文中將我國地方區(qū)域大體劃分為普通行政區(qū)、民族自治區(qū)域和特別行政區(qū)。其中,由于經(jīng)濟(jì)特區(qū)僅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獲得中央特殊安排,其特殊程度維度比較單一,筆者于本文中將其納入普通行政區(qū)范疇,不再單獨(dú)設(shè)項(xiàng)論述。通過比較,筆者認(rèn)為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政策性、法律性授權(quán),是一種復(fù)合型超越性授權(quán)。
表1 我國中央對地方的授權(quán)譜系

(一)中央對地方普通行政區(qū)的政策性授權(quán)
多層科層結(jié)構(gòu)是中國政府組織的重要特點(diǎn),*梁平漢:《多層科層中的最優(yōu)序貫授權(quán)與“一刀切”政策》,《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13年第1期。這一點(diǎn)也反映在我國憲法第30條關(guān)于行政區(qū)域的劃分條款中,同時,鑒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差異懸殊,中央政權(quán)不可能對地方采取“一刀切”控制機(jī)制,其為了貫徹、實(shí)施和實(shí)現(xiàn)中央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等領(lǐng)域的意志,且將相應(yīng)風(fēng)險(xiǎn)厘定在可控范圍,一般采取“試點(diǎn)”等政策性授權(quán)機(jī)制。
從歷史來看,我國積累了大量的政策性授權(quán)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如2016年,國務(wù)院同意浙江省開展國家標(biāo)準(zhǔn)化綜合改革試點(diǎn)工作、國務(wù)院批復(fù)北京市開展公共服務(wù)類建設(shè)項(xiàng)目投資審批改革試點(diǎn);2015年,國務(wù)院同意在上海等9個城市開展國內(nèi)貿(mào)易流通體制改革發(fā)展綜合試點(diǎn);2000年,國務(wù)院授權(quán)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審批設(shè)立高等職業(yè)學(xué)校等。在北大法寶“檢索”輸入“授權(quán)”、“試點(diǎn)”等關(guān)鍵詞,可獲得近百項(xiàng)中央對地方的政策性授權(quán)文件。其邏輯經(jīng)歷了從政治精英的理性框架到央地互動的民主政治框架的變遷,為探索和平衡新型央地權(quán)力關(guān)系提供了重要途徑。歸納這些政策性授權(quán),筆者總結(jié)出其以下特質(zhì)。第一,相關(guān)事項(xiàng)屬于行政管理范疇,多集中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保障等領(lǐng)域。經(jīng)濟(jì)、社會領(lǐng)域關(guān)乎百姓安居樂業(yè)、社會和諧穩(wěn)定、國家長治久安,其改革措施必須采取穩(wěn)妥、漸進(jìn)原則,防止出現(xiàn)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xiǎn)。第二,中央與地方是一種府際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比較剛性的、直接的“主體—客體”模式,遵循嚴(yán)格的科層制倫理。從功能主義角度而言,地方是中央的“試驗(yàn)田”,中央通過對地方的政策性授權(quán)為其國家均衡性治理決策提供“內(nèi)容供給”。在這種語境下,地方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安排。第三,穩(wěn)定性較差。政策性授權(quán)具有比較明顯的時效性,其隨行政或執(zhí)政周期的更替在形式和內(nèi)容上發(fā)生著變化,難以保障其在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維度的連續(xù)和承繼。第四,法治性缺位。政策性授權(quán)的比較優(yōu)勢在于其靈活性、能動性,一般不考慮法律規(guī)范上的實(shí)體和程序約束,但在依法治國背景下,這也產(chǎn)生了合法性困境:不僅缺乏法律依據(jù),無法滿足形式法治要求,而且在首長負(fù)責(zé)制下,其政治性思維與法治思維存在巨大的內(nèi)在張力,難以實(shí)現(xiàn)實(shí)質(zhì)法治。
(二)中央對地方普通行政區(qū)的法律性授權(quán)
法律性授權(quán)一般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決定等形式對地方普通行政區(qū)人大、政府作出的授權(quán),前者據(jù)此在不違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對相關(guān)事項(xiàng)進(jìn)行決策,后者據(jù)此開展具體授權(quán)工作。比如,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quán)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試點(diǎn)工作;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quán)部分地區(qū)開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diǎn)工作;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quán)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對設(shè)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xué)新校區(qū)實(shí)施管轄等等。
通過總結(jié)既有的法律性授權(quán)實(shí)踐,筆者認(rèn)為,中央對地方普通行政區(qū)的法律性授權(quán)具有以下特質(zhì)。首先,相關(guān)事項(xiàng)屬于法律保留或憲制性范疇。從以往實(shí)踐來看,我國中央對地方的法律性授權(quán)集中在司法制度、國家權(quán)力體制、法律實(shí)施等方面,而根據(jù)我國《立法法》第8條的規(guī)定,這些事項(xiàng)(除授權(quán)國務(wù)院制定行政法規(guī)外)只能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來實(shí)現(xiàn)。其次,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表現(xiàn)比較剛性的、間接的“主體—客體”模式。作為國家主權(quán)的代表者和行使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積極行使立法權(quán),使國家意志通過法定程序成為法律,而法律的不確定性又倒逼其不得不通過地方試點(diǎn)來降低由此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在這一過程中,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將自己的權(quán)力授予給地方單位,但地方不會直接獲得這種權(quán)力,而要依靠中央某機(jī)關(guān)或地方人大作為中介催化劑,從而助推完成相應(yīng)的憲制性改革活動。再次,法律性授權(quán)縮小了改革與現(xiàn)行法律、憲法間的鴻溝。突破性是改革的標(biāo)簽,而突破現(xiàn)行法律甚至憲法文本是改革一直面臨的詰問。“重大改革于法有據(jù)”的改革法治觀要求重大改革須法律先行,但法律的滯后性難以匹配改革的緊迫性,在這種情況下,由法律制定者先實(shí)施法律性授權(quán),使得改革具有形式合法性,再待條件成熟時制定或修改相應(yīng)的法律、憲法條款,從而完成改革與法律的互動。可以說,法律性授權(quán)將作為一種常態(tài)化機(jī)制,起到改革(尤其是體制性、綜合性改革)減震器的功能,這一功能特性使其不同于政策性授權(quán)。
(三)中央對民族自治區(qū)域的法律吸收政策型授權(quán)
民族區(qū)域自治是中央政權(quán)為解決民族問題而選擇的基本政治制度,但這一選擇經(jīng)歷了“機(jī)械照搬聯(lián)邦制的萌芽階段、聯(lián)邦制和區(qū)域自治制相結(jié)合的探索階段、民族區(qū)域自治逐漸定位階段”的長期過程。*易清:《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形成的歷史軌跡新探》,《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科版)》2004年第5期。歷史地看,執(zhí)政黨從建黨初期就提出“民族自決”的綱領(lǐng)性口號*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提出的“民族自決”指的是“中國之內(nèi)”的各民族自決,而不是“脫離中國”的自決。參見《惲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7頁;郗玉松:《論中國共產(chǎn)黨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的形成》,《民族論壇(學(xué)術(shù)版)》2011年第7期。,囿于當(dāng)時復(fù)雜的情勢、貧瘠的法律條件等,中央為解決各階段的民族政治問題要依靠對民族區(qū)域?qū)嵤┱咝允跈?quán),由其自身解決本族內(nèi)的問題。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lǐng)》臨時確立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憲法地位,隨后,中央對民族自治區(qū)域的政策逐漸被我國《憲法》、我國《民族區(qū)域自治法》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從而形成權(quán)力的“法律吸收政策”授權(quán)路徑。
法律吸收政策型授權(quán)是民族政策法律化的表現(xiàn),使得民族區(qū)域自治克服政策性授權(quán)的弊端而獲得法律保障,描繪了民族自治區(qū)域“政策—法律—制度”獨(dú)特的授權(quán)變遷軌跡。筆者認(rèn)為,這種授權(quán)類型的特質(zhì)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授權(quán)事項(xiàng)的民族性。不論是中央對民族自治區(qū)域的政策還是憲法、法律等對其的規(guī)定,主要內(nèi)容集中于著力解決民族問題,推動實(shí)現(xiàn)民族自治,從而維持國家政治一體下的各民族平等、團(tuán)結(jié)、互助的民族關(guān)系。第二,中央與民族自治區(qū)域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比較柔性的、有限的“主體—主體”模式。我國《憲法》第115條、我國《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第20條規(guī)定了民族自治區(qū)域變通或補(bǔ)充法律的自治權(quán),這使得其擁有與中央溝通的地位和能量,但是其這種自治權(quán)的行使須要經(jīng)過中央的批準(zhǔn),最終要回到中央意志的控制框架中。第三,授權(quán)性質(zhì)的變遷性。法律吸收政策型授權(quán)實(shí)際包含兩條變遷主線,一條為政策性授權(quán)向法律性授權(quán)變遷,從筆者之前兩個部分的論述可以看出,政策性授權(quán)與法律性授權(quán)不僅是授權(quán)方式的區(qū)隔,而且其內(nèi)在的機(jī)理(包括授權(quán)范圍、授權(quán)者與被授權(quán)者的關(guān)系、授權(quán)功能等要素)存在很大差異;另一條為政治性授權(quán)向法律性授權(quán)變遷,一國法律一般以憲法為起點(diǎn),1954年我國《憲法》對民族自治區(qū)域的憲法性授權(quán)側(cè)重于解決民族政治問題,實(shí)質(zhì)上偏重于政治性授權(quán),直到我國《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的制定,才完成政治性授權(quán)性法律性授權(quán)的轉(zhuǎn)變。民族區(qū)域法律吸收政策型授權(quán)體現(xiàn)了中央政權(quán)在授權(quán)上的法治導(dǎo)向,刻畫了在存在形態(tài)上政策性、政治性授權(quán)轉(zhuǎn)向法律性授權(quán)的變遷趨勢。
(四)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復(fù)合型超越性授權(quán)

五、代結(jié)語:界定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授權(quán)性質(zhì)的四個基本維度
研究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性質(zhì)實(shí)質(zhì)就是探討中央與香港在該授權(quán)場域中所反映的特殊關(guān)系,需要從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二維體系中充分挖掘并準(zhǔn)確定性該特殊關(guān)系的影響因子。筆者以上從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歷史語境、現(xiàn)實(shí)語境和比較語境對界定該授權(quán)性質(zhì)的相關(guān)要素進(jìn)行了近乎全方位的剖析,筆者將剖析的初步結(jié)論總結(jié)為以下幾點(diǎn)。
首先,從歷史語境來看,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行動不同于對其他地方的授權(quán),其既有來自與英方談判的外部壓力,也有當(dāng)時中央管治能力難以匹配香港社會發(fā)展現(xiàn)狀與需求的內(nèi)部壓力,且前者權(quán)重更大,是一種“壓力型授權(quán)”;與授權(quán)密切相關(guān)的《中英聯(lián)合聲明》不是一項(xiàng)國際條約,不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jù),也不是制定基本法的政策依據(jù),其實(shí)質(zhì)是面向國際的記錄歷史事實(shí)的政策宣示性文件,英國沒有依此介入中央與香港特殊關(guān)系的空間和理由,中央與香港的關(guān)系不可能被引入國際因素而成為國際化關(guān)系。盡管如此,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一個在開放國際話語場域中具有國際信譽(yù)性質(zhì)的誠意之舉,中央在今后的授權(quán)行動中(尤其對某項(xiàng)授權(quán)的取消時)除了應(yīng)考慮是否符合中央對香港的既定方針政策,還應(yīng)當(dāng)考慮其所產(chǎn)生的國際影響。
其次,從現(xiàn)實(shí)語境來看,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在我國復(fù)雜單一制國家結(jié)構(gòu)形式下的特殊安排,是國家統(tǒng)一主權(quán)框架下對縱向權(quán)力平衡秩序的特殊價值追求,其內(nèi)涵包括:其一,中央與香港的關(guān)系是主權(quán)統(tǒng)一于中央的中央與特殊地方的關(guān)系;其二,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其三,不存在“剩余權(quán)力”的問題;其四,對香港的授權(quán)實(shí)踐中央享有監(jiān)督權(quán)。同時,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體現(xiàn)了香港高度自治與中央管治互動結(jié)構(gòu)中的主體間性,在這個互動結(jié)構(gòu)中,作為地方區(qū)域的香港必須接受中央為唯一主權(quán)性單位是其邏輯前提,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行動的預(yù)期是其內(nèi)在發(fā)生動力,香港對中央授權(quán)預(yù)期的反作用及其行動評估是其核心,中央與香港分別對各自授權(quán)預(yù)期進(jìn)行理性調(diào)整并由前者作出授權(quán)決定是其關(guān)鍵。
再次,從比較語境來看,我國目前形成了包括中央對普通行政區(qū)域的政策性授權(quán)、法律性授權(quán),中央對民族自治區(qū)域的“法律吸收政策”型授權(quán)和中央對香港的復(fù)合型超越性授權(quán)的授權(quán)譜系。上述幾種授權(quán)類型分別具有不同特質(zhì),其中,中央對香港的主權(quán)性授權(quán)和基本法確認(rèn)、保障香港居民的“超憲法”權(quán)利使得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超出授權(quán)程度上量的積累而具有了質(zhì)的秉性,筆者稱之為復(fù)合型超越性授權(quán)。
通過對以上三種語境下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相關(guān)因素的綜合分析,筆者認(rèn)為,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一種具有國際信譽(yù)的、體現(xiàn)主體間性的復(fù)雜單一制下的復(fù)合型超越性授權(quán)。為進(jìn)一步清晰地界定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從而全面準(zhǔn)確地把握這一性質(zhì)所反映的中央和香港間的特殊關(guān)系,下面筆者將從四個基本維度再進(jìn)一步歸納上述內(nèi)容。第一,授權(quán)環(huán)境的雙重性。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環(huán)境既包括國外環(huán)境即中央為統(tǒng)一主權(quán)而向英方作出妥協(xié),也包括國內(nèi)環(huán)境即中央為保持香港繁榮穩(wěn)定而向香港作出讓步,反映的是中央在香港問題上的國際信譽(yù)和中央管治與香港高度自治在互動結(jié)構(gòu)中的主體間性,其是香港問題在國內(nèi)外環(huán)境疊加的效果,這要求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時需持“雙邊”或“多邊”思維。第二,授權(quán)地位的超越性。香港獲得的權(quán)力或權(quán)利來自于中央的授予或確認(rèn),不存在“剩余權(quán)力”,但中央的主權(quán)性授權(quán)和香港居民享有的“超憲法”權(quán)利使得香港獲得了政治形式上超越性地位。第三,授權(quán)變遷的復(fù)合性。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中央構(gòu)建理性與香港自生自發(fā)秩序的互動與博弈,是兩者特殊關(guān)系的寫照,而中央與香港的特殊關(guān)系既可以通過反映中央與香港政府間關(guān)系的政策發(fā)生,也可以通過基本法或適用于香港的其他法律發(fā)生,甚至通過創(chuàng)造其他形式發(fā)生,因此,相應(yīng)地,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包括了政策性授權(quán)、法律性授權(quán)和超越性授權(quán)等,使這種授權(quán)具有了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多樣性。第四,授權(quán)效力的獨(dú)立性。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屬于中國主權(quán)或內(nèi)政范疇,一方面,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是我國復(fù)雜單一制國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形式的特殊安排,具有自主性、本源性、主導(dǎo)性,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實(shí)踐具有監(jiān)督權(quán)以及相應(yīng)的變更權(quán),當(dāng)然,理論上中央的這種授權(quán)應(yīng)該遵循授權(quán)法定原則,*授權(quán)法定原則是對私法上委托授權(quán)原則和公法上權(quán)力法定原則的借鑒,其要旨為授權(quán)行為不得肆意為之,須有法律依據(jù),遵守法定明示原則,由法律規(guī)定授權(quán)主體、范圍、內(nèi)容、程序、效力、責(zé)任等。有鑒于此,且我國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形成規(guī)模化的授權(quán)譜系,筆者建議全國人大制定以授權(quán)為規(guī)范對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授權(quán)法》。且中央對授權(quán)的變更遵循慎重原則;*《美國獨(dú)立宣言》第4段表達(dá)了這樣的原則,即“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yīng)當(dāng)由于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jīng)驗(yàn)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愿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quán)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xí)慣了的政府”。在本文的語境下,該原則的內(nèi)涵為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只要不違背“一國兩制”原則,只要不危及國家主權(quán)、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中央就不應(yīng)當(dāng)變更授權(quán)(主要是減少授權(quán))或取消授權(quán)。另一方面,包括英國在內(nèi)的國外力量不具有基于《中英聯(lián)合聲明》而制約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法律效力。
最后,中央對香港的授權(quán)不僅是窺探中央政權(quán)與香港特殊關(guān)系的“窗口”,也是識別中央與香港地方關(guān)系的一個“風(fēng)向標(biāo)”,通過它可以判斷中央對香港實(shí)施的是“寬松的一國兩制”還是“收緊的一國兩制”,并且,它還是觀察全球化場域中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關(guān)系的一個縮影,是型構(gòu)全球秩序的一個重要“參考系”,通過它可以評估中國在世界舞臺的國際影響力的強(qiáng)弱。在這種意義上,研究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授權(quán)的性質(zhì),厘清中央政權(quán)與香港在授權(quán)場域中的特殊關(guān)系,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和重要的理論價值。
(責(zé)任編輯:姚 魏)
張定淮,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深圳大學(xué)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底高揚(yáng),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憲法與行政法學(xué)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香港立法會普選背景下的功能界別制度改造研究”(項(xiàng)目編號:13AZZ015)和教育部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重大課題“推進(jìn)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實(shí)踐創(chuàng)新研究”(項(xiàng)目編號:14JZD003)的研究成果。
DF29
A
1005-9512-(2017)05-0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