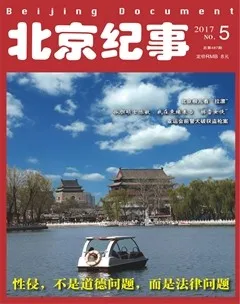戲癡湯吉利(中)
李強
永成從朝鮮回來了,帶著榮譽的光環回到了京劇團。別看永成京劇上實在不怎么樣,只會一出戲,外號永一出,就是永遠會唱一出戲。但是,永成的心里有政治,知道上邊最喜歡什么,知道看風向。特別是在揭發戲子湯吉利是軍閥湯恩伯干兒子這件事上,得到了特別的好處,那心思就更不在演戲上,時時刻刻地用鼻子聞著上邊又有什么新提法,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

您看見了吧,一個人一個活法,通過幾年的努力,永成竟是文化局的副局長了。但是,由于心里的那點小東西在作怪,幾年來,永成一直不見湯吉利。湯吉利可沒那么多心眼,心想事情都過去好多年了,師兄還是師兄,該看還得去看。有一次,湯吉利去看他,卻被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擋在了外面。湯吉利笑了笑,也就斷了再和他來往的念頭了。
這一年的7月,天出奇的熱,樹葉在熱浪的烘烤下彎下了腰,翻卷在一起,寄居在樹上的知了兒也懶得閉上了嘴,沒有了往日的喧囂,顯出了可怕的寂靜。一會兒,天上傳來了雷聲的轟鳴,烏云裹挾著風向人們撲了過來,黃豆大的雨點打在土地上,掀起了一層塵土,馬上這層塵土又被接下來的雨點壓向了地面。
湯吉利老刀李姐三個人站在門口,看著這風這云這雨,聽著噼噼啪啪的聲音,想著剛才會議的情況。回收公司的領導和文化局的領導聯合在這里開了會,聽那意思,這里是右派言論的聚集點,攻擊現代京戲不如老戲過癮,還說,現在找不出黑包公這樣為民請命的官兒。聽得三個人后背直冒冷汗,不就是唱兩口老戲么,還牽扯上反黨了,這是哪兒跟哪兒的事呀!
老刀看著李姐和湯吉利說,沒事。李姐你拉家帶口的,什么都沒參與。吉利,你在我眼里是個孩子,也沒你什么事。真要有事,我老刀扛著。吉利和李姐的眼淚都快下來了。
湯吉利聽得出來,剛才文化局的領導就是沖著自己來的,還點了一句,有的人歷史上就和大軍閥拉扯不清,那肯定是又提起湯恩伯的事啦。正想著呢,老刀說話了,關門上板,愛誰誰,咱們回家吃炸醬面去啦。吉利到我家去吧,小碗干炸。湯吉利說,我這心里不得勁兒,忽悠忽悠的,不踏實。老刀說,管他呢,明天天塌下來是明天的事,今天該吃什么還吃什么。說著,拉起湯吉利打著傘就往家走。
幾天以后文化局和回收公司的兩個工作人員找湯吉利談話,讓他交代右派言行。湯吉利拿著一把胡琴一進門腿就發軟,好懸,沒跪下。他記得有出戲,叫蘇三會審,被審的人一準兒的要跪下,可這是新社會了,平等了。湯吉利沒等那兩個人說話,自己先交代問題,領導,都是這胡琴惹的禍,沒有它,我們就不會唱戲。不唱戲也就不會來這么多戲迷。不來這么多的戲迷,就不會有人亂說。沒人亂說,也就不會給兩位領導找這么大的麻煩。當著您的面我給它摔嘍。說著話,他舉起手中的胡琴猛地往磚地上一摔,那把胡琴瞬間變得粉身碎骨,可憐的軀體飛得滿屋都是。
那兩個人,先是聽湯吉利說繞口令一樣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大堆,還沒明白過來是怎么回事,又見他把胡琴摔了,都吃了一驚。其中一個人站起來大聲地呵斥道,湯吉利,什么亂七八糟的,和胡琴有什么關系?交代你們和社會上的那些人都說過什么?正這時候,門開了,老刀闖了進來,對著這兩個人說道,跟他沒關系,我是這個店的負責人,社會上的那些個人都是沖著我來的。要是說過什么不中聽的,也是我的責任。站著的那位冷笑道,終于跳出來了,那你就交代,湯吉利出去。湯吉利一聲沒吭,冒著一腦袋汗退了出來,他在心里佩服老刀。

過了兩個月,文化局這個右派大戶分出了一個名額,給了回收公司。老刀那張細長臉的上面多了一頂帽子——右派。這天晚上,當老刀拖著疲憊的雙腿回到家里的時候,湯吉利撲通一下給老刀跪下了。哭著道,師傅,我知道,這右派的帽子是我的,他們是沖著我來的呀!我真沒用。燕子一看也跪了下來。
老刀扶起兩個孩子,讓他們坐下。說道,我都快60了,沒事。你們不能有事。今天你們當著我的面發誓,互敬互愛地過好日子,我這個右派就沒白當。湯吉利和燕子雙雙跪在老刀面前,給老刀磕了三個響頭,淚眼漣漣地叫了聲爸爸。老刀笑了,說道,好了,天塌不下來。我去給你們小兩口兒做一鍋羊肉汆面。吉利,到大街酒鋪買兩毛錢豬頭肉,咱們爺兒仨喝兩口兒。
我媽給我講這個湯吉利的時候,特意地指出一點,湯吉利的一生,就是得意裹夾著倒霉,再一次的得意伴隨著倒霉的過程。別有一點好事,緊接著的準保是一件懊啕事,你說怎么這么邪性!我想,這就是湯吉利的命,說白了也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遇上好事得意忘形,老百姓的話叫作不知道摁著點,太張揚。
湯吉利簡單地舉行了個婚禮,算是成家了。老刀喝大了,趴在桌子上指著湯吉利嘻嘻地笑,你小子進我們家門,你是賺大發了。不許欺負燕子,不能讓她掉一滴眼淚。要不然,我打斷你的那條狗腿。湯吉利也喝高了,哥們兒,你放心吧。燕子是我心尖上的那塊肉,我要讓她天天高興,你就放心吧!老刀說,行,夠哥們兒意思。燕子哭得像淚人似的,她知道,老爸明天就要到團泊洼勞改去了,他不放心自己,這是有托孤的意思啊。燕子擦了一把眼淚,拿著一支筷子,在飯碗上打著鼓點,低聲地唱道:
耳邊廂忽聽得人聲喧震,見先生站埃塵珠淚淋淋。
二皇兒含悲淚一旁跪定,孤又慚孤又恨孤又傷心。
寫遺詔不由得孤的珠淚滾滾,叫先生你就是托孤的大臣。
老刀和湯吉利聽到這里,淚水順著手指的縫隙流了下來,落在袖子上,連前胸的衣服也濕了一大片。果然,老刀再也沒能活著回到北新倉。
三
戲子湯吉利過了幾年的安穩日子。京劇是湯吉利的半條命,沒孩子的時候,兩口子下班回到家里就來一段。在湯吉利的開導下,燕子已經會唱幾十段了,而且是有板有眼。星期日的時候,湯吉利騎著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車,到前門大街戲劇商店,買兩根白蠟桿子,再買一塊五合板,拿個破鋸條,吭哧坑哧地做了京劇用的刀槍把子。刀身用銀粉一刷,找個紅布條拴在刀把上,齊活。兩口子在院里練起來了。
平時湯吉利和燕子的對話更有意思。早飯的時間到了,燕子說,主公,該用早膳了。湯吉利要上班了,對著燕子說,啊娘子,我要上朝了啊啊啊。這才出門。不知道要吃什么,燕子問了,啊哈,主公,今天咱們吃什么好呢?湯吉利一扭頭,這這這個么,還是吃打鹵面吧。帶著韻,拉長聲,您乍一聽,還以為真是要開戲了。

湯吉利遇到的事情太多了,除了這一點愛好,再也不敢逞能好強了。他自己認為,我在我們家的后院唱戲誰也管不著,礙不著誰。但是他忘了一條,天上下雨,誰身上不淋上幾個泥點呀。
這一天,戲子湯吉利慌慌張張地跑進自己家的院子,轉身關上街門,進屋以后馬上關上了屋門。這會兒也顧不上喊娘子了,拉著燕子的手,走到靠墻的地方低聲說,我剛聽說,今天,一群人在孔廟里,把京劇院的戲裝一把火給燒了,據說還打了人。你說,咱家的那些戲裝不會惹事吧?他右手攥成拳頭,不停地敲打著左手手心,臉上沁出了汗珠。
燕子一直把湯吉利當作家里的頂天柱,凡事都是湯吉利拿主意,雖然十個主意里有五個有餿味,但是燕子就信他。家里的戲裝是湯吉利和燕子從牙縫里省出來的,有的還是燕子一針一線摳持出來的。甭說燒,就是送人也舍不得。湯吉利說,咱不能燒,我舍不得。燕子也說,我心疼。湯吉利說,我幾十年沒上臺了,我還要穿著它上臺唱戲呢。燕子看著他說,對。可是,現在怎么辦,那些人不會上咱家來燒戲裝吧?
一句話又把湯吉利說慌了,在屋里來回走溜,走著走著,一腳踢在盛米的米缸上了,腦子里靈光一閃,雙手拉住燕子說,我有辦法啦,咱們把戲裝疊好嘍放進米缸,然后埋在院里,誰要問咱們戲裝哪兒去了,咱倆就說扔垃圾堆了。湯吉利笑了,又恢復了以往的狀態,說道,娘子,你看我的辦法是不是真真的高明呀?燕子也這味兒,啊主公,確實地高明呀,哈哈哈!您說這兩口子有個正形嗎?
倆人忙活了半夜,把戲裝用包袱皮包好再放到缸里,拿張油紙包住缸口,湯吉利輕輕地開開門,看看四周,又輕聲地走到門口聽聽門外也沒動靜。這才開始行動,在樹下挖了一個大坑,放進米缸,壓上一塊石板,上面再放上土,再踩上幾腳,然后又把一堆生火的劈柴放在上面。倆人對視著一笑,回到屋里激動得半天睡不著覺。燕子在床上抱著湯吉利,點著他的腦門說,這里面是什么呀,這么聰明。湯吉利得意極了,把燕子壓在身下,幸福了一把。
湯吉利的廢品收購站越來越紅火了,很多的人家被抄了,那些不用的東西送到了廢品站。原先遇到京劇里用的東西,湯吉利都要好好看一看,喜歡的就自己買下了。現在,打死他也不敢了。而且他的腦子里不時地出現那口大米缸,好像那缸會在某一個時間突然從天上掉下來,而且,不偏不正地砸在自己的腦瓜頂上。這時湯吉利的前胸后背就都是冷汗。下班后也顧不得帶回要買的菜,一溜煙跑回家,看到那堆劈柴還在時,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雙手在胸前來回地胡嚕著。然后出門買菜。
人和人就是不一樣,在那個轟轟烈烈的年代,別看湯吉利的師兄永成戲不會兩出,但是,人家腦子好使,會見風轉舵。如今,已經是文藝尖兵戰斗隊的司令了,在他的帶領下搗毀了一切“封資修”的東西。湯吉利看到報紙上永成的大照片,對燕子說,他這些事我做不來,我就想演戲,我生來就是個演戲的,是戲子。可惜呀,這么點愿望看來也實現不了了。說到此時,湯吉利的眼圈紅了。燕子趕忙像哄孩子一樣去哄他,只要你喜歡戲,我以后有錢了一定讓你演上一出鬧天宮。一言為定啊,一言為定。倆人的手在空中拍在了一起,發出了一聲響亮的聲音,這聲音穿透了未來的30年,在我們國家走上發展的大道后,湯吉利還真的唱了一出大戲,當然了,那是后話。
湯吉利擔心的事終于發生了,那口大缸終于從天上飛落下來,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湯吉利的腦門上。
門外一聲亂喊,憤怒的人們踹開了湯吉利家的街門。當湯吉利和燕子被人們揪到院子當中站定,抬起頭看到師兄永成一身綠軍裝,氣宇軒昂迎面走來的時候,湯吉利心中一陣慌亂,心想,完了。剛開口叫了一聲“師兄”,一皮帶抽在湯吉利的腦門上,一股鮮血涌了出來,像幾條紅色的蚯蚓迅速地在臉上蠕動著。湯吉利的眼睛也爬上了蚯蚓,這時在他的視野里全是血紅,略帶著血腥味道。
有人端過來一把椅子,永成站在高高的椅子上,人們仰視著他。嘶啞的聲音從永成的喉嚨里迸發出來:大家看這個人,他歷史上就有問題,國民黨戰犯湯恩伯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個大壞蛋,這個人就是湯恩伯的干兒子,是他留在大陸的一顆炸彈!然后,停頓一分鐘,他指著那堆柴火說,那里有什么?大家知道,封資修的東西我們一定要砸他個稀巴爛,那里是他們藏起來的戲裝,也可以叫復辟裝。
幾個人開始搬柴火,幾下子就把缸里的東西提溜出來,扔在了湯吉利的面前,點上一把火。湯吉利的臉色像死灰一樣,他盯著永成說,師兄,你好久不練功了,聲音都沒法聽了。永成一愣,這個場合竟不知道怎么接湯吉利這句話。
有人給湯吉利戴上一頂高高的紙帽子,上面寫著封資修三個大字。然后,塞在他手里一面小鑼和一柄鑼槌。湯吉利繼續對永成說,這是白無常戴的,你還記得師父怎么教我們表演的嗎?也不等他回答,湯吉利敲兩下鑼,就開始伸著雙手,在院子里來回地蹦著蹦著。永成看到湯吉利的動作,忽然一愣。想起當年在戲校學這出戲的時候,永成不會做動作,老師舉著板子打,湯吉利趴在永成的屁股上,替他挨了幾板子。下學以后,兩個人戴著黑白無常的帽子發誓說,如果今后誰要是做了對不起對方的事,就讓黑白無常把對方一條鏈子鎖走。想起這些,永成愣在那里,兩眼發直,喉嚨發甜,雙手出汗,看著眼前的湯吉利,正在向自己蹦過來,想跑又邁不動雙腿。眼前一黑,一聲大叫,從椅子上摔落在塵埃里。院里的人們趕緊抱起司令上醫院。
院子里只剩下燕子和不停地蹦來蹦去的湯吉利。燕子關上大門,打掉湯吉利頭上的紙帽子,湯吉利不蹦了,只在那里傻笑。
北新倉的人都知道,湯吉利瘋了,他師兄傻了。
(編輯·宋國強)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