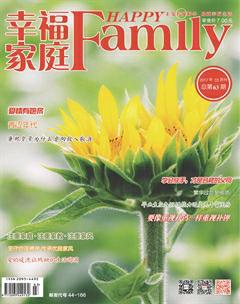“插隊”第一天
汪泰
1969年1月19日是我永遠不會忘卻的日子。從那天起,我的身份開始了徹底的改變。1965年9月至1969年1月,帶著不到初中一年級的文化程度,由1968屆初中畢業生變成了插隊知識青年,農民稱之為“新農民”。從此,我做了十年“知青”。
那天早上,我帶著隨身行李趕到學校,學校組織了下一屆的新生敲鑼打鼓歡送我們下鄉。幾個月前,我們在校門口剛送走了1966屆、1967屆初、高中畢業生。我們是“老三屆”中最低的一屆。
我們的隊伍從學校步行到船碼頭。碼頭紅旗招展,10多條大木船一溜排在河邊。碼頭周邊早已聚集了眾多的知青家長。家長們在孩子到學校集中的同時,把行李、箱子等大件運到了碼頭,他們在為孩子們做最后一刻的事情,盡最后一份的義務。隊伍到了,家長們忙迎上去,幫著把大件行李運上指定的木船。忙碌半天,分手的時刻到了,船上的高音喇叭反復喊話,要同學們上船。岸邊,大人孩子手牽手,叮嚀再叮嚀,囑咐再囑咐。知青們臉上充滿著興奮,洋溢著笑容;家長臉上更多的是不安與隱隱的憂慮。這種不安和憂慮,那時的我們看不到也體會不到。終于,船隊出發了。
別了,高郵古城;再見了,親人。船行出了好遠好遠,家長們的手臂還高舉著、搖晃著。
每條木船可坐30人左右,船上沒有座位,大家在船倉、甲板上隨便找個地方坐下,有的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船隊緩緩前行,看著船外荒涼光禿的樹木,看著沿途向后緩緩移動的景物,忽然一種不知是怎樣的心境傳染開來,同學們都默不作聲。臨近中午,大家紛紛拿出隨身攜帶的干糧充饑。過了好長時間,不知從哪條船上傳來了歌聲,不一會兒,歌聲就此起彼伏了。船隊走了近8個小時,終于到達甘垛公社的糧站碼頭,那時已是下午近五點,天開始暗了下來。
下船,整隊步行到公社會堂,由當時的公社文教負責人主持,帶領全體知青舉行“請示”活動。一番冗長的儀式后,公社領導致歡迎辭,宣布哪一組到哪個大隊哪個生產小隊,要求各生產隊把知青安全帶到。接著,公社代表發言,知青代表講話表示決心,說得最多的是“廣闊天地煉紅心”,喊得最響的是“扎根農村一輩子”。我們這組分到沈團大隊第三生產隊。
天已黑盡,還要趕路,早已守候帶隊的社員帶領我們上路,大件行李上船從水路走,人步行。走在鄉間的路上,說是路,其實就是寬寬窄窄的田埂。到達村口后,村里響起了爆竹聲,我們連忙高呼口號:
“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誰知喊了一陣,領路的社員笑著說:“這是四隊的人,見我們就放炮仗,三隊還在前面呢,讓他們放吧。”又領著我們往前走了一段。到了,我們又激動地喊了一陣口號。
為了迎接“新農民”,生產隊辦了幾桌飯,燒了大麥酒,當天全生產隊每戶一人來吃飯喝酒。說是迎接“新農民”,可“新農民”來得太遲,晚飯已吃過了。見到我們,生產隊長、會計等干部招呼我們坐下吃飯,飯還有,菜沒了,只有些菜湯和剩下的大魚頭。好在我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不計較飯菜。大家吃了來農村的第一頓飯,吃得很香。
飯后,大隊黨支部王支書來了,他向我們介紹了生產隊的各位干部以及給我們配的輔導員。生產隊長說:“明天‘新農民休息一天,到公社買糧、買油,領農具和生產資料。這兩天的飯請姜主任給你們做,到菜田弄點黃芽菜來。”我們感到一陣溫暖。
當晚被安排住在臨時為我們準備的宿舍里,是一家社員的空房子。三張床,兩人一鋪,正好。床上已鋪了一層厚厚的新稻草。于是大家趕緊整理床鋪,收拾各自物品,洗漱睡覺。上床睡不著,看著草房的屋頂,還有新安的電燈,聞著身下柔軟的稻草香,在興奮和莫名的不安中度過了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