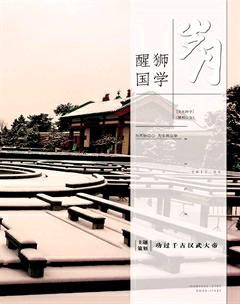圣賢氣象
朱良志
“養”得一種心靈的大氣象,有了這種氣象,則可優游回環,暢游生命之樂。
元代藝術家倪云林有一聯詩道:“喟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奈若何。”此頗有韻味。前一句說的是孔門之事。孔子一日和弟子閑坐,子路、冉有、公西華等都“各言爾志”,有的愿去管理一個國家,有的愿去做一個禮儀官員等,而此時,曾點則在鼓他的瑟,聽孔子詢問,方舍瑟而言。他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完他的話,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這天光云影的氣象、惠風和暢的格調、與天優游的境界,感染了一位時值暮年的哲學家。這暮春季節的向往,簡直有王羲之蘭亭燕集的風韻。
下一句“不利虞兮奈若何”說的是項羽事。項羽作為一世英豪,當初引八千精兵北上,氣勢如虹。但卻在殘酷的楚漢之爭中,最后兵敗垓下,四面楚歌。月黑風高的一個晚上,中軍帳里,項羽飲酒數過,面對絕望的美人虞姬,一首悲愴的歌從他胸腔傳出:“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自嘆是“天之亡我”,歷史學家則多認為他有勇無謀,而在藝術家倪云林看來,項羽缺少的正是那優游回環的心靈境界,如此好勇斗狠,如此褊狹局促,焉有不敗之理!云林在此正是要突顯圣賢的氣象,一個器宇闊大,一個激進褊狹,其成敗不言自明。
中國傳統哲學對“圣賢氣象”非常重視。朱熹《近思錄》專列“圣賢氣象”一節,如其云:“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北宋周敦頤儀態雍容,有人以“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評之。程顥詩云:“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所彰顯的正是其心靈的“云淡風輕”。朱熹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里所寫的,也正是他心靈的“天光云影”。涵容廣大,體露真常,了無滯礙,一任慧心流淌,正是所謂圣賢氣象的體現。
中庸是孔子所奉行的哲學原則,但孔子卻并不排斥狂狷。在他看來,狂妄的人喜歡進取,狷介的人往往奉行正道。他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使我想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東坡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想到春秋時那位泛舟五湖的賢達范蠡。孔子這里所陳示的不是未來生活的安排,它與風乎舞雩的境界一樣,透露出的是從容瀟灑、無所羈絆的精神氣質。據《孟子》記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這里所包含的就有一份“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情懷。圣賢的氣象中,洋溢著濃厚的樂觀格調。有位叫葉公子高的人問子路:“你的老師怎樣?”子路不知怎么回答,歸而告老師,孔子說:你就說,他這個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暢游在道的領悟中、生命的體驗中。后代儒家有尋“孔顏樂處”的說法,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而孔子自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其實這里透露出的不僅是安貧樂道的忍耐力,而且是一種幽深遠闊的生命情調。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識的獲得是技能的,喜愛一種東西并為之奮進,是一種情感傾向的形成;而在傾心的對象中獲得快樂,這是生命的安頓、心性的超越。由知到好,由好到樂,其實正是氣象的提升。
中國先哲們的快樂哲學是一種獨特的宇宙人生體驗。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曾說:“如果幸福在于肉體的快感,那么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的時候,就是幸福的。”孔門的樂處,當然遠遠超越了物質滿足所帶來的愉悅,同時也超越了德性原則滿足所帶來的快樂,而是一種“宇宙般的快樂”。個體生命渾然融于宇宙之中,覺自我與天地為一體,此時生命的短暫超越了,欲望的局限超越了,種種有限性的困擾煙消云散,從而會歸于天地之一氣。此時,一如陶淵明所說的:“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道出了這樣的大樂境界。“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仔細揣摩孔子這段關于“樂”的表述,可以發現,仁者壽,不是說生命的延長,自然生命并不一定能延長,而是人在宇宙中伸展自己。孔子以山靜為人生之蘄向,描畫的是一個生命宇宙的大和諧。
中國哲學關于圣賢氣象的學說,在今天仍然有其意義。氣象和境界,是人生命的智慧,是人所以自立的基礎。培植心靈的氣象,使我們的心宇更“大器”一點,雖未必要去成就圣賢,卻可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氣象的提升,可以幫助我們以從容的心態對待急速流轉的節奏,可以舒緩我們因激烈競爭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可以使人生的步子走得更堅實,并富有快樂的韻味。我們知道,在一個優游的心靈中,月更明,風更清。(轉載自《光明日報》2005年12月27日0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