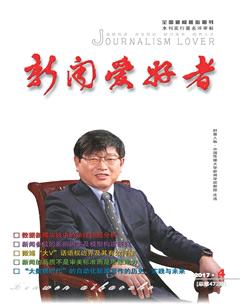“羅爾事件”的是與非
王軍+王璇+朱珊珊
【摘要】2016年末,“羅爾事件”引起輿論沸騰,在法律與倫理層面產生諸多亟待澄清的問題。斯人已逝,信息爆炸的今天,被其他信息沖擊后,公眾對于“羅爾事件”的記憶或許并不長久。或許,深入反思現行慈善制度,促進全社會范圍內達成公益共識,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是將“羅爾事件”銘記在心的最好方式。
【關鍵詞】慈善法;傳媒倫理;羅爾事件
2016年11月25日,羅爾在個人微信公眾號“羅爾”中發布了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該文講述了自己的女兒因白血病入住醫院重癥監護病房的危急情況及就醫過程中面臨的困境。羅爾與朋友劉俠風所創辦的小銅人金融服務有限公司旗下公眾號“P2P觀察”整合羅爾文章并開設贊賞功能,同時,小銅人公司承諾以文章轉發量定額捐贈。深圳小銅人旗下公眾號“P2P觀察”于27日、28日分別轉發了羅爾的文章《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以及《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此后,兩篇文章在網絡空間被多次轉發,文章贊賞一度達到上限,最后共計收到贊賞金額261萬元。11月30日,知情人曝出羅爾家境和真實醫療費用,部分網友質疑該事件是營銷行為。隨后,各大媒體、社交網站以“帶血營銷”等字眼質問羅爾的募捐行為。
一、“羅爾事件”現象級傳播的原因
筆者認為,羅爾的文章算不上精致,形成大量轉發和獲得大量捐款的原因或許在于“讀者每轉發一次,小銅人公司向羅爾定向捐贈一元”。
“轉發一次,捐款一元”這一營銷方案,利用了經濟學中“成本-收益”原理,充分調動了微信用戶的積極性。一般來說,捐款獻愛心是要有成本付出的,但這次事件中,大多數人需要做的只是文章的轉發,無論時間成本還是經濟成本都接近于零。而人們的轉發行為不僅能夠在朋友圈中展現自己的愛心,同時也能夠間接為患病兒童提供經濟幫助,收益顯然遠大于成本。轉發者認為只是轉發一次,并不會對他人帶來影響,只會讓“小銅人”多捐助一元錢。但這種想法在現實中是不可靠的,原因類似于經濟學中的“黑天鵝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罕見和不可能的事件出現的次數比人想得多。”
人們在轉發羅爾的文章時,或許不會打賞文章,而只是單純地轉發。轉發時,轉發者可能不曾想到,文章被如此大范圍地轉發后,有人會自愿捐款。事實證明,捐款者不在少數,無論概率多低的事件,只要經過無數次的重復,都會造成人們想象之外的結果。
當事件進入這個循環的傳播過程后,事件影響力不斷擴大、循環、再擴大,不論羅爾本人還是小銅人公司都無力控制事件跳出這個循環的發展事態,最終高達261萬元的贊賞金額正是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結果。
而從傳播學視角看,羅爾的文章刷爆朋友圈,也與微信的“病毒感染式傳播”有關。社交網絡是基于用戶互相的關注、互動形成的關系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同病毒感染機制一樣,存在著三種人群:信息的易感人群、信息感染者和信息免疫者。[1]最初,微信是由熟人構成的小圈子,隨著微信的普及,這個圈子慢慢流動,“熟人社交”的范圍逐漸擴大,“半熟的人”甚至“不熟的人”也會出現在好友列表中。盡管微信中個人用戶的好友構成趨于復合多元,但是通常“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個體在社交網絡中傾向于同與自己相似性高的人建立好友關系。好友屬性的趨同性,使他們對某一特定類型的信息做出趨同的選擇。當一個微信用戶看到了羅爾的文章并發到微信朋友圈后,他即成為這條信息的“傳染者”,他的微信好友中,對于信息有著相近或相同“口味”的人,看到他的分享后也會點開鏈接,甚至在觀看之后轉發。這樣,羅爾的文章由信息感染者發出后,在微信的社交網絡中通過消息轉發機制,“感染”了更多“消息易感人群”,“消息易感人群”接收消息后,其中的一部分從“被感染者”轉變為“傳染者”,成為文章的新的“傳染源”,羅爾的文章從而得到廣泛而迅速的傳播,形成了龐大的閱讀和轉發體量。
二、從法律層面管窺“羅爾事件”性質
(一)個人求助與慈善募捐
個人求助,指個人因為自身或親屬遇到困難而向外界求助以募集資產。
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組織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包括面向社會公眾的公開募捐和面向特定對象的定向募捐。①同時,《慈善法》禁止沒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個人和組織開展公開募捐,但個人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統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臺發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時在其網站發布募捐信息②。
個人求助與個人募捐的本質區別在于發起人與受捐人的關系。個人求助僅限于為救助本人或者近親屬向社會的求助行為。而如果是為了救助本人及近親屬以外的他人在網絡上發起的個人募捐,則屬于非法募捐,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羅爾事件中的當事人羅爾為患白血病女兒向社會求助的行為屬于個人求助行為,不違反法律的規定。但在此事件中也暴露出當前法律對個人募捐沒有規范的管理、監督體制,依靠法律無法制約受捐人的行為,也無法很好地維護捐贈人的利益。如果出現濫用善款的情況,也只能對受捐人進行道德上的譴責。
(二)非募捐的性質界定與實際結果的沖突
民政部在2016年8月認定了首批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共26家。也就是說,如果個人想在網絡上公開募捐的話,只能通過這26家平臺進行公示,并獲得資助,本次事件的傳播平臺——“微信”并不在其中。
但微信官方否認羅爾收到的贊賞是捐助,沒有核實其資產和資格的義務。微信官方認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一文中,沒有提出募捐的需求,只是用戶自發贊賞,不存在違規行為,平臺沒有處理文章和賬號本身。
優秀的內容獲得大批量用戶自發打賞無可非議,但是,羅爾事件中巨額的微信用戶贊賞與通常情況下的贊賞有本質上的區別。羅爾在文章中雖然并沒有直接請求社會公眾捐助,但與一般文章不同的是,羅爾在行文中不是依靠動人的情節和精美的修辭來獲得轉發和打賞,而是一種類似于哭訴和煽情的家庭敘事,給人們留下了求助社會、哭訴乞討的印象。顯然,人們對羅爾文章的打賞并不是贊賞文章內容本身,而是被文中羅爾的哭訴、文章傳遞的父親救女心切的真情打動,才對患病女童的捐助。單純從文字方面,羅爾的文章顯然與驚人的贊賞金額不相匹配,數額巨大的打賞和轉發在事實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捐助。
對羅爾文章非募捐的性質界定和實際結果中與文不符的高額贊賞,正是本次事件的吊詭之處。
(三)羅爾的行為是否構成騙捐
拋開事件是否屬于募捐的性質,單從結果來看,高達261萬元的贊賞金額應該定義為善款,因此無論動機是否是募捐,都達到了募捐的效果。
知情人曝出羅爾資產和真實醫療費用,引發公眾輿論巨大反轉,質疑羅爾騙捐和營銷,但對此事件是否構成騙捐,還需要進行討論。
羅爾文章確實存在不誠實的情況。“P2P觀察”轉發羅爾的文章《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中提及了患病女童的醫療費用,“每天醫療費用少則一萬出頭,多則三萬有余,一大半少兒醫保走不了”,這一情況經過深圳兒童醫院的聲明證明羅爾嚴重夸大了醫療費用。
但羅爾的不誠實與騙捐還有一定的差別。所謂騙捐,是指行為人打著慈善公益的旗號,向公眾發出捐贈倡議并接受慈善捐贈,但事后將受贈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2]
2016年年初,有5萬粉絲的“知乎女神”童瑤騙捐24萬元。后查證此人是一個男性,注冊了四個“知乎”賬號,一個賬號通過不斷回復感情問題成為擁有5萬粉絲的大V,另一個賬號扮演重病美女,隨后一人分飾兩角詐捐。而羅爾事件中,羅爾的女兒身患白血病且病情危急是事實,羅爾救女心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影響:一是羅爾的文章過于煽情不加克制,二是他的朋友劉俠風在幫助他的過程中采用不當的營銷手段,引發事態的不斷擴大。在此過程中,羅爾和小銅人公司曾試圖控制事態發展,但已無力挽回。在當月的29日和30日,羅爾分別發文《我承認,我被錢砸暈了頭》和《我主耶穌,我向你求告》,呼吁大家暫停打款,又通過部分有影響力的媒體微信公眾號發布“善款已夠,請停止打賞的信息”,但事態進入了傳播擴大的循環后,當事人已經無力控制。因此,從主觀意圖上來說,羅爾并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為目的,并非與“童瑤”事件中當事人一樣有意騙捐。
三、從倫理層面探析“羅爾事件”存在的問題
(一)撕裂的輿論,是善意的覺醒還是善意的缺失
2016年12月24日早晨6時許,羅爾之女因病離世。此后,羅爾因宣布將女兒的遺體進行捐贈再次引起輿論嘩然,羅爾本人也再度陷入爭議。一瞬間,網絡空間充斥著責罵聲,網友“吃草小鼠”在評論中寫道“小朋友真可憐,死了還被父母消費,父母豬狗不如”,并咒罵羅爾夫婦“下地獄”;網友“恍惚未開”認為“羅爾夫婦實在是太惡心了”。這樣的質疑聲在網絡空間隨處可見。其中,有一部分網友還認為羅爾選擇遺體捐贈的做法是在挽回自己的名聲,重塑自己的形象。“IO指萌扣”評論道:“孩子活著的時候遭那么大的罪,死了還要被父母利用洗白。”無獨有偶,網友“夢在相遇前”也認為“一個患白血病的女孩,生前是父親的賺錢機器,死后卻又成為父親洗白的關鍵,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徒”。③
回看整個事件,這并不是輿論的第一次沸騰。在網絡空間瘋轉并獲得極高打賞金額的文章《羅一笑,你給我站住》中,羅爾用細膩的筆觸娓娓道來,寄情于文,字里行間流露著一個父親眼見自己的女兒身患重病卻近乎無能為力的無奈以及對女兒的疼愛與憐惜,感動了萬千網友。正是羅爾感人至深的、無私的父愛及羅爾之女身患重病卻充滿希望的樂觀喚起了網友心中的善意,人性之善觸發了網友轉發文章、助力捐贈、自發打賞的行為。此時,公眾作為輿論的主體對羅爾及其女表現出了關切與支持。然而,此后不久,隨著羅爾個人財產情況被“扒皮”,輿論迅速轉向,很多網友痛罵羅爾是“利用自己女兒的騙子”“只懂作秀、不顧女兒死活的惡人”,譏諷羅爾是“守財奴”。也有網友表示,不一定非要處于絕境,才能向社會求助,如“大漠孤煙直”認為:“一個人陷入困難后,如果能尋求到幫助,何樂而不為,不必非得等到走投無路。”④輿論倒向批判羅爾的行為,其中不乏惡言惡語,但是,也有為羅爾辯駁的不同聲音,喧囂的輿論一度撕裂。
作為輿論主體,社會公眾在“羅爾事件”中扮演著行善主體的角色。亞里士多德主張做人開始于培養向善的能力,這一能力必須在實踐中發展。他認為:“我們一開始行善,做客觀公正之事,并不知道這些行為是好的,也不是自己積極理性的選擇。”[3]網友被羅爾和他的女兒所打動,自發地轉發文章、打賞文章時,善的本心被喚醒,未經過多考慮即選擇了伸出援助之手。社會公眾敏感而脆弱,善意之心在“安徽女‘救人被狗咬騙捐事件”“天津爆炸90后女生騙捐門”“知乎女神童謠騙捐事件”等一系列騙捐事件被爆出后,一次次承受著打擊。然而,在最初看到《羅一笑,你給我站住》《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時,很多人依然沒有猶豫,毅然選擇相信并對患病的女孩施以救助,這是人性中善意與愛意的覺醒。
事件的反轉將羅爾推向輿論風口,一眾網民出于“被騙的憤怒”惡語相向,輿論刻畫的羅爾形象是“利用公眾的愛心騙取善款的惡人”。筆者認為,大多數網友所述的“騙捐”,并非羅爾本意。此事件中羅爾之女身患重病,這一基本事實是屬實的。而在述說女兒病情的文章進入傳播過程后,羅爾因在文章中隱去了包括個人收入、個人積蓄在內的部分真實信息,導致呈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信息殘缺不全,造成信息的不對稱。公眾的憤怒點在于羅爾有能力進行自我救助,卻超越了自我救助—熟人救助—社會救助的順序,直接尋求社會資源的幫助,并且在尋求幫助時未告知部分真實信息。羅爾向社會求助,是其個人權利,但是,求助時應盡可能詳盡地公布信息、講清楚事實,保證呈現在公共空間的信息真實透明,最大程度上不影響公眾進行事件判別和行為選擇。
“善”與“惡”在界定人的行為時形成二元對立。一般來說,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中都追求著滿含善意的愛,這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羅爾事件”中,不管是尋求社會幫助的羅爾,還是使用了營銷方式幫助朋友的劉俠風,抑或是伸出援手卻怒斥羅爾的社會公眾,其出發點都是善的,是對患病女童的關心與愛護。雅各·蒂洛提出“道德體系中應蘊含善良原則”,他認為“盡管倫理學家們對善的實際理解可能不同,但他們無不要求人們努力行善,做正當的事”。雖然在實際操作時,羅爾沒有把握好求助的分寸,劉俠風在捐贈時摻雜了個人的利益訴求,公眾在得知事件真相后沒有克制怒意、大罵出口,但是善的初心未變,善意彌散在網絡空間,因為在整個事件中,不管是媒體的報道還是網友的評論,都在祝愿小女孩能夠早日康復。
(二)媒體報道方式不當,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1989年11月20日,第四屆聯合國大會第25號決議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該公約對“兒童”的概念予以明確界定:兒童系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于18歲。我國的“未成年人”的概念和上述公約中的“兒童”概念具有一致性。199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第一章第二條規定:未成年人指的是未滿18周歲的公民。在我國,“兒童”與“未成年人”這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具差別,只是在不同的學科領域的稱謂不同,“兒童”更傾向于社會學概念,“未成年人”是一個法學概念。[4]
稱謂的差異并不會影響一個事實,即“羅爾事件”中的羅爾之女是一個6歲的女童,尚未成年。這個身患白血病且病情嚴重的小女孩,儼然在媒體持續聚焦的“羅爾風波”中成為事件的焦點,她的病情牽動著萬千網民的心。公眾從媒體的報道中獲知,羅爾之女就像她名字中帶有的“笑”字一樣,在生活中是一個愛笑的小女孩;羅爾之女還是一個樂觀堅強、與病魔積極抗爭的白血病患兒。
羅爾之女的形象能夠如此立體地展現在公眾視野中,與媒體在報道中披露了小女孩的大量個人信息密不可分。在相關報道中,大部分報道的標題毫無避諱地直言女孩的姓名,未經處理的患兒生活照被置于報道正文中的情況也不鮮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0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隱私。”《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中明確表示:“維護報道對象的合法權益,尊重采訪報道對象的正當要求,不揭個人隱私;維護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和殘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合法權益。”姓名與生活照屬于隱私中的個人信息范疇,兒童雖然受到監護人的監督和保護,但仍是獨立的權利主體,合法權利受到保護。媒介具有議程設置功能,媒體在對羅爾事件進行報道時,會引發公眾的注意,并促使大家參與到事件的討論中來。一方面,相關報道可以引導公眾的視點轉移,喚起公眾對病情嚴重的羅爾之女的關心和愛護;另一方面,小女孩身患白血病,與身體健康的同齡兒童相異,女童的隱私信息在被媒體曝光后,可能成為網民茶余飯后的談資,從而造成社會歧視等隱性傷害。
媒體在報道羅爾之女時,大多選擇引用羅爾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中已發布的文章,這些文章本身即含有其女的個人信息。雖然這些文章一經公眾號發布,即進入公共視野,但是羅爾作為父親在文章中公開自己女兒的信息和羅爾作為信息源或受訪者主動將女兒的信息公開給媒體,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關于新聞采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第七條規定:“切實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未獲得未成年人監護人的同意,一般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肖像等能夠辨別和推斷其真實身份的信息和影像資料。”媒體在轉引含有羅爾之女的真實信息的羅爾個人文章時,應獲得羅爾的準許,而不應自作主張、不加思考地引用和發布。而有些媒體在報道時,確實在文章中進行了標注。如《5歲愛女突發白血病深圳婦女病房故事感動朋友圈》⑤一文中,在羅爾之女的照片下標有“昔日的笑笑和入院后的笑笑(應受訪者要求不打碼)受訪者供圖”的字樣,表明媒體這樣做是受到監護人許可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得到了監護人的允許,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報道倫理原則和指南》中提及的“兒童利益最大原則應該放在優先地位”,媒體在進行報道時,應該審慎考慮“報還是不報”以及“怎樣報”的問題,避免在文章中披露太多當事兒童的個人信息。
(三)“渲染悲情”與“二次傷害”
社交媒介等媒介形式的崛起,激活了個人湮沒的信息需求與個人操控社會傳播資源的能力,[5]專業新聞機構在互聯網時代陷入更加激烈的競爭之中。競爭是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不可避免的現象,然而,在實際的行業競爭中,有些媒體會選擇不當的競爭方式,制造噱頭,吸引公眾注意力,以期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占據優勢地位,在行業內部站穩腳跟。很多媒體在跟進“羅爾事件”時,選擇在文字報道中放置羅爾大幅的悲傷哭泣、面容扭曲的照片。從視頻新聞中也可以看到,面對媒體的質問,羅爾流著眼淚,訴說著女兒的病情,此時,攝像機的鏡頭齊刷刷地對準羅爾悲傷的面龐。這樣的圖像極具沖擊性,能引人注意,有助于媒體贏得更多發行量或者點擊率,從而在此次事件報道中,占據優勢地位。
在圖片報道和影像報道中,“悲傷”是一個敏感的內容。“悲傷”在一些國家被定義為隱私,在我國并沒有這樣的明確規定,但是處于悲傷時刻時,個人的悲傷仍然不愿意被他人感知。美國著名攝影評論家桑格塔在《關于他人的痛苦中》指出:“好的新聞,要關乎他人的痛苦。”[6]然而,這并不是指傳媒從業者在進行新聞報道時可以放大被訪者的“悲傷”并呈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中,而是要求其在實際采訪時多加考慮,審慎行文。
是否在具體的報道中選用沖擊力強的圖片或者影像去“渲染悲傷”,其實反映出了新聞報道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觀念的沖突。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淵源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兩類。其中,價值合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為的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是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自己要達到的目的,而不管結果如何。工具合理性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追求工具理性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7]媒體若一味遵從工具理性的價值觀,為追求眼球經濟、博得關注而過多報道被訪者的悲傷情緒,會導致被訪者內心的痛苦被無視,這實在有失人文關懷。
美國新聞工作者協會(SPJ)在其制定的《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道德守則》中,強調了“減小傷害”的重要性。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全體會員相信有道德感的新聞工作者,對待新聞來源、新聞人物和自己的同事都必然抱有應有的尊重和人文關懷。為了遵循“減小傷害”的原則,新聞工作者應該做到“對那些因為新聞報道而可能受到負面影響的人表示同情;在采訪或拍攝受到悲慘或不幸事件影響的人物時保持應有的謹慎與敏感”。同時,要能夠意識到“采訪和報道新聞的過程可能會給他人帶來傷害或不快,新聞采訪的權利并不等于傲慢自大的通行證”。
然而“羅爾事件”中,媒體在采訪羅爾的過程中常常單刀直入,用尖銳犀利的問題質問羅爾,甚至談及其女的病情時也并未語帶婉轉。這樣的采訪方式,可能造成“侵擾悲痛”,羅爾在承受著女兒患重病的傷痛的同時,還經受著媒體造成的“二次傷害”。為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媒體對羅爾的采訪中,提出的問題應力求信息量,以還原事件真相、澄清不實言論,但與此同時,要注意“最小傷害原則”的運用,應該考慮到羅爾不僅是一個關切公共利益的事件的主體,更是一個患病女童的父親。另外,媒體還需堅持“善意原則”,無論在采編前掌握了關于羅爾的什么材料,也不應該從一開始就把羅爾當作被質問和批評的對象,而應陳述事實并給予羅爾發聲的權利。
四、結語:公益需要愛心與善意
小笑笑最終沒有戰勝病魔,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016年。隨著羅爾女兒的病逝,“羅爾事件”會慢慢平息,輿論的大潮也終將退去。回顧整個事件,網絡空間中不同的聲音爭論不休,在爭論之下卻少了幾分對于病人本身的關心與愛護。小女孩的離世讓公眾感到難過與惋惜,在痛心的同時,或許應該多加思考。當發現位于輿論漩渦中心的個人正處于困境中時,一味地站在高緯視角對其進行道德評價似乎有失善意。換位思考,而不是以己度人,或許才是善舉。
羅爾之女已經離開人世,但是社會中不乏有著相同或者相似境遇的群體。如今,中國的社會保障尚不完善,社會公益慈善領域的救助是有效的輔助手段。公眾應將愛心與善心轉移至身處困境的群體,給予其關注與關心,而不是只將視點聚焦個別社會動員能力強的求助者。
斯人已逝,信息爆炸的今天,被其他信息沖擊后,公眾對于“羅爾事件”的記憶或許并不長久。或許,深入反思現行慈善制度,促進全社會范圍內達成公益共識,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是將“羅爾事件”銘記在心的最好方式。
[本文為2010—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媒介融合環境下傳媒法規與倫理研究”(項目編號:10BXW016)成果之一]
注 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21條。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23條。
③王志安微博,《羅一笑賬單》,2016年12月25日。
④新華社新媒體專線(廣州):《羅一笑“走了”留下的爭論仍在繼續》,2016-12-25。
⑤《5歲愛女突發白血病〓深圳婦女病房故事感動朋友圈》,《深圳晚報》,2016年11月30日。
參考文獻:
[1]范紅霞.微信中的信息流動與新興社會關系的生產[J].現代傳播,2016(10).
[2]陳玉卿.公益詐捐法律問題的分析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2014.
[3]雅克·蒂洛,基斯·克拉斯曼.《倫理學與生活(第九版)》[M].程立顯,劉建,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68.
[4]范嬌.大眾媒介(新聞)報道侵犯未成年人隱私權研究[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1(4).
[5]喻國明.互聯網環境下的新型社會傳播生態[J].中國廣播,2016(9).
[6]朱德泉.悲劇、隱痛與殘酷呈現[J].青年記者,2015(6).
[7]王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理解韋伯的社會學思想[J].甘肅社會學,2005(1).
(王軍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網絡新聞與新媒體碩士生導師;王璇、朱珊珊為中國傳媒大學網絡新聞與新媒體2016級碩士生)
編校:鄭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