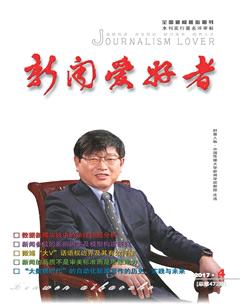美國青少年的網絡使用和家庭監管
李凌凌
【摘要】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各種電子媒介滲入世界的角角落落,對處在人生重要發展階段的青少年來說,數字媒體使用的情況關涉他們的身心發育和社會化過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美國全國性調查中獲得的數據和對美國青少年家長的面對面訪談,得知美國家長普遍介入青少年孩子的網絡生活,采取多種方式監管孩子的在線活動。參照美國的經驗,我們應變“圍堵”為“卷入”,經常和孩子溝通,制定網絡使用規則;采取技術手段管理青少年的接入內容及接入時間,幫助青少年在有效利用網絡和規避網絡風險之間找到平衡點。
【關鍵詞】美國;青少年;網絡使用;家庭監管
隨著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的普及和互聯網對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加速滲透,數字化生活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8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5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未成年網民(18歲以下)規模為1.34億。在信息獲取、網絡娛樂、交流溝通、商務交易四大類互聯網應用中,除網絡游戲外,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群體各項應用使用率均低于25歲以下人群的平均使用率,只有網絡游戲以69.2%的使用率超過25歲以下網民平均使用率2.7個百分點。對1161位青少年家長進行的網絡問卷調查發現,家長對孩子將業余生活投入到網絡娛樂很擔憂。42.5%的家長不支持青少年將業余生活投入到網絡娛樂中,69.5%的家長會擔心孩子由于網絡娛樂影響了正常的學習和生活。家長對孩子網絡生活的監管集中在控制孩子上網時長上,84.9%的家長會控制孩子的上網時間。很多家長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監管孩子網絡生活方面應該承擔的責任和能夠采取的措施,而是希望政府能夠承擔起這一責任。73.6%的家長認為政府對網絡娛樂內容的監管應該更加嚴格。①
和上述現實相適應,我國現有青少年網絡使用的研究集中在網絡成癮,尤其是游戲成癮等網絡偏差行為上,對父母應如何指導和監管孩子使用互聯網缺乏應有的關注。那么,在互聯網的起源地美國,青少年的網絡使用和家庭監管情況如何,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樣的啟示?本文利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報告,結合對一些美國青少年和家長的面對面訪談,試圖從中尋求經驗。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來自一項對美國13—17歲青少年及其家長的全國性調查,調查時間為2014年9月25日—10月9日和2015年2月10日—3月16日兩個時間段,樣本總量為1060組(每組為一名家長和一名青少年)。訪談資料來自筆者在美國訪學期間,于2016年11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就青少年的網絡使用和監管問題對30位青少年家長、教師和學生分別進行的面對面訪談,訪談地點為當地教堂和學校。
一、美國青少年使用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情況
和中國孩子一樣,美國青少年也花費大量時間在網絡媒體上。在皮尤的報告中,幾乎所有(92%)的受訪青少年都表示,自己每天都會上網,且多數人(56%)每天多次上網,只有6%的青少年表示一周上一次網,12%的青少年會將他們的數字活動限制在每天一次。研究表明,對移動設備的使用會促使青少年增加上網時間,絕大多數(94%)使用移動設備上網的青少年每天都會上網,甚至比較頻繁。使用互聯網的情況也體現出一定的種族差異。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青少年更可能“經常上網”(分別為34%和32%),而白人青少年只有19%。分析顯示,這可能是由于非洲裔美國青少年擁有智能手機的比例最高(85%),移動設備的便攜性和對碎片化時間的利用導致了上網時間的增加。
美國的青少年沉迷于什么樣的社交媒體服務呢?最受歡迎的社交平臺當屬Facebook(臉書),大多數(71%)13至17歲的青少年都表示他們使用Facebook。第二受歡迎的是照片分享服務Instagram,有52%的青少年使用。90%的美國青少年日常使用手機短信和家人朋友溝通,33%使用智能手機的青少年表示會使用即時通信應用程序,比如Kik和WhatsApp(瓦次普)。②
阿曼達(女,40歲,初中教師):“我們學校幾乎每個學生都有手機,智能手機大概占70%。但學校不允許把手機帶入教室,只能放在柜子里供上下學的路上使用。我們鼓勵學生積極使用互聯網,家庭作業經常需要學生上網完成。我們也會在一個網站上和家長及學生互動,發送通知及學生的成績單。因為學校里不允許學生使用個人電腦,因此監管孩子網絡生活的責任主要是家長,而不是學校和政府。”
賈斯丁(男,14歲,初三學生):“我每天上網的時間估計有三四個小時,除了戶外活動,其他在家的時間基本上在網絡中。完成作業之后,主要在網上看視頻、聽音樂以及在社交媒體上和朋友聊天。父母有時會檢查我下載了什么軟件、瀏覽過什么網站,但我覺得他們是多慮了。”
二、美國父母對青少年網絡生活的關切
美國的父母普遍關注孩子在網上看什么、做什么、和誰互動、行為是否得體、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為了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網絡生活,大多數父母也試圖提前和孩子討論互聯網使用規則,告知孩子什么是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網絡行為。由于國情不同,美國和中國家長對孩子在互聯網使用中的關切和擔心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體現在對孩子網絡使用時間過長影響學習、接觸不良網絡內容影響身心健康、網上泄露隱私和線下約會網友危害人身安全等。
艾米(女,50歲,社會工作者):“我有5個孩子,我對他們共同的擔心是無意義地上網和發送短信浪費了寶貴的學習時間。你不可能一直盯著他們。當大人忙時,他們就會一直上網和玩手機。網上好的東西很多,但他們不是一直對好的東西感興趣。對男孩和女孩,我也有不同的擔心。對男孩子,主要擔心他們參與網絡暴力游戲和觀看網絡色情片。對女孩子,我擔心她們卷入一些情感陷阱。我的女兒曾經問我能否會見網友,我的回答是:‘你不能和一個你不了解的人單獨見面。如果實在要去,我和你一起去。”
瑞查(男,58歲,計算機項目經理):“我的女兒今年15歲,大多數像她這個年齡的孩子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照片、建立聯系。有的女孩子在網上交到很壞的男朋友,見面后對她們進行虐待和控制。我擔心她在網上被壞人盯上,誘惑她線下見面并利用她。所以我總是和她分享那些女孩子會見網友受到凌辱的新聞故事,希望她能認識到該如何保護自己。”
和我們國情不同的是,美國對網絡內容的管理十分寬松,這使得孩子們可能在網上接觸到的內容五花八門,美國家長對網絡霸凌、恐怖主義宣傳和各種古怪的網絡小組有更深的憂慮。
迪安(男,50歲,政府雇員):“我對青春期的孩子上網有很多擔心。瀏覽色情內容和恐怖組織的招募是最主要的憂慮。我在孩子的計算機和手機上安裝過濾軟件和監視裝置。但是我也知道他們能夠在其他地方上網。我試圖使他們理解網上有些東西對所有年紀的所有人都沒有好處。事實上我對一些虐待狂的擔心還要勝過色情視頻。我們和其他的家長也擔心一些古怪的網絡小組試圖吸引孩子,比如自殺小組或邪教。我想多和孩子交流,多在孩子身上花費時間是最好的防范辦法。”
瑞秋(女,48歲,家庭主婦):“我擔心的是網絡霸凌,也就是孩子在網絡社區中被粗暴地沒有尊嚴地對待。被同輩群體欺辱對孩子自信心的影響是長期的和摧毀性的,而且他們也會從中學習如何對待他人。”
吉姆(男,50歲,企業家):“我有4個男孩,分別是17、16、14和11歲,孩子們幾乎每天都上網。我對他們網絡生活最大的擔憂是被戀童癖盯上。所以我非常留意他們登錄的網站和瀏覽的內容。盡管經濟允許,但我并沒有給他們配備個人計算機,而是讓他們共享放在起居室的兩臺家庭計算機。這樣當我穿過起居室忙于各種家務時,我就能夠隨時裝作不經意地瞟一眼他們的屏幕。”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和這些個案訪談可以相互印證。數據顯示,95%的家長曾經和孩子討論過什么樣的網絡內容適合他們瀏覽,39%的父母經常這樣做。95%的家長曾經和孩子討論過什么類型的媒體適合他們消費(諸如電視、音樂、書、雜志和其他媒體),36%的人經常這樣做。94%的父母說他們和孩子討論什么內容適合他們進行在線分享,其中40%的父母經常這樣做。92%的父母曾經和孩子討論他們在網上應如何對待他人,36%的父母經常這樣做。低齡組孩子的家長也更頻繁地和孩子討論什么內容適合網絡分享,應該消費什么媒體的內容以及如何在網絡上對待他人。比如13—14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有49%頻繁和孩子討論應該在互聯網上瀏覽什么內容,15—17歲孩子的家長有32%這么做。③
其他的研究也表明了類似的模式,父母通過談話,讓孩子了解在線的行為規范似乎是普遍現象。2015年常識媒體報告顯示大多數青少年說父母和他們討論過網絡安全和責任意識。④
三、美國父母如何監管青少年的網絡生活
美國的父母采取各種行動監管孩子的網絡生活,鼓勵孩子以適當和負責任的方式使用科技。父母采取的管理方式多種多樣,從檢查孩子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分享到限制孩子的上網時間。幾乎所有受訪家長都提到要和孩子加強交流,通過交流了解孩子的網絡生活并進行管理。
馬克(男,50歲,企業家):“和現實世界一樣,互聯網上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好的壞的,美的丑的,安全的危險的,合法的非法的,有用的沒用的。作為家長,我主要關切的是希望我的孩子明白這些東西之間的區別,不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或者丑陋的網絡活動中。除此之外,色情和暴力內容的影像、圖片、游戲和歌曲也很危險。在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告訴他們關于互聯網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開放地和他們討論性和其他危險。”
皮特(男,45歲,工程師):“今天的孩子過度地曝光于互聯網環境之下,我對這種狀況感到擔憂。有些網絡內容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沒有父母的指導,在互聯網上玩暴力游戲的孩子很可能以為生活中也可以這樣對待他人。你必須和他們不斷交流,幫助他們建立社會生活和網絡生活的規則,晚餐時間通常是分享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時刻。”
總體來說,84%的父母采取至少6項措施(檢查孩子訪問的網站,檢查孩子的社交媒體個人資料,查看孩子的電話和短信記錄,使用家長控制軟件來屏蔽、過濾和監視孩子的在線活動,使用家長控制軟件來限制孩子的電話使用,使用電話監控軟件來追蹤孩子的地理位置)中的一項來監控或者限制孩子的網絡活動,其中16%的父母說他們采取一項措施,45%的父母采取兩項或者三項措施,19%的父母采取四項或者五項措施,5%的父母采取全部六項措施。16%的父母不采取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項。
在對孩子網絡生活的監管上,61%的父母說他們檢查孩子訪問的網站,60%的家長說他們檢查孩子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資料,56%的家長關注孩子在Facebook、Twitter(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的賬號,48%的家長檢查孩子的電話通話和短信記錄,48%的家長知道孩子的E-mail賬戶密碼,43%的家長知道孩子的電話密碼,35%的家長知道孩子的至少一個社交媒體賬戶密碼。
麥瑞(女,46歲,金融工作者):“我有兩個男孩,一個16歲,一個14歲。我信任我的孩子,但我必須經常檢查年齡尚小的他們是否能夠擔當起這份信任。我經常偷偷地檢查他們經常使用的一些軟件及網址,看是否涉及不當的內容。網上有各種各樣的小組吸引孩子們,有些小組的活動非常怪異,完全不可接受。一旦發現,我就必須立即嚴肅干預,并修復可能已經產生的傷害。我們也使用家長控制軟件為孩子過濾內容。”
索菲亞(女,45歲,教師):“我的辦法是認識她每一個生活中的朋友,關注她所有的社交媒體賬戶,和她討論各種可能的危險,掌握她網上賬戶的密碼,經常查看和評論她發送的內容。我也告誡她和她的朋友們永遠不要把自己和朋友的個人信息比如出生年月、地址和電話號碼等發送到網上。”
低齡組孩子父母的監管力度超過高齡組孩子的父母。比如,68%的13—14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檢查孩子們訪問的網站,56%的15—17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這么做。在13—14歲年齡組孩子的家長中有69%規定孩子什么時候可以上網,以及上網多長時間,15—17歲年齡組的家長只有46%這樣做。
可見,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父母所給予孩子的自由度也隨之增加。13—14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有54%知道孩子的E-mail賬戶密碼,15—17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有44%知道它。41%的13—14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知道他們的社交媒體密碼,而15—17歲年齡組孩子的父母有29%知道它。
但在檢查孩子使用社交網站時的數據不符合這一規律,15—17歲年齡組孩子的家長63%檢查孩子的社交網站上的個人信息,13—14歲孩子的家長為56%。這可能跟年齡更大一些的孩子使用社交平臺的機會更多有關。
種族和教育程度不同的父母在這個問題上有所不同。白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傾向于更嚴格地管理孩子的互聯網使用。白人家長有51%知道孩子的E-mail賬戶密碼,拉丁裔的家長有39%知道它。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有50%以上知道孩子的E-mail賬戶密碼,而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家長只有42%知道它。
由于技術在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父母威脅收走數字化設備是一種強有力的懲罰方式。事實上,65%的父母把沒收孩子的手機或取消孩子的上網權利當作一種懲罰。
一些美國家長使用科技工具來監控、限制或追蹤孩子的在線行為。“無線通信提供商T-Mobile說它有400萬顧客使用免費服務來阻止孩子接入涉及性、暴力和謠言的圖片和內容。它還有375000用戶每個月付4.99美元定制‘FamilyAllowances服務,這項服務讓父母可以阻止孩子和某些電話號碼通話或者短信,在學校和做作業的時間關閉手機,以及監視他們發了多少短信。T-Mobile還有大約100000用戶每月付9.99美元定制另一項服務‘Family Where,這項服務讓父母可以追蹤孩子的地理位置。最近,像蘋果公司這樣的電話制造商甚至可以把‘家庭成員定位服務直接嵌入他們手機的免費軟件中。”⑤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表明:39%的家長使用家長控制工具(如一些監控軟件)限制、過濾或監控青少年的在線活動。16%的家長使用家長控制工具限制孩子使用手機,16%的家長使用監控工具監控孩子的電話,追蹤他們的地理位置。⑥數據顯示,在利用技術監管青少年的網絡活動方面,仍有較大潛力可供開發。
四、討論:美國家長對青少年的監管行為給我們的啟發
數字媒體的使用是不可回避的社會趨勢,對處在人生重要發展階段的青少年來說,數字媒體使用的情況關涉他們的身心發育和社會化過程。作為互聯網技術的發源國,美國人的網絡應用起步較早,網絡普及率為87.4%,明顯高于我國的51.7%。在13—17歲受調查孩子的家長中,94%擁有桌面或便攜計算機,76%擁有智能手機,72%使用Facebook,84%至少偶爾使用智能手機或其他移動終端上網。⑦這使得當今美國青少年的父母普遍具備較高的媒介素養和互聯網使用技能,因而可以有效地指導孩子的互聯網使用,并努力采取措施減少或消除風險。
但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由于各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青少年父母的網絡接入情況和網絡使用能力存在比較明顯的地區差異。“網絡媒體在家長中的實際使用率很低,家長主動、有效利用網絡的能力欠缺。更多的家長對網絡有偏見。家長們對孩子使用網絡普遍采用限制、圍堵的方式。”[1]
信息社會的到來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現實。及早習得互聯網使用的有關技能是成為信息社會公民的必要條件。缺少溝通、強行圍堵的方式不但無法幫助青少年建立起正確的互聯網使用規范和習慣,而且還會破壞代際信任,惡化親子關系。在美國青少年的互聯網使用上,父母的監管沒有缺位,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長,對孩子的互聯網使用管理越嚴格。另一方面,幾乎所有訪談對象都強調和孩子的溝通以及對孩子網絡生活的關切。“圍堵”不如“卷入”,家長如能經常和孩子討論互聯網生活,在青少年的互聯網使用上制定規則,采取一些技術手段管理青少年的接入內容和接入時間,將能夠幫助孩子在有效利用網絡和規避網絡風險之間找到平衡。
借鑒美國的經驗,本文為中國家長監管青少年的網絡生活提出以下建議:
(1)采用家庭共享的方式使用接入設備,盡可能延遲給孩子配備個人電子設備,如計算機、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的時間,并把共享設備密碼作為孩子使用電子設備的前提。比起個人電腦,手機的使用更加便捷也更加隱蔽,不僅導致孩子上網時間的增加和在學業上的分心,對孩子的視力也更具負面影響。因此,如果確實需要給孩子配備手機方便聯系,最好配備只用于簡單通信的非智能手機,從而把上網活動限制在家庭共享電腦上。
(2)把計算機放在家庭的公共生活區而不是孩子自己的房間。父母可以利用在公共區域中的頻繁走動隨時對孩子的網絡活動予以關注,同時當孩子們意識到父母隨時有可能走過來時,他們通常也會約束自己。相反,如果允許孩子在自己的房間里使用電腦,可能當你發覺問題時,大錯已經釀成。
(3)規定每天什么時間可以使用互聯網以及使用多長時間。如果沒有硬性的約束,即使成人也會經常在互聯網上浪費很多的時間。強制執行媒體使用的家庭計劃,如完成作業之后才能使用互聯網,每次使用不超過一定時間,禁止在進餐時間和睡前使用包括手機在內的媒體設備,幫助孩子養成自我管理的習慣,擺脫網絡拖延癥,這有助于學習目標的達成。
(4)經常和孩子探討網絡生活,教會孩子在互聯網上保護她(他)的隱私以及得體地和他人互動。不暴露自己和他人的真實身份、家庭地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身份信息;不參與互聯網上的人肉搜索和霸凌活動;不在沒有成人陪伴的情況下會見網友。
(5)培養批判性思維,幫助孩子學會分辨網上的信息來源,評估網上內容的質量。比如權威信源和一般信源,普通網友上傳的內容、業內專家上傳的內容和有關機構官網提供內容之間的差別。幫助孩子借助常識和檢索識別謠言,提高互聯網使用的質量和效率。
(6)教育孩子認識到網絡分享中有些內容可能是危險的。比如傳播謠言或上傳自己的裸露照片、親密行為等。雖然有些軟件允許發送者在一定時間內撤回信息,但如果對方立即截屏,他就能夠保留相關信息。利用一些新聞故事讓孩子明白,這些信息可能會在某一天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
(7)使用軟件幫助過濾內容或者限制上網時間,監管孩子的網絡活動。很多電子設備本身內置家長控制軟件,應該學習并加以利用。中國的軟件和通信服務商也應努力開發適合中國家庭監管的軟件產品,做好有關技術和服務的應用推廣,降低用戶使用的技術難度和經濟門檻。
(8)年齡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嚴格監管。而隨著孩子年齡和經驗的增長,可逐步賦予其更大的自由空間。同時,對不同年齡和性別的孩子,關切的重點應有所不同。
(9)對于那些不熟悉互聯網的家長,大眾媒體和學校有義務對家長進行數字化素養的培訓,指導他們采取合適的手段來監管孩子的網絡活動。
[本文為河南省教育廳201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電子媒介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013-ZD-094)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5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研究報告》,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
②皮尤最新報告:美國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調查2015,http://ww
w.wtoutiao.com/p/ybdVqp.html.
③Pew research center:Parents,Teens and Digital Monitoring,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1/07/parents-teens-and-digital-monitoring/.
④Pew research center:Parents,Teens and Digital Monitoring,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1/07/parents-teens-and-digital-monitoring/.
⑤Nick Wingfield,Should You Spy on Your Kids?The New York Times,NOV.9,2016.
⑥Pew research center:Parents,Teens and Digital Monitoring,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1/07/parents-teens-and-digital-monitoring/.
⑦Pew research center:Parents,Teens and Digital Monitoring,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1/07/parents-teens-and-digital-monitoring/.
參考文獻:
[1]魏南江,孔祥靜,唐承群.中小學生網絡媒介素養及其教育現狀的調查——以江蘇省17所中小學為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4).
(作者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American University訪問學者)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