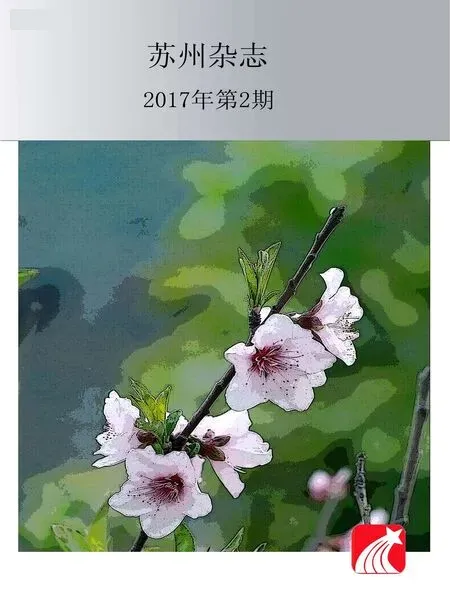杭鳴時印象(下)
姜紅
杭鳴時印象(下)
姜紅

杭鳴時粉畫的啟蒙老師是他父親的學生、后來成為他姨父的李慕白先生。在杭鳴時母親王蘿綏30歲生日時,李慕白為她畫了一幅粉畫肖像。雖然杭鳴時對這幅畫當時的創作不太有印象,但母親的這張色彩淡雅、形象俏麗的肖像畫,最初是掛在上海永安公司文房部作為招徠廣告之用的。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畫初識粉畫之妙,并和粉畫結緣的。這幅畫一直陪伴他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歷經歲月洗禮。今天看來,畫面里母親恬靜端莊的儀容透露出絢爛至極的平淡,溫暖慈愛的眼神穿越塵封的歲月直抵人心。他說,對于很多擔心粉畫保存問題的人來說,母親這張栩栩如生的肖像畫就是最好的證明,粉畫收藏不懼歲月。
1962年,杭鳴時從沈陽回到上海,李慕白送給他一盒有200多種顏色的法國鐵錨牌粉畫筆和兩張帶有羊絨成分的法國粉畫紙。當時,他舍不得動用這些彌足珍貴的粉畫紙,就在魯美不到9平方米的斗室中,用從五金公司買來的墨綠色金相砂紙試著畫小張人物肖像。粉筆飽和的色彩、極強的表現力讓他對粉畫的喜愛一發不可收。1980年,他完成了表現女體操運動員的《上杠之前》,接著又創作了《魯迅在版畫展上》。談及對粉畫的一往情深,杭鳴時有些激動,他覺得粉畫就是一個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少女,只要和她一朝邂逅,無不被她艷麗的氣質與獨特的情懷所打動。
至此,杭鳴時和粉畫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轟轟烈烈的“戀愛”,并結出一個個豐碩果實。一方面因為家學淵源,他從父親月份牌畫中汲取繪畫技藝,一方面結合后來在魯美系統的學院派素描教育培訓,兩者相得益彰,再博采眾長,融入自己對繪畫獨特的理解和創新。我國著名的美術史論家朱伯雄評論他的粉畫人體堪稱一絕,嚴謹的寫實功力,嫻熟的運色技巧,粉畫人體的皮膚真實、柔和、細膩得就像有溫度,會呼吸一樣。
1984年,杭鳴時的粉畫作品《泳裝少女》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被評為優秀作品,開創了粉畫入選全國綜合性美展的先河。1998年,他的粉畫《柯橋夕照》榮獲美國第26屆粉畫大展一等獎,這是繼顏文樑先生的《廚房》獲法國沙龍獎后,第二位獲得國際大獎的中國粉畫家。1999年,粉畫《山城》入選美國第27屆粉畫大展,獲專業畫家聯盟頒發的“優秀畫家獎”。2001年粉畫《水鄉蟬聲》入選美國第29屆粉畫大展,獲德加粉畫學會頒發的優秀獎。接二連三在美國獲獎,被譽為“粉畫巨子”,使他獲得了以后參展作品可以免審的資格,并成為美國粉畫協會會員、國際粉畫協會會員,所有這些奠定了他在國際粉畫領域的影響和地位。
如果故事只是到這里,那杭鳴時也就是在粉畫的世界里流連忘返、樂享其成而已,既不可能有今日的“杭鳴時粉畫藝術館”,也不可能有今日中國粉畫星火燎原的蓬勃發展。
他說,他要的不是自己的一花獨放,萬紫千紅才是春。這令人想起他的父親杭稚英。杭稚英剛剛琢磨擦筆水彩月份牌的畫法時,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比他早采用此技法的畫家鄭曼陀是怎么作畫的,幾次三番請教,對方總是避而不談。后來自己琢磨出是用炭精粉代替墨色渲染這一竅門后,又對技法進行改進,用原本修補照相底版和印刷制版的噴筆來調整畫面色調,表現色彩的細膩過渡,使畫面虛實有致,主次分明。一時間,同行們對此欽羨不已,凡是登門請教的,杭稚英都會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自己所用技法,并且當場示范,直至對方弄懂學會。為什么他不怕泄露天機?除了對自身實力的自信之外,他更懂得,好的技法只有讓更多人了解掌握,才能創造出月份牌畫的新天地。而且,新的技法會層出不窮、不斷創造,如果墨守某一種技法,勢必學不進其他新的技法,就會被淘汰出局。
和父親杭稚英當初廣泛傳播月份牌技法如出一轍,為了讓更多人學習粉畫技法,杭鳴時舉辦了多期粉畫研修班,應邀去各地大專院校以及美術愛好者群體中示范粉畫技法,為我國培養了一批粉畫骨干。現在,他的一些學生已經在各自的高等院校開設了粉畫必修課和選修課,他撒播的粉畫種子,正在各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了壯大粉畫隊伍,他總是利用一切機會,不厭其煩地逐一給作者打電話、寫信、寄作品、送粉畫工具材料,用一腔熱情去感召對方。如今全國的粉畫創作人員已經從當初的8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
2012年,央視書畫頻道欄目組來蘇拍攝了24集《杭鳴時粉畫教學片》,把他幾十年潛心實踐探索的粉畫技法記錄下來,傳播出去。2013年12月“中國粉畫藝術網”開通運行,中國粉畫學會籌備工作也在進行中。
2014年首屆中國大學生粉畫作品展在蘇州“杭鳴時粉畫藝術館”舉辦,全國64所高校共有349人有效投稿443件,覆蓋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參賽作品涉及題材廣泛,表現形式多樣,兼具藝術性和觀賞性,已具相當水平。大學生群體的踴躍參與和高品質的粉畫作品,充分證明了粉畫創作后繼有人。杭鳴時這么多年的奔波努力得到了最好驗證。他說,粉畫就是他的孩子,從尚在襁褓到蹣跚學步,從牙牙學語到成長為活力四射的少年,每一步都不容易,每一步都讓他欣喜。
他就像一座燈塔,用幾十年積蓄的能量,默默吸引愈來愈多的人加入粉畫創作的隊伍。對于粉畫今日方興未艾的喜人局面,他淡定地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他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踐行了自己25年前的承諾。
2013年,蘇州粉畫邀請展順利開幕,在邀請展的學術研討會上,著名粉畫家王相箴說,半個月以前跟杭老師通電話,杭老第一句話就說:“身體怎么樣?我們要為粉畫多活幾年啊!”王相箴說,他接了這個電話,特別震撼,自己是想多活幾年,但是從沒想過要為粉畫多活幾年。可見杭老日思夜想的就是粉畫。短短一句話,如此本真地顯露自我,無須再加修飾或解釋。
“只要對粉畫發展有用的事情我都會努力去做。趁我去見馬克思以前,希望自己還能為粉畫做一點事情。能多畫一張就是一張,能多教一個人就是一個人。”
我就是要創作雅俗共賞的作品
大鋼琴家霍洛維茨說:“我用了一生的努力,才明白樸素原來最有力量。”這句話用在杭鳴時身上,我覺得再貼切不過。他著裝普通樸素,神態像一個兒童。因為肚中有貨,心里有數,不必借助各種花樣。他堅持有所不為然后有所為,他義無反顧又舉重若輕。他質樸、清淡、簡約,無旁逸斜出、繁榮奢華。他寬容、謹慎、執著,不工于心計察言觀色,不刻意揣摩營造人際氛圍。他的語言平淡樸實謙卑,沒有更多修飾,和他簡單樸素的家一樣,總是在不經意中打動我,讓我肅然起敬。樸素的藝術是最好的藝術,就像玉質文章,含蓄蘊藉,謙沖雅靜,盡得風流。杭鳴時的藝術人生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想,那就是樸素。
許多藝術家都會選擇在風景秀麗的郊外置別墅以怡情養性,杭鳴時的家,卻在蘇州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大隱隱于市,你無法把這樣一個地方與粉畫大師聯系起來。夫婦倆不會開車,也沒有雇請保姆照顧起居。他們就和普普通通的大多數人一樣,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走進他們家,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畫。原本寬敞的房間被四處堆放的畫作塞得有些擁擠。奇怪的是,我們面對滿室畫作一點都不感到逼仄,反而感覺視野開闊,神清氣爽,也許這就是藝術的魔力。家境優越,從小就有保姆跟在身后收拾東西的杭鳴時,現在反而不習慣請保姆,他說,家里東西太多,他又喜歡隨時畫畫,保姆清理好東西反而會讓他覺得亂,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久而久之,他們也就習慣了在畫室一樣的家里生活。
藝術家最隱秘的世界,每每潛藏在他作品的深處。因此不管他畫什么,總像有個隱身人以不易察覺的方式游蕩其中,并將自我的精神、氣息與想象賦予那些剛剛生發完成的事物,使之獲得應有的形象、光影,以及虛實交錯的時空。
杭鳴時強調,畫家要“以畫說話”,要把真善美作為藝術創作的靈魂,創作老百姓喜歡看的雅俗共賞的作品。在當前藝術創作多元化的背景下,藝術創新和多樣化不可避免。他旗幟鮮明地說,自己厭惡那些盲目照搬西方藝術觀念和形式,丑化中國形象,傷害民族自尊,既無視傳統中的經典,又不去反映生活中的美,還要裝模作樣、自吹自擂的所謂作品。藝術家的使命就是要通過自己的作品,把從生活中發現的真、善、美表達出來,傳遞給廣大人民群眾,同他們一起分享,讓觀眾從作品中得到振奮、愉悅,凈化心靈。
對于父親杭稚英的藝術思想和在月份牌畫上取得的成就,杭鳴時認為這一切源于父親的善于學習和善于創新。無論是破解鄭曼陀秘而不宣的新仕女畫法,還是吸取美國迪斯尼動畫和西方廣告畫擅用色彩的營養、重視素描、走中西合璧的藝術道路,父親在藝術上不妄自尊大,打破門戶之見,不僅鼓勵弟子去其他畫室進修,在藝術創作上也采用最好的繪畫工具和材料,大膽借用噴筆等新式工具創作畫面處理的新技法。
受父親創新意識潛移默化的影響,杭鳴時的藝術視野非常開闊。在魯藝4年,盡管沒有出國門,但他翻閱了學校圖書室里所有藏書,有他喜歡的畫作他就會盯住不放。魯藝的館藏豐富,他說這是他對學校最滿意的地方。在父親家學的擦筆水彩基礎之上,他一頭扎進圖書館,孜孜不倦地汲取營養。各種畫作展覽他更是一次不落,對名作的臨摹是他功成名就后至今沒有放下的功課。在他家里,我見到了他最近臨摹的安格爾的《泉》。他說,安格爾的《泉》反映了他心中理想的晚年的美,使得他心中長期積聚的抽象出來的古典美與具體的寫實少女的美,找到了完美的結合。
安格爾一生在裸體素描上下過精深的功夫,毋庸置疑,杭鳴時受安格爾影響很深。安格爾說:“一幅畫的表現力取決于作者豐富的素描知識。撇開絕對的準確性,就不可能有生動的表現;掌握大概的準確,就等于失去準確;那樣,無異于在創造一種本來他們就毫無感受的虛構人物和虛偽的感情。”杭鳴時說他就是按照這樣一種態度來創作筆下的每一幅作品。但他并不受限于安格爾,他覺得安格爾的裸體畫少有揭示人物內在精神,過于注重形式和技巧。
盡管在藝術創作道路上,他不墨守陳規,敢于也善于兼容并蓄,但是對于自己的藝術主張,他又像九斤老太,絕不遷就。他是一個善于博采眾長而又堅持自己見解的藝術家。他堅持自己追求真善美和雅俗共賞的藝術觀點,堅持用寫意的手法畫出寫實的效果,皓首窮經,任爾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永遠不在滾滾紅塵中迷失自我。
在杭鳴時丁薇伉儷粉畫展畫冊的封底,他寫道:“人生苦短,不經意間居然活到了80后,回顧幾十年來風風雨雨,用成語‘不堪回首’似乎太消極,但確實不容易。我癡迷繪畫,既有傳統,又喜歡新潮。在社會主義轉型期也曾經迷惘過。但我認為藝術就是要為群眾服務的,否則只能是自說自話,自以為是。和群眾不相干的藝術是沒有生命力的。我畢生追求的是寫實寫意并重,以寫意的筆法出寫實的效果,雅俗共賞和真善美,群眾喜聞樂見,我就開心了,僅此而已。”
寥寥數語是他對自己藝術道路心路歷程的總結。畫家是為老百姓服務的,一幅作品,如果老百姓連看都看不懂,怎能引起共鳴呢?唐代詩人白居易是他最喜歡的詩人,因為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婦孺皆知,廣為流傳。杭鳴時認為,畫的風格沒有新與舊、高與低可言,具象與抽象、寫實與寫意各有千秋,關鍵在于作者對待藝術是否真誠,對待人民是否平等。他不喜歡孤芳自賞,也不喜歡高深莫測、玄而又玄的理論。他就是簡簡單單,樸樸素素,把老百姓看得懂的,自己感動的,認為美好的東西奉獻給大家。《南方油畫》主編吳楊波認為,經過一個世紀的分分合合,杭鳴時的作品中真正體現了人民性,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人民性,樸素而有生命力。對于一些所謂“新文人畫”,他說,你看這些畫家的妻子一個個都如花似玉,他們筆下的人卻畫得那么丑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米勒曾經說過一段話:“要使人感動,首先要自己感動,要不然再怎樣巧妙的作品都絕不會有 生命。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他建議我去讀一讀黃河清的《藝術的陰謀》。談到這里,他顯得有些激動。他認為美國破壞我們的文藝生產,鼓動那些大的財團收藏我們國內丑化勞動人民形象的畫,大肆吹捧,有些人就跟著亂畫。他說他以前魯藝一個同事的女兒大學畢業后,就是迷迷糊糊地亂畫。有一天,一個法國小姐讓畫廊把她一張畫得很差的畫高價買走了。之后,她傻了,因為再畫畫就不知道是非好壞的標準了。在仔細拜讀黃河清的《藝術的陰謀》之后,我理解了他那天言辭的激動。不管怎樣,正如書的作者所言,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文化冷戰把缺乏文化積累的美國藝術變成了世界藝術。對杭鳴時后來執意不再參加美國的一些畫展的舉動,我更多了些許敬佩。
作為海寧人,他很喜歡他的同鄉王國維,他說,碰到有學生迷糊了,就會推薦對方去看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王國維的三重境界說也正是他對繪畫藝術追求的真實寫照。境界本質上是由“景”和“情”兩個元質構成的,但不論是客 觀的“景”,還是主觀的“情”,都是“觀”——人的精神活動的結果。只有“情”“景”交融,對立統一,才能形成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藝術作品。
對杭鳴時來說,無論是藝術追求上的雅與俗、寫實與寫意、保守與創新,還是生活當中流露的“匪氣”與俠義、世俗與天真,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方面在他身上卻巧妙地統一在一起,構建著他簡單樸素的藝術人生。在他的世界里,閱盡風云之后,蟲兒啾啾,鳥兒鳴鳴,水兒潺潺,草兒芳香,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和諧。
《莊子·天道》曰:“靜而圣,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杭鳴時的樸素何止于外在衣衫、陋室和談吐,更多在于心靈。一個人心靈樸素,猶如蘭生幽谷,不香自香。
他說,年輕時自己也有過爭強好勝,后來看到老子《道德經》中的“圣人之道,為而不爭”,頓時恍然大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巧言令色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才能,忍辱不辯才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
他說:“我不是什么大師,只是一個樸素的藝術匠人,畫老百姓喜歡看的作品而已。”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