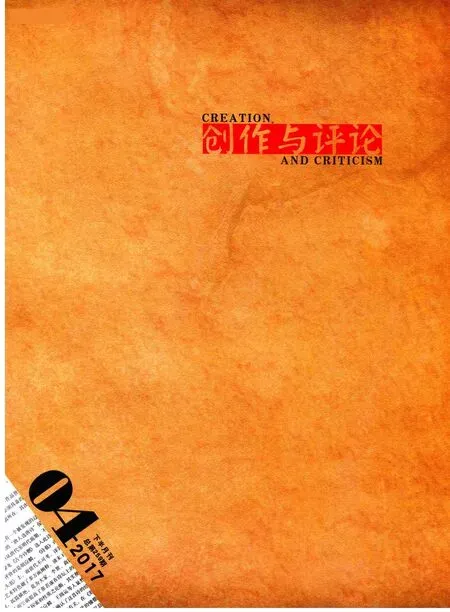從傳統到現代: 文學經典的建構元素
○趙勇
從傳統到現代: 文學經典的建構元素
○趙勇

趙勇
1963年生,山西晉城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專職研究員。兼任北京市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批評、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證法——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法蘭克福學派內外: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大眾媒介與文化變遷: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的散點透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審美閱讀與批評》(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透視大眾文化》(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再版)、《書里書外的流年碎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版)和《抵抗遺忘》(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等,合著有《反思文藝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主編有《大眾文化理論新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修訂版)、《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八卷、第九卷)(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等,合譯有《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在 《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
雖然許多文學作品在其誕生之初就具有了成為經典的潛質或氣象,但它們既無法自封為經典,也不可能被一下子認知,而是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被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一般稱之為“經典化”(canonization)。而在經典化的過程中,種種元素都會參與其中,呈現出一種頗為復雜的格局。但相比較而言,在古代乃至近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元素相對要簡單一些;而在現代和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元素則變得紛紜復雜起來。因為“在文學的周圍圍繞著一個強大的社會群體。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負責文學教育的教師,或各種形式的研究機構、出版社、學術團體、教育部門……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龐大的文學機構,形成一整套對文學作品行之有效的選擇機制,并且逐漸確立了各種文學制度。這些文學機構負責對當代甚至歷史上的作家作品進行挑選、鑒別,衡量價值,確定地位,從中篩選經典。”正是在他(它)們的共同作用下,才導致了文學經典的誕生。
需要說明的是,童慶炳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撰寫過關于文學經典建構問題的文章,其中的分析框架(考察文學經典的建構宜注重內部要素與外部要素)很有價值,歸納出來的六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空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現人或贊助人)也非常重要。但或許是因為從大處著眼,一些更為具體的文學經典建構元素他并未觸及。有鑒于此,筆者以為這一問題依然有“接著講”的必要。
為把問題細化,我們可把文學經典暫分為傳統經典和現代經典,這種區分或許有助于我們重點聚焦于兩類經典建構中的不同面向,也有助于我們思考當今更為復雜的經典化格局。
一、傳統經典的生成元素
這里所謂的傳統經典主要是時間久遠的古代文學經典。雖然這類經典現在看來似已不存在異議,但其形成往往并不一帆風順。在傳統經典的建構中,發現人、選本和評點構成了其中更重要的元素。
1.發現人。所謂發現人就是最早發現某篇文學作品價值的人。發現人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不同時代的好幾個人,他們作為專業讀者所必須具備的品質是:首先他們要有披沙揀金的能力,能在眾多文學作品中發現某篇作品的價值所在。其次,他們要有較大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保證了其發現能被推廣開來。
例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就有一個被發現的過程,其中發現人的確功不可沒。據陳文忠教授梳理,此詩在唐代通過已佚的“唐人選唐詩”保存到宋代,北宋時這首樂府體詩又僥幸被收錄進《樂府詩集》之中。但從唐代至明代前期,不但沒人承認它是一篇杰作,甚至對它的關注度也很低。明代中期李攀龍《古今詩刪》選入此詩后,它的命運出現了轉折。而第一個對《春江花月夜》作出分析評價的是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制,初唐無疑。”其后,晚明以降的詩評家對這篇杰作的藝術特色做了多方面闡釋。清末王闿運進而指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為大家。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詩,盡其支流,宮體之巨瀾也。”從而空前提高了張若虛在詩壇上的地位。現、當代評論家聞一多、程千帆、李澤厚等人對此詩意義之探索和性質之論斷,其實便是對“孤篇橫絕,竟為大家”這一斷語的充實和豐富。由此看來,胡應麟、王闿運等人顯然是《春江花月夜》最重要的發現人,正是他們的眼光、評點和定位,最終才確認了這首詩的經典位置。而當代人之所以能認識到這首詩的價值,很可能與李澤厚的鑒賞與推廣有關。在《美的歷程》中,李澤厚接過聞一多的話題展開賞析,并進一步指出:“它是一種少年時代的憧憬和悲傷,一種‘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憧憬和悲傷。所以盡管悲傷,仍感輕快,雖有嘆息,總是輕盈。”考慮到李澤厚的美學家身份,同時也考慮到《美的歷程》在1980年代對國人影響巨大,他的這種賞析與贊嘆便具有了某種權威性,他也可以看作此詩不斷被追加的當代發現人之一。
2.選本。文學作品進入某個選本,首先意味著對其文學價值的確認,其次意味著為其更久遠的傳播和接受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選本在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詩經》便是最早的詩歌選本,由孔子選出。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這意味著孔子的刪詩與選詩成就了《詩經》這一選本,而這一選本的出現又為那些古詩的經典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其余像蕭統的《昭明文選》,蘅塘退士編選的《唐詩三百首》,吳乘權、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等選本,都對古詩文的經典化起過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選本是和編選者聯系在一起的,因此,選家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是文學經典的發現者。另一方面,選家既有自己的審美旨趣,也會確立自己的編選原則和標準。像蕭統的“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便是其選文準則。這種準則既是標高,也不可避免地會留下遺珠之憾。但總體而言,選本刪繁就簡,既方便了閱讀和流傳,也讓經典之作在眾多作品中得以凸顯,可謂功莫大焉。如《全唐詩》收錄詩歌48900多首,沈德潛編選的《唐詩別裁》也有1928首,而《唐詩三百首》則收錄310首,自然更加精粹。或者也可以說,經歷了這樣一個編選的過程之后,《唐詩三百首》作為詩歌選本一方面更普及,一方面經典化程度也更高了。
3.評點。這里所謂的評點專指對小說、戲曲的評點,是中國古代文論家所創造的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形式。評點究竟起源于何時學界雖有爭議,但到晚明開始風行則是不爭的事實。一般而言,評點往往由正文前后的總批、文中的眉批或夾批組成。而至金圣嘆,體例則更加完善。主要體現在:增加了“讀法”;回評由回末移至回首;大量增加正文中的夾批。在小說方面,金圣嘆點評《水滸傳》,脂硯齋點評《紅樓夢》,李卓吾點評《西游記》,毛宗崗點評《三國演義》最為有名。
那么,在文學經典的形成中,評點扮演著什么角色呢?首先,評點文字的作者實際上便是文學批評家,他們既有極高的文學鑒賞能力,又能道盡文中之妙。他們對某部作品的詳盡評點本身已呈現出一種姿態——這是一部好作品,是值得認真對待和仔細品讀的。這種姿態如同廣告,既肯定了文本的文學價值,也對普通讀者構成了一種吸引和召喚。
其次,在評點之前,那些文學作品往往已在讀者中享有好的口碑。評點既是對文學之經典位置的進一步固定,同時也是對文學作品的進一步闡釋。評點越詳盡,意味著批評家越有話說,也意味著某部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空間越大,這實際上已昭示出文學經典的價值;另一方面,這種闡釋往往又是批評家的再創造,它們與正文相互補充,相互支撐,構成了文學經典化中的一種特殊景觀:既要讀正文,也要讀評點,甚至讀后者更為重要。錢穆曾回憶說,他年幼入學堂時曾遇顧先生。顧先生知他已讀《水滸》,便考他所讀內容。但考來考去發現他只讀了小說,于是便說:“汝讀此書,只讀正文大字,不曾讀小字,然否?”“不讀小字,等如未讀,汝歸試再讀之。”錢穆聞聽此言,“大羞慚而退。歸而讀《水滸》中小字,乃始知有金圣嘆之批注。”這個例子似可說明評點文字的重要性。
第三,任何文學作品若要能夠流傳,都離不開讀者的閱讀和呵護,這也是經典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評點則能提高讀者的鑒賞水平,弄清楚經典之所以是經典的奧秘,進而觸類旁通,掌握閱讀其他經典著作的路徑和方法。這又反過來增加了讀者擁戴經典之作的信心。錢穆說:“自余細讀圣嘆批,乃知顧先生言不虛,余以前實如未曾讀《水滸》,乃知讀書不易,讀得此書滾瓜爛熟,還如未嘗讀。”因讀金批《水滸》使他“神情興奮”,“每為之踴躍鼓舞”,他甚至悟出了許多道理。如《水滸傳》中寫道:“只見智深提著鐵禪杖,引著那二十三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沖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金圣嘆批曰:“看此一句,便寫得魯達搶入得猛,宛然萬人辟易,林沖亦在半邊也。”錢穆因圣嘆這一批,領悟了《史記·鴻門宴》中一處寫法的妙處:“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錢穆說:“照理應是張良至軍門,急待告樊噲,但樊噲在軍門外更心急,一見張良便搶口先問,正猶如魯智深搶入廟來,自該找林沖先問一明白,但搶入得猛,反而林沖像是辟易在旁,先開口問了智深。把這兩事細細對讀,正是相反相映,各是一番絕妙的筆墨。”于是他進一步指出:“好批注可以啟發人之智慧聰明,幫助人去思索了解。”在我看來,評點固然首先是讓讀者獲益,但無疑也增添了文學作品的經典指數。
二、現代經典的建構因素
事實上,發現人、選本和評點等因素也延伸到現代經典的建構之中,但與古代相比,這些因素又略有差異。比如,現代經典的發現者往往是期刊或出版社的編輯,但他們往往又處于匿名狀態;選本除了體現選家眼光之外,有時也會打上某種意識形態色彩;而評點則衍化為大塊頭的文學評論文章,批評家通過現代文學批評樣式品評、推薦、褒揚某些文學作品,其功能與評點相似。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建構文學經典的種種新元素,如教科書與文學獎的作用,文學機構中和學院制度下的種種舉措,國家意識形態的深度介入等等,所有這些,都讓文學經典的建構變得更加復雜了。以下,我將擇其要者,簡析其中的三種因素。
1.教科書。雖然教科書的編寫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而進入教科書的文學作品不一定都能成為經典之作,但是某篇或某部作品是否入選了教材,是否進入了文學史的講述之中,畢竟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在現代經典的建構中,教科書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反復進入教科書中的作品,既加速了其經典化的進程,也讓它擁有了更多的受眾。
比如,魯迅的《故鄉》自從它在1921年5月號的《新青年》雜志刊出后,反復入選教科書便成為其經典化過程中的重要途徑之一。據日本學者藤井省三的考證與分析,《故鄉》第一次出現在1923年8月刊行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五冊中。此后,它又“作為具有超穩定的教材,經過日中戰爭至民國末期的1948年,自始至終都被各社的中學國文教科書收錄”。1949年之后的毛澤東時代,《故鄉》依然被中學語文教材收錄,但那時主要側重于該小說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以至于許多人在“豆腐西施”的階級性上大做文章。而在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故鄉》在教材中的解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為“豆腐西施”平了反,而且《故鄉》的主題也發生了變化——“又開始被閱讀為知識分子(而非知識階級)以及‘母親’、楊二嫂等小市民的故事”。而無論《故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怎樣被解讀,它在教科書中的位置始終沒有動搖過。不同的解讀方式則意味著此篇小說具有巨大的闡釋空間。這樣,“《故鄉》閱讀史”實際上可被看作文學經典化的一個典型個案。
如果說中學語文教科書對文學作品的選用還只是體現著單篇作品的經典化過程,那么,大學文學史教科書的書寫則更能從整體上確立作家的經典位置。例如,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早已形成了“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序模式,也意味著這六位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中的經典地位。這其中的原因雖然非常復雜,但大學文學史教科書對他們位置的固定顯然起著更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指出,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開山之作”,而這部文學史又是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框架進行編寫的。在這種歷史觀的引領下,“魯郭茅巴老曹”的專章模式和敘述方法盡管在當時還未浮出歷史地表,但事實上已構成了對文學史秩序的整頓,并為后來的文學史編寫樹立了榜樣。其后,直到那部使用率很高影響亦很大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合著,1998年修訂版),“魯郭茅巴老曹”的經典地位并無多大改變。而通過文學史的固定和文學教師的反復講授,他們差不多已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
2.文學獎。古代是不存在文學獎的,但是進入現代社會(尤其是20世紀)以來,文學獎項的設立越來越多,它們也對文學經典化構成了重要影響。國際上重要的文學獎有諾貝爾文學獎、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英國布克獎、美國國家圖書獎、西班牙塞萬提斯獎、德國畢希納文學獎等。而在中國,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馮牧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姚雪垠文學獎、大家·紅河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則構成了較重要的文學獎項。既然有這么多文學獎參與其中,它們對文學經典化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把某個文學獎頒發給某個作家或某部(篇) 作品,無疑是對這個作家創作實力與成就的一次確認,而越是重要的獎項,其確認的力度就越大。以中國作家莫言為例,此前他的一些作品已獲得臺灣“聯合文學獎”、法國“Laure 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意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中國的“大家·紅河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茅盾文學獎”,這固然是對他文學成就的一次次確認,但其力度都無法與他2012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相提并論。正是“諾貝爾文學獎”把他推向了獲獎的最高峰,也是這個獎完成了對他創作實力的最大確認。
其次,文學獎如同商業廣告或名牌商標,它提高了作家作品的知名度,擴大了文學受眾的數量,也加大了作家作品的傳播力度。依然以莫言為例,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前,普通讀者對他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但獲獎之后的短短幾天內,莫言知名度大增,他的小說也在書店里銷售一空,出版社不得不緊急加印他的各種小說,并在封面上打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作品系列”(上海文藝出版社)或“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代表作”(作家出版社)的醒目標記。而種種跡象表明,獲獎后的莫言與獲獎前的莫言已不可同日而語。
由此看來,文學獎項已參與到文學經典化的進程之中,為許多作家作品再鍍了金身。當然,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每種文學獎項都有自己的評判標準,這種標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文學獎也只是文學經典化中的一個環節,它雖然重要,但并非經過這個環節的作家必然都能成為經典作家。因為說到底,檢驗作家作品是否經典的最后尺度依然是時間。
3.學院。學院既是學術研究的重鎮,同時也是精英主義審美趣味較為流行的地方。因此,作家作品能否進入學院師生的視野之中,成為他們研究、講授、學習和相互探討的對象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已經進入文學史敘述的作家作品自不待言,而那些游離于文學史之外的作家作品若要躋身于經典之列,似乎必然要經過學院之手的梳理、分析與再造。這樣,把學院的接納和推崇看作文學經典化的又一環節,便具有了充分理由。
讓我們以金庸為例略作分析。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于1950-1970年代,當它們在1980年代以盜版書的方式在大陸的讀者中流行時,“還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個人愛好,甚至是某種具有可疑意味的校園文化”。而到1990年代,金庸其人其作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2年,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 (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作此書的起因之一便是“翻閱了好些金庸等人的作品,或許是因為心境不同,居然慢慢品出點味道來”。1994年,品味高雅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一套(36冊)裝幀精美的金庸文集,緊接著便有了學院的接納與推動。1994年8月,在王一川先生(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金庸被列為小說大師之一,名列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后,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位居第四,而此前在文學史中排名第三的茅盾則未能入選。《中國青年報》為此專發的消息中曾引王一川的話說:“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雅俗共賞。”同年10月,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從1995年起,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為本科生開設了“金庸小說研究”的課程,后講課內容結集成書,名為《金庸小說研究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99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宋偉杰寫出大陸首篇研究金庸的博士論文,后以《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沖動——金庸小說再解讀》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1999年,金庸被浙江大學聘為文學院院長。
金庸的小說一般被看作通俗文學,而其作品的藝術價值也一直存在爭議。比如王彬彬、王朔等人就寫過重頭文章,破解“雅俗共賞的神話”,對金庸小說進行了全盤否定。北京大學中文系雖是推動金庸小說研究的重鎮,但也并非所有的學者對金庸小說都有好感,如洪子誠教授就讀不進金庸的小說。不過盡管如此,金庸及其小說已進入學院之中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他在經典化的路上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因為雖然他的小說與雅文學或純文學還有距離,但學院的專家學者卻擁有調整和修改文學評判標準和價值尺度的權力。而調整和修改的過程也就是為金庸這樣的作家敞開學院大門的過程。于是,通過學院的命名和認可之后,金庸小說仿佛也就獲得了進入經典行列的通行證。
三、讀者與群選經典
在經典化的過程中,讀者的因素也至為重要。這里之所以把它單獨拿出來加以談論,一方面固然是因其重要,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更為復雜。在當今傳媒化的時代,讀者甚至造就了一種經典化的新路徑,所以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先說讀者。在接受美學與敘述學的分類中,讀者有實際讀者、隱含讀者、真實讀者、虛設讀者、理想讀者等等之類的區分。我們這里所謂的讀者是指與專業讀者(如批評家、大學教師等)相對應的普通讀者。這種讀者具有讀寫能力也具有一定的鑒賞水平,他們構成了文學作品最廣泛的接受人群。
然而,在傳媒不發達的時代里,普通讀者一方面處于無名狀態;另一方面,即便他們閱讀完作品之后有感受、有想法,甚至有發表評論的欲望,卻依然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可供他們發聲的媒介和傳播渠道少之又少。而在大眾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急遽發展的時代,這種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觀。他們可以通過自媒體(如博客、微博、微信等)對作家作品發表看法,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如BBS、QQ群、豆瓣里的讀書小組、百度貼吧等)進行交流與討論。而他們所形成的那種聲勢最終又會對文學經典化的進程構成影響。下面,我主要以路遙《平凡的世界》為例,簡要分析構成這種影響的幾個層面。
首先,讀者喜歡某部文學作品,必然會在閱讀量、借閱量和相關的調查數據中體現出來,它們既造成了一定規模的閱讀聲勢,同時又會反作用于出版發行部門,使某部文學作品變成長銷書。有學者指出:
長銷書與暢銷書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轟動一時,但是在讀者中有著長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不止表現在穩定的、“細水長流”的銷量上,更表現在對讀者認同機制長期、深度的契合上。從時間上看,讀者對長銷書的認同不僅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隨著時世的變遷,長銷書原本的基礎內涵會被賦予新的價值,煥發出新的生機;從認同方式上看,長銷書讀者的認同不是停留在淺層的愉悅、獵奇等層面上,而是在人生觀、社會觀等深層的觀念上。通過一部書籍潛移默化的影響和長期的凝聚,處于零散狀態的個體或小群體的認同感悟逐漸融合,可能匯成一股“內力深厚”的社會性的文化力量。
《平凡的世界》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這部長篇小說既體現在圖書館的借閱量上(如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外借圖書的統計結果顯示,2005年1月1日-2010年5月1日,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外借1314次,排名第二,僅次于白壽彝的《中國通史》),也體現在歷次的調查數據之中。如在面向北京進行的“1978-1998年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中,有“20年內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的分段調查,結果如下:1985-1989年,《平凡的世界》位居第17;1990-1992年,該小說位居第13;1993-1998年,該小說位居第7。而在1998年進行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調查”中,讀者購買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 (占讀者總數的30%),讀者最喜歡的作品也是這部小說。
其次,在傳媒不發達的年代里,讀者會以口耳相傳的方式讓某部文學作品享有好的口碑,而一旦有了發聲的渠道,讀者又會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從而形成一種評論聲勢。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最新出版(2009年1月版)的《平凡的世界》進入當當網上書店后,短時間內就有讀者評論1500多條,至2013年7月,讀者評論已多達32700多條。有讀者說:“我很慶幸自己在青少年時期就幸運地接觸到了這本書,它影響了我整個兒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擇偶觀。”還有讀者說:“在人生最關鍵的時刻,是《平凡的世界》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兩本書在激勵著我,其中尤以《平凡的世界》為重。”另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當筆者的一篇《今天我們怎樣懷念路遙》的短文在路遙去世15周年的日子里被貼至個人博客后,幾天之內被點擊11000多次,跟帖160多個。一名網友說:“路遙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唯一值得一提的作家,……只有在路遙的書里面,你才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對于中國這幾十年巨大變革下的普通人的遭遇,他們的思想道德遭遇的挑戰和崩潰。路遙在中國的地位接近于Charles Dickens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另一位網友則說:“懷念路遙,《平凡的世界》我看了三遍,據一哥們說他一哥們看了七遍,是我知道的最牛的。”
第三,讀者的閱讀規模、口碑和評論聲勢最終會作用于專家學者,讓他們感到震驚,使他們形成思考,進而引導他們走出閱讀盲區,甚至矯正他們的一些看法。例如,《平凡的世界》長期缺席于文學史的講述之中,但正是如上所述的幾個調查數據對北京大學中文系學者邵燕君構成了極大的沖擊,于是這部小說開始進入她的視野并使她展開了相關研究。錢理群、嚴家炎、陳平原等北大教授之所以關注金庸,則主要是受學生影響、推動和督促的結果。

不過,普通讀者介入經典化的勢頭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警覺,于是有了“群選經典”之說。
群選經典是由國內學者趙毅衡教授提出并使用的一個概念。借用符號學者縱聚合軸和橫組合軸的說法,他認為傳統的經典評判和重估是專家學者面對前輩大師遴選出來的經典之作進行比較的結果。因此,“批評性經典重估,實是比較、比較、再比較,是在符號縱聚合軸上的批評性操作”。然而,隨著大眾大規模地參與經典重估活動,經典的推選與評判開始向橫組合軸上轉移,因為“大眾的‘群選經典化’,是用投票、點擊、購買、閱讀觀看等等形式,累積數量作挑選,這種遴選主要靠的是連接:靠媒體介紹,靠口口相傳,靠軼事秘聞,‘積聚人氣’成為今日文化活動的常用話。群選經典化有個特點:往往從人到作品,而不是從作品到人,被經典化的是集合在一個名字下的所有作品”。批評性的經典重估需要論辯,但“群選經典是無須批評的:與金庸小說迷辯論金庸小說的質量,與瓊瑤、三毛小說迷辯論瓊瑤、三毛小說的質量,幾乎不可能。不是說偶像碰不得,而是他們的選擇,本來就不是供批評討論的,而是供追隨的。”
筆者以為,群選經典無疑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概念,因為它非常準確地概括出了當今時代讀者大眾參與文學經典化的盛況;另一方面,它也隱含著如下事實:如今讀者大眾可借助于新媒介,嘯聚網絡,呼風喚雨,生發出巨大能量,甚至讓以往的經典遴選和重估偏離了既定的軌道。尤其是讀者大眾成為商業和媒體的同謀時,群選活動顯然會對正常的經典遴選構成一種干擾。而更讓趙毅衡擔心的還不是“群選經典進入經典集合,而是批評界開始采用群選經典‘全跟或全不跟’原則”“學院開始奉行‘大眾喜歡的必是好的’”“學院經典更新開始橫組合化”。像嚴家炎等學者把金庸經典化,就是經典遴選從縱聚合軸向橫組合軸位移的一個重要信號。從這個意義上看,群選經典甚至搞亂了學院經典化的價值標準,讓專家學者失去了以往的自信。
趙毅衡主要從負面意義上呈現群選經典所存在的問題,固然值得重視,但我們也不妨把這個問題復雜化,考慮一下群選經典的正面價值。長期以來,遴選和重估經典都是專家學者的事情,普通讀者是無法擁有這種特權的。但久而久之,這種特權一方面打造出了一種精英主義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也把學院營造成了一個封閉的空間,阻斷了與民間的交往與聯系。這種狀況最終讓學院派的視野變得狹窄起來了。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生產異常豐盛的時代,專家學者已無窮盡各類文學作品的目力,這時候,普通讀者的群選經典正可以彌補學院人力、精力、目力之不足,為他們提供打開通往其他文學經典的各種通道。一旦這些通道暢通起來,來自民間的文學觀、審美觀、價值觀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入學院之中,并與學院的觀念形成一種碰撞,乃至形成交往互動。互動的結果并非誰戰勝誰、消滅誰的問題,而是要為雙方、尤其是要為學院派提供一種重新打量文學經典的眼光和視角,從而讓他們對自己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尺度做出調整和修正,進而讓他們在關注雅文學之外,也把目光聚焦于優秀的俗文學或介于雅俗之間的文學。比如,從群選經典的角度看,《平凡的世界》的價值可能主要在其勵志色彩,而勵志等等原來并不在學院遴選經典的價值尺度之中,但如果學院接納了這部長篇小說,其實也就接受了這種民間標準,并已悄悄修改了自己衡量經典的標尺。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大可不必把群選經典看作洪水猛獸。既要正視它所存在的問題,同時又去吸收它的有益之點,很可能才是學院派應該采取的應對方案。
雖然以上分析并未窮盡文學經典建構的所有元素,但我們似已可發現某種規律性的東西。在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元素既相對簡單,建構的過程也往往比較漫長,同時,經典建構一般也不是有意為之的。這樣一來,經典的建構固然也有外力推動,但水到渠成的意味則更濃一些。而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一方面經典建構的元素多且復雜,另一方面建構之事也往往成為一個人為的系統工程,從而使建構的速度開始加快。18世紀的英國批評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在思考莎士比亞的文學成就時指出:“他早已活過他的世紀——這是為了衡量文學價值通常所定的時間期限。”這意味著在那個時代,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常常成為衡量作家作品是否經典的時間尺度。但艾布拉姆斯(M.H.Abrams) 卻發現,20世紀的許多作家如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托馬斯·曼和納博科夫,似已取得了經典作家的聲譽和影響力。而像葉芝、T.S.艾略特、伍爾芙等作家,似已穩居民族經典作家的位置。這很可能意味著,現代經典的建構元素在助推其成為經典的途中更有成效。但話說回來,齊心協力的建構是一回事,最終能否成為經典是另一回事。因為除了那些人為的因素外,還有自然因素,而最大的自然因素就是時間。這樣,當今那些已經建構和正在建構成經典之作的文學作品,無論其在短時段內如何被賦予了經典光環,也依然需要接受未來時間的檢驗。
注釋:
①南帆編:《文學理論新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
②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③童慶炳:《童慶炳文集·文學創作問題六章》(第六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頁。
④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頁。
⑤李澤厚:《美的歷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頁。
⑥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六),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36頁。
⑦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圣嘆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頁。
⑧⑨錢穆:《中國文學論叢》,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43-144頁、第144-145頁、第150頁。
⑩[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第44頁、第173頁。
?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頁。
?吳曉黎:《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對金庸小說經典化與流行的考察》,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頁。以下筆者使用的部分資料亦來自于吳曉黎一文的搜集。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金庸成為文學大師》,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37/1/class013700001/hwz227802.htm.
?王彬彬:《文壇三戶——金庸·王朔·余秋雨:當代三大文學論爭辨析》,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頁;王朔:《我看金庸》,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8頁。
?趙勇:《什么時候讀金庸》,《文學自由談》2006年第3期。
???邵燕君:《傾斜的文學場——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6頁、第160-162頁、第160頁。
??趙勇:《為什么喜歡讀路遙》,《書里書外的流年碎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第83頁。
?趙勇:《今天我們怎樣懷念路遙》的網絡跟帖,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62739&PostID=11806739.
?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頁。
?黃書泉:《文學消費與當代文學經典建構——以〈平凡的世界〉為例》,《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1期。有關“恒態經典”和“動態經典”的論述可參見[加]斯蒂文·托托西著,馬瑞琦譯:《文學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頁。
??趙毅衡:《兩種經典更新與符號雙軸位移》,《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
?[英]約翰遜著,李賦寧、潘家洵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見楊周翰編:《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頁。
?[美]艾布拉姆斯著,吳松江等編譯:《文學術語詞典》(第7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