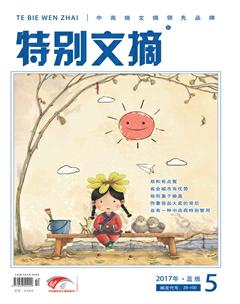特供天氣預(yù)報(bào)
劉誠龍
古時(shí)氣象預(yù)報(bào)是有的,比如屋背后有股風(fēng)吹來一朵云,先人便睜開眼睛,細(xì)細(xì)瞧:這是一朵雨做的云,還是一朵火做的云,或是一朵雪做的云,抑或是一朵為云而云、云做的云?進(jìn)門看臉色,出門看天色。天上魚鱗斑,曬谷不用翻——這是短期預(yù)報(bào);雷打冬,十間牛欄九間空(這個(gè)冬天是冷冬)——此乃中長期預(yù)報(bào)。
古人之天氣預(yù)報(bào)是誰的預(yù)報(bào)?多是農(nóng)民吧。如: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如:麥蓋三場被,枕著饅頭睡。如:日落烏云洞,明朝曬得背皮痛。如:虹高日頭低,明朝著蓑衣……農(nóng)民伯伯是最需要天氣預(yù)報(bào)的,也是最不需要天氣預(yù)報(bào)的。春要下種,秋要收麥,不可沒天氣預(yù)報(bào);夏要下雨,冬要飄雪,要甚天氣預(yù)報(bào)?虹高日頭低,明朝著蓑衣,蓑衣就是一身老皮,嘩啦啦淋上一場雨,淋成落湯雞,犁田不須歸——太陽當(dāng)空照,照脫一層皮,也沒見農(nóng)民伯伯涂防曬霜,打太陽傘。
市民跟農(nóng)民相似,是最不需要天氣預(yù)報(bào)的,也是最需要天氣預(yù)報(bào)的。只是需要與不需要,恰是相反的。曬谷下雨,播種暴晴,跟市民有甚關(guān)系?市民才不在意這個(gè)呢;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了,市民同志便心情緊了——要帶雨傘啊,要定飯館啊。給農(nóng)民提供天氣服務(wù)的,是老天,老天飄來一朵云,老天吹來一陣風(fēng),老天堆砌一層層朝霞與晚霞,便是老天給老農(nóng)做預(yù)報(bào)了。
老天做天氣預(yù)報(bào)員,在鄉(xiāng)村沒問題,在城里可能就不行了。“月著蓑衣,天要下雨”,城里水泥高樓,見得到什么月?“半夜無星,大雨快臨”,市民夜里倒是沒睡,卻在夜總會(huì),但見滿屋燈,不見滿天星;“雞啁風(fēng),鴨啁雨,螞蟻攔路要落雨”,城里沒有雞,沒有鴨,沒有螞蟻,叫人如何曉得要下雨?
宋朝城市化建設(shè)搞得好,直把杭州作汴州,直把汴州作杭州,市民猛增。市民們?nèi)绾我褂^天象?古代也有氣象局,時(shí)謂司天監(jiān),機(jī)構(gòu)貌似還挺完備的,有推算局,有測驗(yàn)局,有漏刻局。這個(gè)測驗(yàn)局,多半是測天氣吧——檔次比農(nóng)民夜觀天象,肯定要高些,還會(huì)捉只青蛙,捉條泥鰍,做天氣預(yù)測啥的。
天氣預(yù)測了,那何以告天下?有人說,古時(shí)天氣是國家機(jī)密,不報(bào)人的——估計(jì)其所講的是“季(劉三,劉邦也)所居上常有云氣”(這天氣,定然定為國家絕密級);然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平常氣候,還是要報(bào)人的吧。如今天氣預(yù)報(bào),報(bào)道平臺(tái)有CCTV,有微信微博,有短信電信;古時(shí)城市天氣預(yù)報(bào),怎么報(bào)呢?
至少宋時(shí),是有預(yù)報(bào)員的,“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或木魚沿街報(bào)曉,各分地方”。宋朝夜市很晚,宋朝早市很早。宋朝城里,沒得雞鳴,但是姑蘇城外寒山寺,有和尚打更;和尚道士各分區(qū)域,負(fù)責(zé)各自社區(qū),梆梆梆,“御街鋪店聞鐘而起,賣早市點(diǎn)心,如煎白腸、羊鵝事件、糕、粥、血臟羹、羊血、粉羹之類”。
庵舍行者頭陀只是更夫么?他們還是天氣預(yù)報(bào)員,“若晴,則曰‘天色晴明”。梆梆梆,今天天氣好啊,好踏青哪,好曬被啊,記得擦爽膚水吶。“陰,則曰‘天色陰晦”。梆梆梆,今天陰天,宜出門,宜動(dòng)土,宜婚嫁,不用打傘,不能曬書,不適合去西湖柳樹下,人約黃昏后(沒得月色)。“雨,則曰‘雨”。梆梆梆,今天小雨,今天中午中雨,今天午后暴雨,雨天里,你愛干嘛干嘛,你能干嘛干嘛。
宋朝天氣預(yù)報(bào),還真不只是冷冰冰的“專業(yè)術(shù)語”,他們把天氣與勞動(dòng)與生活連在一起,什么天氣得干什么,都是在天氣預(yù)報(bào)時(shí)候,跟生產(chǎn)隊(duì)隊(duì)長一樣,一并喊,一并吹口哨,今天天氣晴,便喊:同志們,今天天氣好,公家說了,不放假,都得好好上班。
宋朝的天氣預(yù)報(bào)屬國家機(jī)密?這話可能不太對,宋朝天氣預(yù)報(bào)不太屬于平民,或是真的。有謂,宋朝市民睡在床上,便可知“今天天氣呵呵呵”,這情況有肯定有,不過非所有市民都能享受這般服務(wù),除非是房子買在公務(wù)員小區(qū)。宋朝天氣預(yù)報(bào)員分區(qū)域報(bào)曉,其區(qū)域多半得住了公務(wù)員,或住了洋人。預(yù)報(bào)員報(bào)晴報(bào)雨報(bào)“今天陰轉(zhuǎn)晴”,多報(bào)與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蓋報(bào)令諸百官聽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諸司上番人知之,趕趁往諸處服役耳”。天氣預(yù)報(bào)的服務(wù)對象是哪些人呢?百官,公人,官兵,還有“諸司上番人”,喊他們?nèi)ド习嗟牡胤缴习唷W≡诠珓?wù)員小區(qū)或附近的,可以聽到天氣預(yù)報(bào),隔得遠(yuǎn)的小市民、小商販、小老板、公子哥兒與小姐,多半是享受不到天氣服務(wù)的。
哪個(gè)朝代的天氣,都屬于普供,老天不管官與民、將與兵、朝與野、中與洋,陽光雨露普惠蒼生;而宋朝或謂史上各朝,或有天氣預(yù)報(bào),卻非普供,多是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