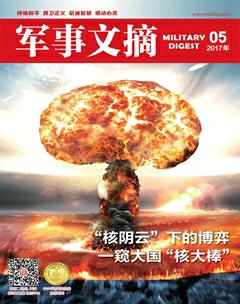大數據:讓指揮決策更科學
李橋銘
如同農業時代的土地、工業時代的能源,數據成為信息時代的核心資源。大數據改變了數據使用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給作戰指揮領域帶來新的機遇。可以預言,大數據或將成為戰斗力生成的核心要素、信息化戰爭的制勝關鍵,誰掌控了“數據主權”,具備戰場大數據優勢,就將更有把握立于不敗之地。
正如望遠鏡能夠感受宇宙,顯微鏡能夠觀測微生物一樣,大數據為探索戰爭制勝機理提供了新的視角。基于大數據的指揮決策,能夠建立起以各軍兵種、戰場環境間數據共享為基礎的自主式決策支持系統,實現“從數據到決策”。大數據時代,云計算、物聯網技術充分應用于軍事領域,扁平結構、層次簡捷、高度集成、體系融合成為作戰指揮體系轉型建設發展的方向。大數據是信息技術的一次革命性變革,將加速戰爭形態向智能化、無人化方向轉變。大數據將以不可阻止之勢對戰爭指揮控制產生影響,為戰爭指揮控制模式轉變提供契機和可能。
推動探尋新的戰爭制勝機理
冷兵器時代,地形、陣法、兵器是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機械化時代,機動、火力、謀略、時空間結合是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信息時代,各種因素交織關聯更趨普遍,單點優勢不再突出,數量和規模不再是主導。信息把戰場、力量、行動糅合成整體,制勝因素更為復雜多變。運用大數據及其內含的處理方法,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五維戰場數據信息,分析各環節、時機、因素之間的關聯關系,構建模型和算法,為探尋戰爭制勝機理找到更為科學有效的路徑。
為探索戰爭規律,人類把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延伸到軍事領域,先后產生了實驗科學、理論科學和計算科學3種研究范式。大數據模式被稱為第四科學研究范式。該范式通過以大數據為核心技術的數據挖掘、知識發現等,準確把握諸如敵方指揮員的思維規律,預測對手的作戰行動、戰場態勢的發展變化等復雜問題,為探索戰爭機理提供新的方法手段。
西方有一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須用數據說話。”利用大數據,可以透過“戰爭迷霧”窺探制勝機理,并基于這些機理制定決策,進而實現對戰爭的精確設計。冷兵器和熱兵器時代,把握戰爭、設計戰爭缺少足夠數據,也不具備相應的計算能力和方法,甚至數據本身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也難以保證。人們更多依靠經驗對作戰進行概略或粗放設計,“藝術”大于“科學”。
隨著大數據不斷融入軍事實踐,精確設計戰爭意識和手段有了長足進步,大數據有望實現戰爭設計“科學”與“藝術”的統一融合、殊途同歸。針對特定的作戰對手和作戰環境,對己方作戰單元進行合理的模塊化編組,從而實現整體作戰能力最優。面對眾多性質不同、防護力不同且威脅度各異的打擊目標,對有限數量、強度和精度的火力進行統籌分配,能夠實現作戰效益的最大化。
引領指揮決策轉變
傳統數據決策模式收集和處理的是與決策直接相關的數據,數據的結構化程度較高,主要采用匯總、聚類、因子分析等統計方法,以及圖表、虛擬現實等可視化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利用的是數據本身所蘊含的信息。大數據情境下,數據以聲音、圖像、視頻等多種方式呈現,數據的結構化程度較低。需要通過數據抽取轉換、數據挖掘、語義分析等多種處理才能獲取到信息,更加注重利用數據間的相關關系,決策問題由傳統結構化決策轉變為非結構化決策。
傳統決策分析主要基于因果關系,更關注“為什么”。大數據下指揮決策分析基于需求,不再一味追求“為什么”,重點是通過關聯性解決“是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戰廣為流傳的“波斯貓的故事”,是依據“波斯貓與高級軍官”“高級軍官與指揮所”之間的關聯關系,概略判定了法軍指揮所位置。這雖與大數據無關,卻揭示出關聯性對數據價值挖掘的極端重要性。“波斯貓的故事”帶有極大偶然性,但隨著大數據的軍事應用,極強的數據處理能力將推動這種偶然成為必然。
傳統指揮決策受計算能力、信息獲取能力限制,往往采用基于樣本分析,準確度不高。大數據通過全數據關聯分析,各種條件都變成了數據,數據量越大、越豐富,關聯度就越高,越容易找出制勝的方法,使指揮決策變得更加高效、準確、自動。2011年美軍擊斃本·拉登就是靠對海量信息的相關性分析實現的。
“知己知彼”一直是作戰指揮的核心要義。傳統作戰指揮對數據本身的真實性、準確性依賴大,力求通過每條信息的精準,提高信息判斷的精準。大數據環境下,允許單條信息的不精準,在甚至有些混亂的數據中,卻使找到精準的信息成為可能,單個數據的錯誤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方法得以修正。在大數據支持下,指揮員能夠發現“戰爭迷霧”中的內在規律,掌握敵方的戰役企圖、作戰規劃和兵力配置,使戰場變得清晰透明。
加速作戰指揮體系變革
在大數據條件下,信息系統間無縫鏈接,云計算提供的巨大計算能力極大縮短了指揮層級,指揮結構由“樹狀”變為“網狀”,改變了指揮體系“樹干、樹枝、樹葉”編成的組織形態,為精簡優化指揮體系提供了必要條件。“網狀”指揮結構中,指揮所的設置更加靈活機動,指揮員可以在指揮網內任意節點實施指揮決策。一個旅的指揮系統被打垮,所屬各分隊仍可借“網”與上級或其他作戰單元聯系,避免出現“樹狀”指揮結構中“打斷一枝、癱瘓一片”的指揮弊端,有效提高指揮效能。
現代戰爭要求諸軍兵種作戰體系深度融合。作戰體系融合的關鍵在于信息的充分共享和高效流轉,使得整個體系在認知與行動兩方面達到協調一致。而依靠傳統信息技術卻很難實現,大數據的發展應用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保證。首先,大數據把類型眾多的數據整合到一起,提供高度共享的數據池,保證獲取信息的一致性。其次,按照大數據要求,建立明確的數據結構和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各系統間的信息交換會更加順暢,各力量、各要素之間的互聯、互通、互操作更加良好,為最終形成自同步、自適應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創造條件。
現代化戰爭,小核心、大外圍,精前臺、強后臺是指揮編組發展趨勢。大數據基于云計算的處理服務,能夠有效提高信息融合和分析處理能力。它將大量的信息、情報處理交由后方大型專業處理中心完成,精簡了前方指揮人員編組,從而將指揮人員從繁重的信息處理中解放出來,實現小行動編組、大體系支撐、高效率決策。
催生新的戰爭形態
大數據時代的無縫鏈接,要求指揮員具備基于體系作戰的系統思維、基于內在聯系的關聯思維、基于數據模型的精確思維。美軍提出“全球一體化作戰”,要求各軍兵種及盟國軍事力量之間快速融合,按照以數據為中心、以搜索分析處理數據為中樞的架構,自上而下地建設“數據網絡”,實現從數據轉化為決策的智能化和瞬時化,實現發現即打擊、發現即摧毀,反映出大數據時代聯合作戰的高級形態。
大數據激活了具有自主能力的無人作戰平臺。受益于大數據技術,作戰平臺從戰場上的信息使用者升級為高度智能化和自主化的系統。指揮控制系統、空中作戰平臺、精確制導彈藥等完成由精確化向智能化過渡,最終機器人可能實現自主使用武器。未來十年,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軍事技術創新和利用可能進入爆發期,智能化戰爭比人們預料的時間會來的更早、更快。
網絡空間作戰主要依靠態勢感知、信號分析、密碼破譯、漏洞挖掘、病毒攻擊等方法技術,大數據的應用為這些方法提供了更好的技術支撐。大數據還可以探索異構網絡的動態兼容、風險管理等,提高網電空間的穩健和抗毀能力。“棱鏡門”事件昭示我們,一場以大數據為核心的網電空間戰爭已經打響。信息成為戰場,數據成為戰斗力的來源。網電空間控制權成為未來戰爭勝負的關鍵,誰能夠控制和利用更多有價值的網電虛擬資源,誰就能掌握作戰主動權,也就能擁有更大的勝算。
摘編自 2017年2月28日
《解放軍報》
責任編輯: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