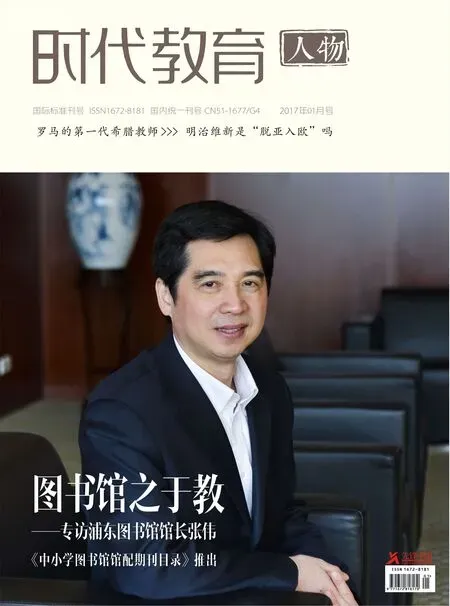余琳:用游戲與童年對話
本刊記者_周春倫
余琳:用游戲與童年對話
本刊記者_周春倫

就在我們走進成都第十六幼兒園的前一天,這里發生了一個小故事。有關十六幼,我們就從它開始講起。
這天的戶外活動時間,小四班的孩子們一起玩皮球。游戲剛剛開始,球便“嗖”一下跑到了屋檐上。現場小朋友們瞬時都興奮得不得了。
“怎么辦呢?”老師問。孩子們停頓片刻后,開始對著球大喊:“快下來,快下來……”
當然,球紋絲不動。有孩子拋起手里的另一個球,試圖將它打下來,然而沒有成功。
“必須有個長東西把球弄下來。”有孩子提議。他找來了童話劇里的“大刀”。老師組織幾雙迫不及待的小手輪流試罷,球還是穩穩當當地停在屋檐上。
“為什么球還是不下來?”老師追問。
“我們可以用竹竿。”又有孩子提議。
順著孩子欣喜的眼神,老師發現了立在圍墻一角準備用來搭藤架的竹竿。竹節凸起,深綠色澤宣告著它的重量。
老師沒有猶疑,和孩子們一起高高舉起其中一根,伸到屋檐處,可還是沒有夠到小球。
“太短了,換一根長的吧!”有孩子建議。
經過好幾番折騰,球終于骨碌碌滾下來。
原本一場玩球的游戲,在這位老師的支持下,演變為“怎樣將球從屋檐上弄下來”。而這個突發的小插曲亦被稱作“游戲”,以“學習故事”的形式出現在十六幼的公眾號里。
看罷,筆者心中生起一連串疑問:
球飛到屋頂這件事,為什么讓孩子們感到如此興奮?
對于幼兒來說,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游戲?
除了使人快樂,游戲還承擔怎樣的功能?
幼兒教師應有的游戲素養指的是什么?
在幼兒階段,如何聚焦核心素養的培養?……
帶著這份求解答的心情,我們走進十六幼,以及這所園子的“掌舵者”余琳。
“當球跑到屋檐上了,孩子們的第一反應是:球,你快下來,快下來——在他們眼里,球也擁有生命了。這就是孩子的世界。"

孩子們的“大玩具”
因為游戲教育,十六幼在成都幼教界的影響頗大。
2016年是余琳任園長的第10個年頭。在各類媒體刊登的照片里,她始終是笑著的,或直面鏡頭,或望向游戲里的孩子。一線幼師的教育經歷,讓她身上散發著和園內其他老師同樣的親和。多出來的,是爽利和干脆。
十六幼有兩個為人熟知的代名詞:童年的院子、一個大玩具。余琳曾在一篇《尋找適宜兒童成長的方式》里,表達自己的教育理想:“辦一所玩味十足的幼兒園,在這里孩子們可以從室內玩到室外,從前院玩到后院,從地面玩到屋頂。童年的院子里有山有水、有動物、有植物,每一個生命的成長都能得到尊重和支持,每一個生命的潛能都能得到釋放和激發。”
十六幼的面積不大,園子的主體部分是一條長廊相連的兩棟教學樓,走廊兩側以及教學樓前后的空地,都被精心規劃并開發為各類游戲區。到目前為止,它確實是一個可以從室內玩到室外、從前院玩到后院、從地面玩到屋頂的大院子。
空間利用的最大化在這里體現得很充分。由大門往里走,走廊左側是自然材料游戲區,分布著小花園、沙坑、水渠,孩子們在這里玩沙玩水畫石頭;走廊右側是開放游戲活動區和建構游戲活動區。在開放區,孩子們被鼓勵自選材料、自設游戲、自主運動;建構游戲區里運用經過專門設計的大型積木,讓幼兒感受不同場地、大小和材料的積木的差別,在建構中建立有關空間的各種概念;教學樓旁是木工游戲區,真的錘子、釘子、鋸子一應俱全,來這里的孩子都一副正兒八經的木工師傅模樣,未完工的作品擺放在靠墻處;再往后,是藝術游戲區和最受孩子歡迎的“小人國”;原本利用率較低的頂層平臺也被改建為手工活動室、創意活動室和圖書閱覽室。
“小人國”得專門說一說。這個如霍比特人小屋式的建筑,是幼兒園基于兒童視角特意打造的。乍一看,它仿佛剛從童話世界里活生生走出來——圓形的小門小窗小煙囪,呈暖人的原木色,屋頂鋪著綠草皮,門前盛開著彩色花朵,屋內是各類家具和餐具,尺寸都比正常使用的小上一號。童話元素以及半隱蔽的特點,使它備受喜愛。不同年齡的孩子們常在這里過家家,玩角色扮演。只要愿意,他們甚至可以爬上屋頂。
十六幼的教室很大,通過少隔墻、巧布局,每個班級都有超過100平米的專用游戲活動室,分布著各類游戲區角。由于10月份是全園國慶主題活動,每個班被布置為各類展館:發明制造館、中醫養生館、熊貓館、小吃館、民俗文化館等等。主題對應之下是各班的游戲課程,以發明制造館為例,孩子們通過浸泡、攪拌、過濾、烤制等一系列手段,制作再生紙,用再生紙作畫,到造紙廠實地參觀。實際上,對于紙的研究,這個班的孩子已經從中班持續到大班,研究的內容也在一層層深入。
室內游戲與室外游戲,常規游戲和節日主題活動,以教師為主導的預設游戲和以孩子為主導的自發游戲,幾條線不斷交織,最終織就了十六幼里的這張游戲大網。

在“最炫民族服”活動中,連接兩棟教學樓的長廊也被裝飾起來,孩子們將其作為T臺走秀
將童年還給童年
為什么是游戲?這個問題在現在來提似乎有些多余了。
隨著教育部《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的發布,幼教工作者們對學前教育的認識日益走向科學,對兒童發展的期待更加合理。尤其在對待游戲的態度上,“游戲是兒童的天性”“游戲是兒童最基本的活動方式”等理念,被更多人接受和重視。
2006年,余琳在接手十六幼后,之所以選擇將游戲作為辦園特色,借用她所說,是基于自己前兩個9年教育經歷的豐富與滋養——做一線幼師的9年和做教研員的9年,讓她在“尋找最適宜幼兒成長方式”的路上,更深刻地看到游戲對童年的價值。
第一個9年。在余琳工作2年后的1989年,《幼兒園工作規程》(試行)頒布,學前教育開始規范辦園、科學保教的改革,并提出在認識兒童的基礎上尊重兒童。恰恰是在這個階段,余琳所在的班級發生了一件“大事”:孩子們偷偷在廁所里養“蛇”。
事情的緣起是幼兒園的一片草坪里被懷疑有蛇。緊張的老師們組織人員手握竹竿展開了連續兩天的地毯式驅逐。整個過程被孩子們目睹了,于是,他們偷偷在廁所角落置辦起一個蛇窩,養了十多條大小顏色各異的“蛇”,待到放學后再把蛇放到草坪,模仿老師進行搜索,比賽誰找的“蛇”多。
這原本是一件成人眼中可怕的事,到孩子們這里卻成了快樂的游戲。他們善良而富于幻想,他們與大自然保持著最親密的關系,對世界萬物充滿友善。這給余琳帶來很大震動。她反思,自己真的認識兒童、理解兒童嗎?
從那以后,她開始有意識地將自己變身為兒童,不僅與他們一同養蛇,還養青蟲、蠶,看青蟲變蝴蝶,看蠶生命的多樣變化與生生不息。她試圖用童心去讀孩子們的童年。這是第一個9年,孩子的一個游戲將她喚醒了。因此才有后面拆除所有桌椅、讓偌大的活動室變游戲室的舉動,也是在這個9年里。
由此,回到文章開頭處我們所講的那個小故事。當球跑到屋檐上,孩子們的第一反應是:球,你快下來,快下來——在他們眼里,球也擁有生命了。這就是孩子的世界,余琳說,很多大人不懂。
而當球飛到屋頂時,孩子們為什么感到興奮?因為他們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沒有困難的環境里,所有問題都被家長包辦解決了。
不僅如此,相較于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前出生的孩童,現代孩子的成長環境也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鄉村城市化,房屋集中建造,鋼筋混凝土建筑、柏油路替代了山莊、農田和小石板路,樹木、河流等都被圍欄圍住,與學校隔離開——天然的游戲場所已經消失殆盡。
過去有趣的、“散漫”的童年只存在于他人的描述中:“我們所有人一直都把時間用在摘野花兒、逮蝌蚪、尋茨菰、打濕雙腳、玩沙子、玩水的事情上。玩沙子就是讓沙子從指間落下,玩泥巴就是拍打它、戳穿它、舉起來、扔下去……我的童年時生活中全是成人漠不關心的事。”
十六幼年輕的楊老師提起自己記憶深刻的一件事。小時候有一天,她獨自爬上小山坡,在那里發現了一朵美麗的紫色花朵,含苞待放。她非常開心,急切地想要跟伙伴分享,于是采下花朵一路狂奔下山,待到山腳,再一看,花竟然開了!年幼的她頓時感到十分神奇。正是這份開心與奇妙的感受,讓她將這份記憶保留至今。

基于兒童視角打造的小人國

神奇的泡泡
我們的教育應該賦予孩子發展的力量,應支持兒童發展那些能夠讓他們有自信地去面對未來生活中各種挑戰的核心素養。
楊老師基于這份體驗來理解十六幼所提出“生命綻放的童年院子”。她說,“生命綻放”大抵就是:孩子們能夠遵從內心,去充分地體驗和嘗試,即使遇到困難,但心是自由的,狀態是愉悅的。
第二個9年,教研員余琳開始帶動家長一起樹立起這樣的觀念:教育,不能以任何神圣的理由剝奪孩子的童年。教育,應該把童年還給童年,讓童年富有詩意、讓童年充滿情趣、讓童年接受大自然的撫摸。
不只是玩玩
2006年,十六幼由企業園轉型為教辦園,余琳接任園長后,一方面規劃改良空間環境,投放大量游戲材料,滿足各類兒童對游戲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逐步建構屬于自己的園本游戲課程。
趙老師是和余園長同一年到的十六幼。她說,剛開始,老師們對游戲的理解也只是怎樣讓孩子們玩起來。年輕的老師們很快遭遇了尷尬:有一天,在組織孩子們玩完一場游戲之后,她突然聽見一個歡呼聲:啊,我玩完老師的游戲了,接下來該玩我們自己的了。聲音細小,于趙老師而言卻振聾發聵。什么是“老師的游戲”?什么又是孩子“自己的游戲”?在他們幼小的心里,這兩者的差別在哪里?
為此,余琳園長特意組織老師們利用孩子的游戲材料,玩孩子的游戲,找“做孩子”的感覺。回想當年,她自己也是通過這樣一個“推己及幼”的過程,去認識和理解兒童。她說,正確解讀兒童,及時抓住兒童在游戲中的需求,推動游戲層級遞進,是一個老師必備的游戲素養。
以最初我們所講述的“球跑到屋檐上”的故事為例,如果現場老師沒有讀懂孩子眼里的興奮和期盼,只將眼光停留在“玩球”這件事上,或者粗暴地將球直接拿下來,就不會有后面這一連串動作的發生。
另一個例子。新學期,大一班的孩子們都在建構區專注于搭建立交橋,但搭出的立交橋總是不令他們滿意,孩子們試圖找出原因。老師聆聽他們的討論后發現,孩子們并未察覺,單一的奶粉桶作橋墩的立交橋,忽高忽低,而沒有層次落差。
老師便拿出一輛小車放在立交橋上,孩子們發現,小車并不能順利下滑。終于,一個孩子說:“我們的立交橋高矮有點亂。”老師沖他會心一笑。小男孩開始一邊比著奶粉桶的高矮一邊對立交橋進行改造,這次小車順利通過了。
雖然成功了,但老師發現孩子們修的立交橋結構過于簡單,沒有層次,于是在建筑區張貼了立交橋結構圖。受到圖片啟發,孩子們嘗試搭建雙層立交橋,但嘗試了幾次都未成功,原來是作為橋墩的材料太過單一,限制了孩子們的想法。老師又通過活動課程與孩子們一道制作了高矮錯落有致的立柱并投放到修建區。在圖片引導下,經過近一月的嘗試和調整,一個美觀而縱橫交錯的立交橋終于搭成了。
在這兩個游戲中,老師的“教”都猶如一個支架,不留痕跡地推動游戲走向更深更遠。但是,當我們的老師在觀察游戲中的兒童時,所聚焦的究竟是什么呢?
余琳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今天的幼兒園教師必須知道:我們的教育應該賦予孩子發展的力量,應支持兒童發展那些能夠讓他們有自信地去面對未來生活中各種挑戰的核心素養。”
在她看來,這些核心素養涉及三個領域:道德、能力、情意。而幼兒園階段,是這三大領域核心素養發展的“種子期”,種子分別是:友善、思考和獨立——倘若在孩子幼年時,便種下這三顆種子,給予時間和養料,它們將凝聚為強大的生命內核,“為人未來的素養:自信與誠信、進取與盡責、堅持與擔當、反思與發現等的全面形成,提供持續的生發動力。”
作為孩子最好的學習方式的游戲,自然而然承擔起這一使命。因此,游戲并不僅僅是讓孩子玩玩而已。游戲之于教師是教育,之于幼兒是發展。以“素養表達”推動評價改革
近年來,新西蘭“學習故事”被國內越來越多的幼教工作者采納。“故事研習”也是十六幼開展教研的一種重要方式。
余琳園長鼓勵老師們將游戲中的所見所聞所思都用敘事性案例的方式記錄下來,特別是不能準確解讀孩子游戲現場需要的故事,統統搬上教研舞臺。
同樣,我們以十六幼一位老師的“學習故事”為例。徐露老師的學習故事《水溝取筆獻妙招》,記錄了發生在孩子大雙身上的一個故事:一次繪畫活動之后,班里的孩子發現大操場上的下水道里有支水彩筆,于是,你一言我一語地出招,想要將這支筆給撈出來。大雙的辦法是用繩子綁住鐵絲圈,作為撈筆工具到水中撈。經過多番嘗試,終于,他意識到這個工具的不足,并對其進行改造,在費盡周折之后,筆被成功打撈出水。
TIPS:
學習故事
新西蘭早期教育課程框架《Te Whariki》(Ministry of Education,1996)編著者之一瑪麗特·卡爾帶領研究團隊經過數年時間開發和形成的一套形成性兒童學習評價體系。在深刻反思了“民間"或傳統的評價模式后,主張用敘事的方式來捕捉兒童學習過程中能夠體現他們能力和自信的那些時刻,關注兒童能做的、優勢和興趣。
近兩年,很多中國幼兒園也開始借鑒學習故事的理念和實踐來貫徹《指南》精神,促進中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木工游戲區,真的錘子、釘子、鋸子一應俱全
TIPS:
水溝取筆獻妙招
教師 徐露
2014年12月26日
繪畫活動過后,“小不點"驚訝地發現:大操場上的下水道里有支水彩筆。
班里其他小朋友紛紛跑來圍觀,你也跑了過來,跟大家一起討論著“是誰把它扔進去的?"
“我們得把它撈出來。"
于是,我問你們:“怎么把它撈起來呢?你們有沒有什么好辦法?"
小朋友們圍在一起出主意,有的說:“撿些小木棍放進去,這樣水就會升高,筆就會跟著水浮起來。"
有的說:“用網子網起來。"
有的說:“用吸鐵石吸。"
還有的說:“用夾子把它夾起來。"
你說:“用繩子兩頭套上鉤鉤,把筆勾起來。"
聽著你們討論,我在心里默默為你們的善思鼓掌。
我問你們:“怎樣才能知道自己的辦法是不是能夠成功呢?"
你們說:“那就試試唄。"
于是,我請你們周末跟爸爸媽媽一起制作自己認為可行的撈筆的工具,然后周一來驗證。
2014年12月29日
大雙,周一你的工具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好了。
你告訴我說:“我的圈圈是用鐵絲做的,一定能撈得起筆。"說完你便開始了實驗。
你提著繩子朝筆的方向慢慢靠近。繩子在空中不停晃動無法靠近水中的筆。你繼續嘗試。可當你的工具好不容易靠近筆時,筆又跟著水面的波動游走了。你調整了姿勢,跟隨著筆繼續嘗試。當你再次提著線把鐵絲圈放到水里時,鐵絲圈漂浮在水面上,線也因為細、軟無法對抗水的阻力,你始終無法用鐵絲套住筆桿。
你嘗試幾次都沒有成功,并受到了其他圍觀小朋友的質疑,你似乎有些猶豫。我問你:“大雙,你覺得你的辦法能不能取出筆?"你肯定地對我說:“能!"
你在水溝邊繼續試驗,一直到吃午飯時間才戀戀不舍地回到活動室吃飯。
今天你吃得比平時都快,吃完飯的你站在擺放工具的桌子邊摸了摸你的工具。
我知道,你堅定地相信你的辦法是可行的,你不想輕言放棄,于是我來到你身邊,問你:“你覺得你的辦法能成功嗎?"你依舊堅定地告訴我:“能!"
說著,你就一個人帶著你的工具再次來到水溝邊。
你認真地提著繩子不停地擺弄。教室離水溝很近,我在教室門邊看著你“孤單"地在水溝邊實驗,你足足嘗試了20分鐘之久。
偌大的操場上,你顯得如此瘦小。可是此時,我卻感覺你無比強大。
你的堅持吸引了廚房的叔叔阿姨的關心。他們駐足觀看你的實驗,為你加油打氣。
該睡覺了,你提著你的工具回到班上。
小朋友們都非常關心:“大雙,你取出筆來了嗎?"
你說:“沒有,繩子不停地晃,我想把它放到筆旁邊,可是它一直不停動。不好控制。"
你發現了其中的秘密。
2015年1月4日
元旦過后,你帶來了你的新工具,細軟的繩子變成了兩根硬硬的寬塑料桿,塑料桿的兩頭仍然套有鐵絲圈。
你再次來到水溝邊進行嘗試,你將一頭鐵絲圈套進了筆桿的一頭,再把另一根鐵絲圈套進筆桿的另一頭。接著,你緩緩抬起手,筆跟著你的工具來到了水溝口。
你趕緊伸手拿出了。你成功了!
老師有話說
什么樣的學習可能發生了?
大雙,老師為你有自己的想法,并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的信念所感動,即使自己的方法遭到同伴的質疑,你依然堅定地相信自己。
當你第一次嘗試撈筆時,你所表現出的耐心和堅持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你知道嗎,你足足嘗試了40分鐘之久。更可貴的是當你第一次嘗試沒有成功時,你并沒有放棄,而是智慧地用硬的塑料桿代替了繩子最終取得了成功。
你已經是一個能獨立解決問題的學習者了!


大雙的試驗引來了廚房叔叔阿姨的關注
故事中,大雙是學習的主角,老師用敘事的形式,描述了由三個不同的學習事件組成的一個持續的學習過程。
“素養表達”貫穿始終:在整個過程中,老師發現和記錄的是孩子能做的,重點關注的是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的想法、意圖、方法和策略,以及孩子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核心素養。并在了解孩子想法和意圖的基礎上用給予他時間、空間、信任、理解和權利來回應孩子的學習需求,讓大雙能主導自己的學習,實現自己心中的想法。顯然,大雙身上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不會或不能,但都不是老師評價的焦點。
此外,我們似乎無法從故事中看到家長的身影,但家長卻一直存在:大雙兩次制作工具都是在家里完成的,父母自然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敘事性案例評價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分享與回顧——老師會將故事與全班孩子、家長進行分享。這個分享對故事中的孩子來說,是在回顧中不斷建構自己作為學習者形象的過程,對家長來說,是進一步了解兒童的學習及學習背后的核心素養的過程。因此,學習故事、敘事性案例評價在改變我們的兒童觀、學習觀的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評價方式。
從2006年到2016年,十六幼的游戲教育日益深入和成熟。而對于園長余琳來說,教育生涯的第3個9年又過去了。
用童心讀懂童年,把童年還給童年,用游戲綻放童年的生命,這是她在尋找最適宜幼兒成長方式的過程中走過的三個階段。她說,“最適宜”始終只是相對的,教育之路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