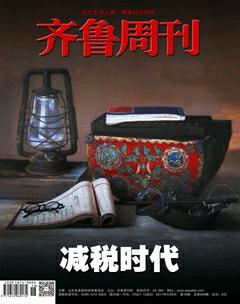婚姻現形記
宗禾
《人民的名義》近日迎來大結局,破8的收視率基本鎖定今年的劇王。從開播到結束,該劇空前的尺度引起一輪又一輪熱議,官場現形記之后,其實還有婚姻現形記。劇中老中青三代夫婦,各有各的唏噓,各有各的畫皮。年輕人床頭床尾地打官腔,中老年則一邊利益捆綁一邊人心隔肚皮,簡直魔幻。
米蘭·昆德拉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愛,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總希望從別人那里得到什么,而不是無條件地投入其懷中并且只要這個人的存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如果在考慮婚姻問題時,依舊像只在叢林中生活的猴子,只追著香蕉跑,將愛看成奢侈,不是太可憐了嗎?
鳳凰男祁同偉VS高干老師梁璐:各懷鬼胎的婚姻里,兩人的自私生出更多惡果
《人民的名義》這部劇中,最恐怖當然是祁同偉和梁璐這一對,一個為獲得權力向高干女老師求婚;一個為了報復前男友,向他證明自己的魅力,轉而追求比自己小10歲的學生。各懷鬼胎的婚姻里,兩人的自私生出更多惡果。除了出席宴請這樣的公眾場合,基本每一刻都在爭執:你看看你對我都做了什么?
祁同偉是真正的鳳凰男:苦孩子出身,上大學后的第一雙球鞋,是他的第一個戀人陳陽所買的。他從底層爬上來,以最艱苦卓絕的方式。在這個途中,他曾經被遺棄在鄉村的司法所中,曾經在前線挨過毒梟的三顆子彈,曾經試圖與愛人團聚而被上級打下馬來。他努力、上進、永不停歇。他簡直就是愛拼才會贏的政治版。
祁同偉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始終愛護和珍惜高小琴,即便當他所有的一切行將暴露的時候,他選擇自己“戰斗到底”,卻費盡心機一定要送高小琴出去。他到最后也沒有出賣高育良,而高在祁同偉暴露之前和之后都已經和他切割了。而祁同偉落入這個局中的開始,是因為要幫高育良料理趙瑞龍的事情:但高老師卻始終是高老師。
最能夠準確定位祁同偉的,是他始終喜歡的那篇小說《勝天半子》。如何才能勝天半子?小說給的,以及祁同偉自己給的,都很清晰:以己為棋。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只有把自己賭上去,才能與整個社會的機制抗衡。祁同偉后來跟朋友說,他的自尊心死于那天正午,漢東大學的操場上。
正如劉震云的小說《一地雞毛》,后來被改編成電視劇。男主角小林選了陳道明,他將小林從清高狂放充滿理想,到最終被生活的大網束縛著放下清高,對命運投降,被世俗成功改造的性格變化演繹得深刻入骨。小林最終感慨,“老家如同一個大尾巴,時不時要掀開讓人看看羞處,讓人不忘記你仍是一個農村人。”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鳳凰男本身不是罪過,他們往往都是些聰明肯吃苦的人,肩負著家族的期望,通過自己的奮斗,最終改變了個人的命運。而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之后,接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改造整個家族的命運。沒有辦法,他們很多都是集全家之力供養出來的,自小就被耳提面命的要知恩圖報,在血液之中早就埋下了“茍富貴勿相忘”的基因。
就婚姻本身而言,由古至今,它從來就不是公平的制度,也不是全面保護愛情的制度。而其中最致命和最大的矛盾不過是平等自由獨立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里從屬理論的矛盾。傳統文化中,父子、夫妻等秩序倫理下通常類似互相綁票。親密關系缺乏界限感,生命個體不獨立,父輩認為自己的人生,子女的情感和生命歸屬自己所有;“鳳凰男”由族落社群結成共同生存關系的鄉村走來,這種綁票的情感倫理關系又延伸到夫妻相處中。至此,關系成為一種痛苦的糾纏。
李達康VS歐陽菁、高育良VS吳惠芬:很多中國人的婚姻,是閹割了情感的麻木
劇中李達康與歐陽菁這對則是好好的婚姻基礎,偏偏被事業插足。李達康為實現政治抱負,漸漸對家庭冷淡,于是妻子賭氣,也寄情工作。除了高速上被檢察院攔車,夫妻倆臨別時錯過的那一握手,情感是在兩人關系中絕跡的。
穿上囚服后的歐陽菁,一臉落寞地怨恨當年選錯人。劇情為了加深她的孤獨感,制造了一個檢察院給她送生日蛋糕就把她防線攻陷的劇情。
許多人評論這個情節太假了,那是因為他們見到的寂寞中年人太少了。社會新聞里翻翻,類似聳人聽聞的事不算少:一個廣場舞大爺將艾滋病毒傳染給五十多個大媽;一個英俊中年騙得好幾位女性傾家蕩產。得不到情感呼應的婚姻,久而久之會把人脆弱化到經不起一點小火星的撩撥。缺愛的時候,人真的會刀鋒舔血、飲鴆止渴。
高育良與吳惠芬則是權力婚姻里的典型,兩人可以深夜坐談天下大事,懇切地推心置腹,但其實早就因為高育良的出軌離婚。兩人協議,離婚后大陸的一切歸吳惠芬,高育良去香港與小嬌妻團聚。于是,吳惠芬勸梁璐:顧全大局。
在他們眼中,什么是大局呢?利益是,其余都不是。但即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利益,轉過身,吳惠芬還是藏不住一臉的落寞,仿佛下了舞臺的演員,妝容一下、戲服一脫,整個人就散了架。
都說婚姻恐怖,但西方人的恐怖和國內人的恐怖截然不同。《苦月亮》《革命之路》里,歐美人是拷問靈魂、追求欲望滿足的折騰,但中國人的婚姻,是閹割了情感的麻木。
你瞧都是18世紀的小說,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與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描寫的婚姻形態多么不同。
簡奧斯丁的小說里那些鄉紳階層的婚姻,固然也講究門當戶對,但終究需要雙方有情感基礎。《傲慢與偏見》中的達西和伊麗莎白,雖然出身差異巨大,但最終還能夠為了情感突破階層。那些以各種理由反對他們婚姻的人,即便拿出再多理由,也不能堂皇說出“感情不算什么”這句話。
但《紅樓夢》中的賈政與王夫人,完成家族聯姻,生下嫡子嫡女后,一個念佛吃齋;一個端起讀書人架子,寧愿與潑婦似的趙姨娘談天困覺。王夫人少女時,被劉姥姥形容為“聰明爽快”,但婚后卻變成了賈母口中的木頭人,可見這樁婚姻的幸福指數。
在中國宗法社會里,婚姻與當事人無關,與家族利益有關。小到傳宗接代,大到利益交換、政治聯盟。兩個當事人,都只是群體利益中的一個棋子。
古代皇帝遇到軍事危機,外邦來犯又無力迎敵時,最恨的就是怎么沒個成年女兒可以出嫁?拉攏權貴門閥,賞銀升官還不夠親,得安排子侄通婚,才算互換人質。
在這樣的婚姻里,雙方都在犧牲,犧牲掉人渴望情感的天性,犧牲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男人拼命追求事業上的成功,以性代替愛,以填補內心的空虛。女人呢,只好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王夫人那么恨晴雯、恨芳官,那恨意里何嘗沒有被她們身上自己當年影子引發的觸痛?
鐘小艾PK高小琴:如果沒有能力愛,如何能夠抵達對方的靈魂深處?
美國心理學家斯滕伯格提出愛的三要素:激情、親密、承諾。但在《人民的名義》中,很多主角的婚姻和情感關系里,這三要素都是殘缺的。
歐陽菁入獄后,李達康與王大路聊天,將婚姻的問題歸結于歐陽菁拒絕成長,因為需索愛屬于少女不懂事時的行為。而侯亮平,在監視器后面,也輕視地說:“這女人哄哄就好。”
瞧,為什么侯亮平鐘小艾夫婦總不說人話,床頭床尾都沒有情意?這就是原因吶。高育良與吳惠芬,當年也一定有恩愛美滿的時刻,可各自情感中的缺憾轉移到工作里時,也一定拿“愛情最終會變成親情”來哄騙自己。所以,誰能保證侯亮平夫婦不會是下一對高育良夫妻呢?
如今有許多情感專家,在教人怎么表達情感,怎么使用技巧。但很少人談到真正的痼疾:壓根不正視情感需求。學了一肚子技巧,學會如何“哄哄對方”有什么用呢?如果哄對方的目的,只是為了達到相敬如賓,不是為了滿足自己與對方心中對于親密的要求,那種假性關系,還不如一通熱吵、一拍兩散。
如此說來,《人民的名義》中祁同偉和高小琴這對在黑暗世界里擁抱取暖的地下情人反而在各色“假模假樣”的官場模范夫妻中顯得熠熠生輝,雖然二人狼狽為奸,絕不是政治正確的感情。
劇里有一段,祁同偉滿懷歉疚地自責道:抱歉,我不能給你一個安定的生活。而高小琴有些無奈又有些滿足地說了一句,我愿意。
他們看著彼此的眼神里,帶著光,而這才是愛情該有的模樣。他們愛的不是在外人看來彼此光鮮亮麗的皮囊和假象,而是知道了彼此足夠骯臟或卑劣的過去,依然愛上了對方的企圖、勢力、軟弱、不堪。
當兩個殘缺的人互相依偎時,愛情也因為破碎而變得靠近人性——我愛上的不是你的純潔無瑕,而是你美好面貌后的渾濁不堪,是他們都只看到你老謀深算、權傾一方,只看到你年輕貌美,坐擁金銀,而我卻看到了你軟弱又卑微的靈魂,陰狠又毒辣的內心。可看透了一切,我依然愛你。
正如祁同偉對高小琴所說,你是唯一能夠抵達我靈魂深處的女人。祁高戀,也許在別人看來很骯臟,也注定是悲劇,但他們至少誠懇又真真切切照亮過彼此。
米蘭·昆德拉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愛,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總希望從別人那得到什么,而不是無條件地投入其懷中并且只要他這個人的存在。
社會發展到現在,城市中人其實已經不會再有生存的憂患(生活欲望的滿足不在其中),如果在考慮婚姻問題時,依舊像只在叢林中生活的猴子,只追著香蕉跑,將愛看成奢侈,不是太可憐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