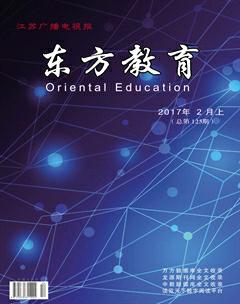模仿與超越
劉靖靖+梁翰晴
(浙江師范大學(xué))
摘要:《最后的常春藤葉》是短篇小說(shuō)巨匠歐·亨利的代表作之一,入選我國(guó)高中語(yǔ)文教材以來(lái),對(duì)其進(jìn)行的文本解讀長(zhǎng)期囿于結(jié)尾技巧與人物精神層面的剖析,如“精神超越死亡”、“信念決定生命”、“為了他人而自我犧牲”等。老畫(huà)家貝爾曼行動(dòng)背后模仿與超越的辯證思索、外貌特征映射下的形象分析卻往往為人所忽略。本文試圖以符號(hào)隱喻、藝術(shù)哲學(xué)理論為依托,從貝爾曼的外貌、行動(dòng)切入,對(duì)文本進(jìn)行再解讀。
關(guān)鍵詞:模仿;超越;再解讀
一、貝爾曼形象分析
在小說(shuō)中,有一段專門(mén)刻畫(huà)貝爾曼外貌的文字,現(xiàn)摘錄于下:
老貝爾曼是住在樓下底層的一個(gè)畫(huà)家,年紀(jì)六十開(kāi)外,有一把像米開(kāi)朗琪羅的摩西雕像的胡子,從薩蒂爾似的腦袋上順著小鬼般的身體卷垂下來(lái)。貝爾曼在藝術(shù)界是個(gè)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畫(huà)筆,仍同藝術(shù)女神隔有相當(dāng)距離,連她的長(zhǎng)袍的邊緣都沒(méi)有摸到……他喝杜松子酒總是過(guò)量,老是嘮嘮叨叨地談著他未來(lái)的杰作。此外,他還是個(gè)暴躁的小老頭兒,極端瞧不起別人的溫情,卻認(rèn)為自己是保護(hù)樓上兩個(gè)青年藝術(shù)家的看家惡狗。
貝爾曼為什么認(rèn)為自己是別人的“看家惡狗”?其實(shí),本段的“眼”就在于開(kāi)頭的幾個(gè)比喻句,這幾個(gè)比喻句用了典故,這些典故是解開(kāi)疑惑的關(guān)鍵所在。
(一)、摩西雕像的胡子
摩西是古代的著名先知。在《出埃及記》中記載,摩西受耶和華之命,率領(lǐng)被奴役的希伯來(lái)人逃離古埃及,前往一塊富饒之地——迦南地。在摩西的帶領(lǐng)下,希伯來(lái)人擺脫了被奴役的悲慘生活,學(xué)會(huì)遵守“十誡”,并成為歷史上首個(gè)尊奉單一神宗教的民族。
據(jù)說(shuō)“十誡”中有一誡“不準(zhǔn)崇拜金錢(qián)”,這是總結(jié)古埃及人墮落之后得出的教訓(xùn)。但是摩西的兄長(zhǎng)亞倫卻是拜金主義者,他積民間金器鑄金牛讓子民膜拜,使以色列人墮落。摩西立即下令將崇拜金錢(qián)者殺死,其中包括他的兄長(zhǎng)。處決了大部分人之后,他將手中的十誡法板扔到西奈山下,憤怒地說(shuō):“你們不遵訓(xùn)誡,要它何用?”這就是典故“摩西式憤怒”的由來(lái)。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能揣摩到歐·亨利看似簡(jiǎn)單的一筆實(shí)則意味深長(zhǎng)。他賦予貝爾曼 “摩西式的憤怒”是用心良苦的,那他為何憤怒呢?小說(shuō)開(kāi)篇就花重筆墨寫(xiě)了“藝術(shù)區(qū)”的窘境,其實(shí)就與貧民區(qū)無(wú)二:
不少畫(huà)家就摸索到這個(gè)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來(lái)了。他們逛來(lái)逛去,尋求朝北的窗戶、18世紀(jì)的三角墻、荷蘭式的閣樓,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們又從第六街買(mǎi)來(lái)一些錫蠟杯子和一兩只烘鍋,組成了一個(gè)“藝術(shù)區(qū)”。
可見(jiàn)在那個(gè)時(shí)代,藝術(shù)是被冷落的,藝術(shù)家是處在社會(huì)邊緣的。
筆者認(rèn)為,摩西因人們崇拜金錢(qián)、背叛訓(xùn)誡而憤怒,而貝爾曼的憤怒則因藝術(shù)被邊緣化。貝爾曼摩西式的胡子,表征了一個(gè)老畫(huà)匠對(duì)不重視精神財(cái)富的社會(huì)的憤怒。
(二)、薩蒂爾似的腦袋
古希臘神話中的薩蒂爾,是半人半獸的森林之神、牧神,是長(zhǎng)有公羊角、腿和尾巴的怪物。他耽于淫欲,性喜享樂(lè),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色情狂或者性欲無(wú)度的無(wú)賴式人物形象。在古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獸的牧神是創(chuàng)造力、音樂(lè)、詩(shī)歌與性愛(ài)的象征,后被認(rèn)為是幫助孤獨(dú)的航行者驅(qū)逐恐怖的神。
筆者認(rèn)為,歐·亨利之所以取這個(gè)比喻,是想要表明貝爾曼身上既有“狂徒”的特點(diǎn)(如酗酒等),又有無(wú)賴的特質(zhì)(如“極端瞧不起溫情”),不過(guò)更多的是想表明,老貝爾曼雖然在藝術(shù)上是個(gè)失意者(耍了四十年的畫(huà)筆,仍同藝術(shù)女神隔有相當(dāng)距離),但卻是不折不扣的藝術(shù)虔誠(chéng)者,是幫助像瓊珊那樣的青年藝術(shù)家驅(qū)逐恐懼、沖破困境的引路人。
正是因?yàn)樨悹柭哂斜Wo(hù)者的特質(zhì),才會(huì)為生病的青年藝術(shù)家無(wú)私付出,也正是因?yàn)樗砩系臒o(wú)賴特質(zhì),最后一句才會(huì)直言不諱自己是“看家惡犬”了。這反而顯出其率真可愛(ài)的特點(diǎn)。
二、模仿
從藝術(shù)史角度來(lái)看,模仿是人類最早的藝術(shù)活動(dòng)之一。
徳謨克利特認(rèn)為,人在藝術(shù)中模仿自然,如在織布時(shí)模仿蜘蛛,建房時(shí)模仿燕子,唱歌時(shí)模仿夜鶯等。顯然,將藝術(shù)簡(jiǎn)單地歸為模仿是不全面的,因?yàn)樗囆g(shù)還需要“再現(xiàn)”,還需要“創(chuàng)作”——但模仿的確是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老貝爾曼這輩子在做的事情,都是模仿:
貝爾曼的房間里有一塊白色的大畫(huà)布,但是那么多年從來(lái)就沒(méi)在上面畫(huà)過(guò)一筆。他替廣告商畫(huà)畫(huà)本質(zhì)上是一種模仿,為一些青年藝術(shù)家當(dāng)廉價(jià)模特,即是為他們提供模仿的對(duì)象。總之,歐·亨利用一句話概括了他的境況:幾年來(lái)沒(méi)有什么創(chuàng)作。
老貝爾曼最令人敬佩的一點(diǎn)就是,他始終惦記著他“未來(lái)的杰作”,他對(duì)待生活雖然多有抱怨,但卻一直沒(méi)有失去生活的信心,也沒(méi)有失去對(duì)藝術(shù)的熱忱。這與得了肺炎的青年藝術(shù)家瓊珊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
肺炎不至于奪取生命,筆者認(rèn)為,瓊珊之所以如此悲觀,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求生欲望不強(qiáng)所導(dǎo)致的。這與當(dāng)時(shí)藝術(shù)的窘境息息相關(guān),即青年藝術(shù)家看不到出路,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
需要有怎樣的忠誠(chéng),才會(huì)在這樣的藝術(shù)窘境里不忘初心?老貝爾曼用他四十多年不厭其煩的模仿,帶給了我們答案。他不但在藝術(shù)之路上孜孜以求,也想方設(shè)法地挽救瓊珊的性命,其實(shí)就是想換回她的求生意志,這種意志來(lái)自何處呢?就是對(duì)藝術(shù)的信心。毫無(wú)疑問(wèn),貝爾曼做到了——通過(guò)那最后的杰作。
其實(shí),那片畫(huà)到墻上去的葉子也是一種模仿,它屬于模仿的最高超境界——賦形奪真。
賦形奪真是宋人提出來(lái)的,但是在西方也有類似的例子。在貢布里希的《藝術(shù)與錯(cuò)覺(jué)》中講述了這樣一個(gè)故事:
古希臘畫(huà)家宙克西斯與巴爾拉修比賽繪畫(huà)。宙克西斯畫(huà)的葡萄引飛鳥(niǎo)啄食,而巴爾拉修卻只拿出一塊簾布。當(dāng)宙克西斯迫不及待去掀開(kāi)簾布時(shí),卻發(fā)現(xiàn)簾布就是畫(huà)。最終的結(jié)果當(dāng)然是巴爾拉修獲勝,因?yàn)槠咸阎或_過(guò)動(dòng)物的眼睛,而簾布卻騙過(guò)了人的眼睛。
三、超越
上文已提到,貝爾曼最后的杰作也是屬于模仿的范疇,并沒(méi)有提升到創(chuàng)作的境界,但是,通過(guò)這次模仿,他卻帶給了年輕畫(huà)家以生的希望,帶給她新生。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這又是一種超越。
歐·亨利為什么要以“常春藤葉”作為切入點(diǎn)?因?yàn)槌4禾偃~具有非同一般的內(nèi)蘊(yùn),在希臘神話中,常春藤代表酒神迪奧尼索斯,是歡樂(lè)與活力的象征。后來(lái),尼采將酒神當(dāng)作藝術(shù)的代表。也就是說(shuō),常春藤葉就是藝術(shù)的具象化。這正是解讀《最后的常春藤葉》的重要密碼,有了這個(gè)認(rèn)知,就會(huì)明白為什么瓊珊把自己的生命與一片微不足道的葉子聯(lián)系在一起,又為何能通過(guò)那一片葉子找到活下去的動(dòng)力。
最后的常春藤葉牢牢定在枝頭,是藝術(shù)火種傳承不絕的寫(xiě)照。貝爾曼通過(guò)最后一次轟轟烈烈的模仿,完成了自我的超越,他一直想要的杰作,就是對(duì)藝術(shù)的孜孜以求,以及為身邊的青年藝術(shù)家點(diǎn)燃希望。
且看小說(shuō)中的兩處描寫(xiě):
①“她—— 她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不勒斯海灣寫(xiě)生。”
②一小時(shí)后,她說(shuō):“蘇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灣寫(xiě)生。”
當(dāng)瓊珊病重到只有一成希望的時(shí)候.她的心事不是“男人”而是“畫(huà)畫(huà)”,當(dāng)瓊珊看見(jiàn)在兩個(gè)風(fēng)雨之夜后仍然未落的葉子,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欲望,首先想到的還是“去那不勒斯海灣寫(xiě)生”。將這兩處結(jié)合起來(lái)看,我們不難理解:在瓊珊的心中,藝術(shù)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生命本質(zhì)的超越。先前葉子的飄零恰如藝術(shù)之花的凋落、藝術(shù)命運(yùn)的淪落,這才讓瓊珊痛不欲生。
于是,在對(duì)藝術(shù)的虔誠(chéng)上,青年藝術(shù)家與老年藝術(shù)家實(shí)現(xiàn)了某種對(duì)接,兩人的超越都側(cè)重于藝術(shù)靈魂的裁剪,側(cè)重于對(duì)氣韻生動(dòng)的精神宇宙的把握。歐·亨利通過(guò)這個(gè)短篇,將批判的視角投向了現(xiàn)實(shí),對(duì)只重物質(zhì)而不重精神的社會(huì)進(jìn)行了狠辣的批判。
參考文獻(xiàn):
[1]潘幸龍.高尚的結(jié)局與矯情的人物——從《最后的長(zhǎng)春藤葉》重識(shí)歐·亨利 [J],電子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8.2
[2]鐘峰華.《最后的常春藤葉》的主題三重奏——兼向?qū)O紹振先生請(qǐng)教[J]. 中學(xué)語(yǔ)文, 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