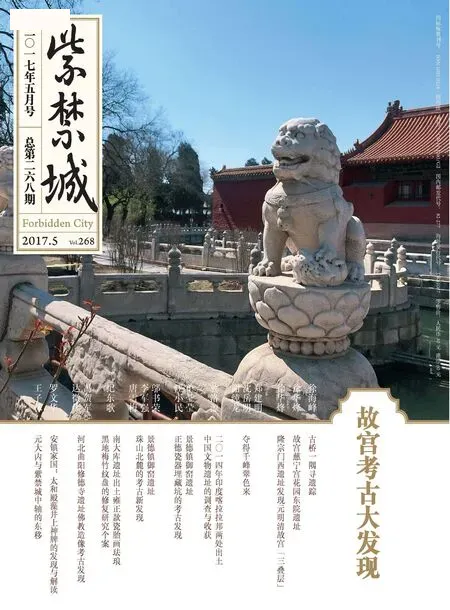延伸閱讀:故宮長信門勘探坑發現的明代早期大型墻基
延伸閱讀:故宮長信門勘探坑發現的明代早期大型墻基

長信門勘探坑
長信門為慈寧宮花園東院的北門,南與東院南門南天門,北與慈寧宮南門慈寧門構成南北中軸線。二○一六年五月,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對慈寧宮花園長信門西北側基建勘探坑進行隨工考古調查,發現一處明代早期墻基及其附屬的夯土夯磚層、底部樁承臺、基槽等遺跡。這是紫禁城首次發現明代大型墻基及建筑基槽遺跡。
在東西寬二點五米、南北長五點四米的探坑內,距地表深零點三米以下,是整個慈寧宮區域大面積存在的明后期磚鋪地面和約零點三米厚的夯土層。探坑南壁明后期夯土層下為殘存二十層、殘高二點八米的磚砌墻基。墻基以北是起到加固作用,厚約二點八米的十五層夯土夯磚層。墻基底部是生土上直接下挖的斗型基槽。在探坑底部北距墻基約三米、距地表深約四點四米的基槽內發現東西向四根木質地釘(豎樁),地釘之上為東西向一組排木和南北向一組排木(臥樁)組成的樁承臺。樁承臺向南延伸至墻基之下,樁承臺周邊基槽內夯筑厚約零點八米的碎磚層。令人驚奇的是,在依生土下挖基槽底部的傾斜狀北壁上,發現自上而下三個腳窩,遺留有堅硬的青泥夾雜竹木碎塊,應為工匠上下作業踩踏形成的痕跡。
此處大體量的墻基在層位關系、施工工藝和出土遺物等方面與慈寧宮花園東側發現的明早期大型宮殿建筑基址基本一致,可以判定其始建年代為明早期,廢棄年代為明后期。雖然這段墻基的東西向長度和南北向寬度目前暫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與其南側約六十米的慈寧宮花園東院發現的明早期大型宮殿基礎在功能上具有密切關系,是紫禁城建造之初具有宮廷分區功能的大型墻基。
墻體底部基槽的發現,為研究建筑基礎的做法提供了實證資料。經過對明早期墻基夯磚層出土碎磚瓦塊的篩選,發現大量的青胎陶質重唇板瓦、青胎陶質動物裝飾類屋脊飾件、青胎陶質溝紋磚、紅胎布紋琉璃瓦等建筑材料殘件,少量的灰陶折沿盆、灰陶罐、紅陶卷沿盆殘片和白底黑花罐、醬釉淺腹盞等殘片,都有明顯的元代風格。特別是青胎陶質重唇板瓦與元大都后英房遺址出土的同類遺物造型相同,
說明明早期紫禁城營造之初利用了元大都的建筑廢棄物作為建筑基礎材料。

墻基北側的夯土夯磚層

墻基底部樁承臺

長信門勘探坑南壁墻基
閱讀鏈接:古高粱河與高粱河
高粱河經歷了兩個發育階段,一個是作為永定河干流的古高粱河時期,另一個是非永定河干流的高粱河時期。
全新世時期,永定河在北京平原上經歷了多次擺動。大約一萬年前,永定河從石景山出山后流向東北,經海淀附近的清河注入溫榆河(即古清河),古清河結束于五千年前。八千年前永定河曾經流經北京城南,為“古漯水”。四千多年前,永定河的干流或干流的一支從石景山東流,經過今天的積水潭、后海、什剎海,轉而向南,經北海、中海和南海,流向亦莊方向,這就是古高粱河。
大約在東漢時期,古高粱河水向南擺動,改走漯水河道,延續了兩三千年的古高梁河結束。由此以后,寬闊的古高粱河故道中,形成一條由泉水匯聚的小河,《水經注》中稱之為高粱河或高粱水,即后期高粱河。后期高粱河的水量大為縮小,河道沉積物由砂礫石變為以細砂和粉砂為主,在古高粱河故道中,裸露的砂石灘上逐漸發育出一些湖泊。到金代時,這一帶的湖泊沼澤經過長期經營,逐漸開辟為金中都東北郊外一個富有生產價值的風景區。元代規劃大都實際上就是以高粱河水系為基礎營建城址的,都城內的湖泊稱“積水潭”或“海子”,皇城內的稱“太液池”。歷經明清兩代,古高粱河故道的湖泊逐漸演變、改造成為今天的積水潭、后海、什剎海、北海、中海和南海。
——參見岳升陽、馬悅婷《元大都海子東岸遺跡與大都中軸線》,《北京社會科學》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專家現場勘察后還認為,此處墻體基槽底部的黃沙層和含有青灰色有機物的生土層是距今四千年至兩千年前后海、北海至中南海一線古高粱河道的自然遺存。這對研究北京城市變遷、紫禁城歷史、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具體重要的科學價值。(本文文字由徐華烽提供,所涉圖片由王琎、徐華烽拍攝)

基槽底部北側的腳窩

元大都后英房居住遺址出土重唇板瓦瓦頭拓片

長信門夯磚層出土陶質重唇板瓦

長信門夯磚層出土白底黑花罐腹殘片

長信門夯磚層出土陶質動物裝飾類屋脊飾件

專家考察長信門探坑底部黃沙層、青泥層堆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