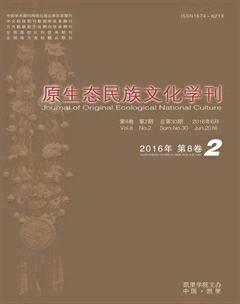法律的判決與習俗的無奈
楊戴云
摘 要:隨著國家法律的強勢推進及人們生活價值觀念和行為選擇方式的變化,近年來黔東南臺江、雷山苗區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文化色彩的風俗習慣在生活中被卷入國家訴訟領域,遭遇“法律裁判”。對當地苗族“敬橋”“偷婚”“打花貓”等習俗涉及法律糾紛經由法院判決的現象進行了田野調查,對習俗和國家法律“共同在場”進行文化人類學分析,并試圖探討此種情形對當地苗族社區傳統文化所產生的可能影響。
關鍵詞:苗族;習俗;法律判決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6)02-0067-06
一、 臺江、雷山的社會文化概況
本文調查地貴州省臺江、雷山等縣,在清代雍正年間為新辟的“苗疆六廳”中的“臺拱廳”和“丹江廳”。改土歸流后不久,由于朝廷通過機構設置、移民等強行介入當地民眾生活,引發了大規模苗民起義反抗,最后清政府傾7省之兵力耗時近5年時間(1735-1739年)方能平息[1]。為“長治久安”和減少統治成本,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朝廷對于“新疆六廳”苗民內部“細事”糾紛,準于一律適用地方習慣——“苗例”調整,即“苗人與苗人相訟之事,俱照‘苗例歸結”[2]。乾隆《大清律例》頒行,減緩了國家強行干預苗族風俗習慣的行為。民國時期,政府雖然在雷山等地強制推進“新生活運動”,但由于不順人心,習俗改革無果而終。至于邊遠村寨,當時政府更是鞭長莫及。農村的糾紛極少訴諸國家法律,鄰里之間的“細事”一般都由糾紛雙方自己消化或者寨子的長者“講理”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國家實施市場經濟改革前,盡管這一地區苗族傳統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遷,但是本文所涉及的臺江、雷山兩縣,至今仍然是我國苗族最主要的聚居區,兩縣苗族人口分別占兩縣總人口95%(臺江)、826%(雷山),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當地苗族社會核心價值觀、語言、風俗習慣等還是得到了較為完整的延續,依然對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產生約束和規范的作用。在這樣一個區域,近年來伴隨著區域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種要素流動加快,當地傳統風俗習慣與人們的現代生活行為方式的沖突有上升的趨勢。
二、民族習俗及相關訴訟案例
在黔東南苗區,“敬橋”“打花貓”“偷婚”習俗不僅是“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當地政府推出的對游客展示次數最多的 “民族原生態文化”(當地人語)之一。在臺江縣,政府每年農歷二月二日都組織引導民間群眾向外來游客展示“敬橋”習俗。在雷山縣,“偷婚”習俗一直是旅游觀光當中苗族獨特的“原生態”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由政府和民間在每年農歷十月“牯藏節”、十一月“苗年節”期間隆重推出。“打花貓”習俗在農村廣泛盛行,但由于這種習俗主要特點是在人的臉上涂抹黑紅色彩,搞笑取娛,所以不好表演,只是在農村各種“喝喜酒”的場域才真實發生。筆者調查的地點都是這幾種習俗盛行的村寨,由于人們的習俗活動中發生了糾紛,打了官司,從而導致習俗文化被法律評價。這3種習俗基本情況如下。
(一)“敬橋”
臺江、雷山地區的山寨苗民,祖祖輩輩在山谷、溪澗等險峻阻隔交通的位置,用各種樹林(主要是杉木)架橋開路。山民們有的也根據鬼師、祭師或者祖上的要求去架橋,并期望這座橋能夠保佑家中孩子們平安無事。一般在每年農歷二月初的某一天,這些人家就要帶著香火酒食前去修橋、“敬橋”。敬橋需要帶的食物主要是雞蛋、糯米、白酒、紙錢、香、豬肉(刀頭肉)等。臺江、雷山、劍河、黃平、麻江等縣都有這一習俗,而臺江這一習俗更加隆重,更加熱鬧。臺江的方如鄉、臺拱鎮等地每年農歷二月二日這一天,村寨各家各戶就開始敬橋。敬橋具體時日,視每戶農事忙閑、吉日良辰、天氣好壞等具體情況而定。農歷二月二日一到,有的農戶準備較早的,就在當日敬橋,準備晚一些的,就晚些時候敬橋,這樣敬橋活動就陸陸續續進行到月底。各地村寨,通常一房或者一戶,只能固定地“敬”一座或幾座橋,這些木橋如有損壞,則只能由這一戶或者這一房人家維修。也就是說,這些山谷、溪澗的眾多的木橋,都各有其主,只要哪一家哪一房的子孫不斷,香火就不斷,敬橋和修橋的行為也就世代傳承,由來已久,以至于習俗形成的時間無可考證。現在臺江,每年農歷二月二日政府和民間都共同組織“敬橋”活動,將這種習俗作為苗族“原生態旅游文化”(當地人語)展示給那些前來旅游觀光的客人。
2008年2月,臺江縣苗族農戶李姓為了行走更加方便,在未與張姓人家協商的情況下,將自家房屋門前不遠處的系由張家世代敬香的一座木橋撤掉,換成水泥橋。張家發現后強烈要求恢復原狀,但雙方協商未果,訴至縣法院。① ①本案例來源于臺江縣法院民事審判檔案,由臺江縣法官于2009年2月在貴州黔東南電視臺解讀案情,并專題播出。 法院認為張家木橋所處位置位于村寨范圍內,按照國家法律,行政村范圍內土地屬于村委會集體所有,因此張家無權在此長期敬橋。但考慮到“敬橋”是當地風俗,無害社會,且張家敬橋在先,李家拆橋在后,所以李家亦存在過錯,而且同樣道理,李家也無權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拆舊橋修新橋。而實際上,村委會才是“糾紛橋”的主人,村委會應當作為第三者參加到訴訟中確認自己的權利。② ②筆者在此無意探討法院這樣判決的法理問題,而只關注判決的結果及其對當地文化的影響,后文提到的另外兩起實際案例,也是基于這種思維。 法院判決后,雙方仍然不能平靜下來。因為經過法院判決后,李家同樣無權拆舊橋而建水泥步橋,張家也同樣無權要求恢復原來的橋。總之,原來的這座橋不可能繼續維持了。張家始終認為那座橋由自家世代敬香至今,現在橋被李家這樣拆掉,太傷感情了,但法律又不支持修復,非常矛盾。實際上,村寨上田園間,那么多的木橋,歷來都是誰家歷代敬香就是誰家的,橋是各有其主的。張家世代敬香的這座橋的命運,只是李家的拆橋的行為才發生了如此不可逆轉的變故。如果沒有這場官司,那么這座橋仍然是張家的橋。而且,如果本村另外兩家也對另外一座橋發生了類似的糾紛的話,村寨上的那些木橋命運的歸屬又會怎樣呢?
(二)“打花貓”
“打花貓”習俗在雷山各苗寨都很盛行。每逢孩子出生滿月、喬遷新居、建新房、結婚等喜慶事情,人們通常要“打花貓”。一般是在男女賓朋主客酒足飯飽即將散去之際,主人家取來紅色顏料混合清水、食油、黑灰等物,手搓在掌中,逢人便朝他的臉上抹去。此時此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萬一躲閃不過被抹上了,甚至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也以為是樂趣,并不生氣。其實,更主要是不好意思生氣,如果生氣了反而不好,“打花貓”是表示主人主動“熱鬧”氣氛,“打花貓”隱含了慶賀和快樂的意義。有時候大家在混亂之中,盡管互相涂抹得面目全非,但每個參與者都覺得若無其事,自得其樂地歸去。秋收過后的農閑時節,苗家人多在這時候置酒操辦各種喜事,走在鄉間,如果見到那些臉上涂紅的酒氣熏天的人們,那一定是哪一戶農家剛剛散了酒宴。2007年5月雷山苗族劉氏張姓人家背著滿月小孩回到劉家喝“滿月喜酒”。劉家設宴款待張家來的客人,按照習俗,客人于第三天告辭,主人也要在第三天送客。第三天中午時分,主客已經酒足飯飽,臨別之際,照樣有好事的人玩起“打花貓”。由于參與“打花貓”的兩雙主客,大抵已經醉意朦朧,在互相往對方臉上抹紅過程中,肢體接觸,混亂一片。此時,劉家主人婦女仗著人多,趁機將客人少婦梁氏的褲子脫掉,并在梁氏下體抹紅。其時梁氏并不完全醉酒,她發現有的男人也在圍觀,頓時覺得羞愧難當。回家以后,梁氏將此事告訴丈夫,丈夫也覺得此事系有人故意讓梁氏出丑,于是找劉家“講理”,要求賠禮道歉。不料劉家以為自己的人上次前去張家做客的時候,也受到張家婦女以同樣方式“取笑”過,因而覺得可以互相扯平,雙方兩清,誰也不欠誰,也以此為由明確表示不予賠禮道歉。但梁氏并不這樣認為,梁氏及其丈夫此時覺得自己太沒有面子了,此事必須有個了結。于是梁氏將劉家告上法院,要求劉家賠償精神損害費用2 000元。雷山法院受理案件,認為本縣苗民“打花貓”習俗是此案的緣起,應當依法判斷,同時兼顧情理和民族風情習俗,最后判決劉家向梁氏賠償精神損害費用200元,劉家承擔主要訴訟費用。判決書下達后,雙方雖然都覺得有些不平,但都沒有上訴。① ①本案例來源于黔東南雷山縣法院民事審判檔案。這個案例中,案件起訴后判決前,筆者正在雷山做田野調查,當時訪談了被告。
(三)“偷婚”
黔東南世居苗族村寨,有一種婚姻締結方式一直傳承著:未婚的女子在夜間離家出去,由心儀的男子接到該男子家,次日或隨后幾日由該男方家族派人攜禮正式通知女方父母,同時,男方家舉行婚宴,婚宴之后即算婚姻締結完成。這種婚姻締結方式,雷山苗語是“at kat xit hnians”,可直譯為“偷婚”,意為“悄悄結婚”。這種習俗之獨特之處,其一,它僅在苗族村寨流傳;其二,當地苗民認為它理所當然,如果內部成員不按這種習俗結婚就會遭來非議。在苗族社區成員看來,女子夜間出嫁,男方夜間迎娶,是合情合理、亙古不變的。這就與事先經過父母同意的“明媒正娶”“白天出嫁”的域外婚俗頗不相同。此即為“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這種“偷婚”是以婚前男女青年通過長時間“游方”,互相了解,兩情相悅為基礎的。但這種兩情相悅受到當地傳統行為習慣的束縛,也就是女方在成婚之前,一般從未到過男方家。現今黔東南很多苗族村落,這種結婚方式仍然流行。在這里,難以看見女子在大白天出嫁的情況。女子正式離家出嫁的時間總是選在夜間,出門的時刻視具體情況而定。一般是女子事先與該男子共同選擇一個美好的時辰,從容出走。也有的女子擔心父母察覺或者阻止,走得比較倉促,也就不管時辰了,只要自己心儀的人一到就馬上走。“偷婚”習俗成就了無數美好的姻緣。但是,也有因為父母反對和女子反悔導致婚姻失敗的例子,只是這種例子為數極少。
2001年11月雷山縣永樂鎮苗族楊家女子與鄰寨的蔣家男子“偷婚”,第二天蔣家即攜禮派人正式稟報,遭到楊家父母反對,此時楊女也感到反悔,在來不及帶回自己的結婚服飾物品的情況下,只身從蔣家回到父母家。楊女回來后,楊家父母多次到蔣家取回女兒的衣物,蔣家表示予以扣留。楊家無奈訴至雷山法院。法院判決楊女帶到蔣家的結婚物品,由蔣家全部退還。判決執行2年后,楊家女子嫁到了另外一個寨子。② ②本案例來源于黔東南雷山縣法院民事審判檔案。筆者于2008年3月到達原告的村寨走訪。 這類糾紛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女子一方通常都不起訴(主要是沒有意識到可以打官司),而是一走了之。為了挽回場面,男子一方通常很強硬地扣留女子的衣物,不予退還,而女子一方除非動用家族力量,往往是沒有辦法再要回自己的東西的。女子在承受精神和物質損失的同時,也認為這種結局乃因當初自己輕率的“偷婚”行為所導致。如此,萬一遇到此類事情,當地的人們無不以為是人生的憾事。近年來,這類糾紛轉換為訴訟案件的已經越來越多。這表明,國家多年來“送法下鄉”方案的實施,已在邊遠少數民族鄉村社區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至日益改變當地糾紛的傳統的解決(消解)模式。
三、民俗風情遇到“法律判決”
本文調查的“敬橋”“打花貓”“偷婚”等習俗,都是黔東南苗族地方盛行的風俗,其所伴隨的訴訟現象,都是這幾年才出現的。而臺江縣“敬橋”糾紛和雷山縣“打花貓”糾紛,在小地域的各自村寨中,均屬首例。發生在臺江縣的“敬橋”案例,臺江縣法院于2009年春節過后不久,就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電視節目中專題播出。在臺江,“敬橋”習俗是民族旅游文化。法院在電視新聞頻道中播出案例的做法,可視為國家法律對當地“民族文化”的回應。法院判決意味著國家法律對地方習俗文化的評價,并在今后生活中產生影響,這個過程可能是潛在的長期的,一時還不能完全看出來。但總體而言,隨著人們對類似糾紛解決方式的效仿和訴訟個案的增加,法律肯定會對這些邊遠山區少數民族風情習俗起到指引的作用,進而改良這類習俗,甚至使其變異或者喪失,導致這些地域文化的變遷。
(一)指引
“文化”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觀念、制度和實踐三個層面[3]。在文明社會,無論是人們觀念中的習慣法規則,還是寫在紙上的國家法律,都要通過暗示(認可)或者明示(強制)的實踐方式得以實現,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法的指引功能。只不過這種指引功能的發揮,通常會受到當地的地理條件、生活環境和行為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在本文案例中,僅僅從涉案的經濟利益上看,那是微不足道的,當民間的協商機制用盡,只要一方或者對方心里不服,還是要打起官司。但他們打官司,據說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一口氣”。為了爭一口氣,除了打官司,別無退路。其實,封閉的小地域的社會里面,面子和尊嚴是很重要的,越是在小地域村落范圍內的“熟人”社會中,“面子”意識就越強,苗族村寨也不例外。人一旦丟了“面子”心里就很難受,所以“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層皮”的心理就很嚴重[4]。通過打官司經由法院判決勝訴,是自己在村寨當中顯得“很有面子”的有效證明。在“打花貓”的訟例中,由于“打花貓”是村寨上的習俗,這種酒后的娛樂行為在當地看來是習以為常的。但梁某這次參與活動,因為褲子被脫,超出了“打花貓”習俗的娛樂底線,梁某的心理感受也就不再是大家所認為的那種“正常娛樂”了。梁某回家不久就向劉家提出賠禮道歉的要求。可是劉家至此仍不以為然,因為畢竟大家都是親朋,所以還責怪梁某小氣,竟然提出如此要求,感到很傷和氣。為了挽回面子,梁某在地方上的一位訟師指點下找到了“面子”與國家法律的關系,“丟面子”可以“精神損害”為由提起訴訟。法院最后判決劉家賠償了200元,這個賠償數額是極少的,可能大大低于梁某打官司所花的費用(訟師費、路費、訴訟費等),但畢竟獲得了賠償。而法院判決不僅是本案決斷本身,還隱含了另一個判斷傾向,即盡管這種習俗滿足人們娛樂生活的需要,但對于其中具有侵害事實或者侵害危險的行為,國家法律是否定的,而不問此種習俗的是否具有民族風情的特質。這可以理解為主流文化對于地方文化的沖突。近年來,邊遠山區外出務工的人員流動已經加快了,不同文化交融也在加深,苗民不僅人要走出封閉的村寨,思想也從山里走到山外,異文化的浸染導致多元意識,特別是經濟利益追逐增強了個人權利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打花貓”這個案件現在看來雖然屬于首次,但并不等于今后不再發生。雖然這種習俗承載了苗民設宴飲酒當中的享樂和激情宣泄的功能,但由于這種實踐活動中的粗獷無羈的行為,容易越過娛樂的底線,使參與活動的人可能受到某種輕微的身體傷害和人格受辱。訟例的出現,突出了這種暗示和隱喻,對當地人的類似的行為起到指引效應,而“移風易俗”這樣觀念也變成事實。
(二)改良
隨著國家法律持久深入的宣傳,“送法下鄉”“以案說法”在山區農村反復實踐,“法律”“權利”的意識也就在人們的習慣心理和行為中逐漸形成,并分化出來。對很多人來說,私了、調和、認命等解紛的形式逐漸偏離了傳統的“講理”模式,不再成為最佳選擇。比如“偷婚”習俗中,苗族村寨男女結婚前,女子是從未到過男方家的,平時都通過親戚、熟人打聽男方的家庭。女子出嫁的時候,也只有在夜間跟著男方走,到第二天才看到男方的家庭。這在客觀上構成了對女子的結婚知情權的極大限制,對未婚女子是不利的,但大多女子此時也認命了。本文調查的“偷婚”案例中,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支持了女子在“偷婚”以后的反悔行為,這實質上是對女子權利的補救。同時,還防止了民間婚姻習俗中可能存在男方騙婚、濫用權利(比如扣留女子衣物等)強行成婚的情形。臺江、雷山苗族村寨盛行“偷婚”習俗,就保護當地社區傳統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偷婚”確實是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偷婚”固然傳承了古樸的習俗,但也保留了其中不利于保護未婚女子的成分。當這種習俗被糾紛卷入到國家法律評價體系里面的時候,法律中的“女子”更多的是個人權利的符號,而不再是“偷婚”習俗村落中的女性。苗族青年男女在“偷婚”中,對于“女方反悔,男方強行扣留女方的財物”的習慣,法院的判決書明確援引了國家法律的禁止性規定。這樣,本地習俗文化中與法律相悖的成分就受到了國家強制性的否定,這種信息反饋到民間,從前的“偷婚”劇本將來如果再上演,“女方反悔,男方強行扣留女方的財物”的實質情節就會受到國家法律的否定和排除,而只保留一套改良了的習俗。
(三)變異
我們知道,打破一種傳統的秩序或者否定一種風俗文化并不難,難的是改變這些秩序與風俗賴以存在的客觀條件。主要表現在:其一,生存環境決定習俗的完整性。比如雷山縣境內的交臘村,全村共61戶,都是苗族,村寨處于封閉的雷公山核心圈的高山之巔,山民們平時總是要徒步5-6小時才下到縣城趕集。“人間四月芳菲盡,山上桃花始盛開”是那里的地理氣候寫照。2004年,雷山縣政府決心將交臘村作為退耕還林和整體移民搬遷的重點工程配套實施,專門從狹小縣城有限的住房用地中拔出地盤,建成了漂亮的現代移民住宅區,請交臘村“下山”。但由于下山以后意味著失去土地,無法生活,結果只有幾戶愿意“下山”,雷山縣政府最后只好作罷。像這些村寨,人們敬橋就很虔誠,很莊重,敬橋習俗都完整地保留。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情形就不同了。現在許多村寨交通要道上的木橋都被公路取代了,甚至一些不適合修建公路的地方的木橋都用水泥鋼筋改造成了各種現代的便民橋,原來由各家各戶敬香的木橋也變成了水泥橋。面臨這種變化,有的村民也就不再給這些鋼筋水泥橋敬香了,而只是繼續在田邊地角、山間叢林小道木橋上敬香,這樣,他們的“敬橋”信念才繼續延續。其二,解放前因為農村鄉鎮醫療條件奇缺,小孩一旦生病,大多生命難保,所以農戶敬橋祈福小孩平安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解放后,農村醫療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小孩生病大多轉向求諸國家衛生醫療,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敬橋祈福平安的觀念也就逐漸衰退、淡出。其三,“敬橋節”作為一種原態的習俗被表演,使“敬橋”與“兒孫平安”之間的內在的信仰關聯越來越偏離傳統的意義,其中敬橋“神性”進一步淡出,加劇了敬橋節的世俗化。在臺江縣,在政府引導下每年都向外來游客隆重展示敬橋活動,雖然參與活動的人還是村里人,敬的“橋”還是真實場景下的木橋,但為了滿足大量的游客觀光,當地政府將農戶原來分散“敬橋”的單個行為集中起來,不斷復制和擴大。游客是陌生的“他者”,他們看完了這種場面就走,根本不知道山寨里面真實的敬橋情況。一些國外游客看到當地苗族不分男女老幼都穿上盛裝,兒童胸前都掛著裝有彩蛋的網袋前往“敬橋”的時候,還以是為苗族的“兒童節”。這類活動年復一年地展示,也讓村民漸漸改變他們原來對于“敬橋”的看法。在田野訪問中,有的村民認為敬橋還是靈驗的,也有的村民認為敬橋“是個形式”。在這種趨勢下,筆者專門就張家和李家“敬橋”官司走訪了一些村民,大部分村民認為李家“自私”,“拆張家的橋是不對的”。很多村民不知道是自己祖上有多少代人在敬橋,后代只是照著去敬香就是,而且,自己敬自家的橋才得到靈佑,所以各家各戶絕對不會去敬別人家的橋,也不會拆別人家的橋。在村民看來,村寨上的橋雖然很多,但都各屬其主,不會亂的,哪座橋屬于哪一人家的,都清清楚楚。這與法院判決下的橋的“法律權屬”是完全不同的。但現在法律這樣規定,“我也不知道”“沒有辦法”,當地一個村民如是說。還有一個村民說“敬橋是迷信”。看來,“敬橋”習俗只能“或在封閉中保存,或者在開放中變質,沒有第三種選擇。”[5]
(四)喪失
習俗是隱含著行為規則的,有的習俗的規則和國家法律秩序并不相悖,存在于人們生活中。法律是國家秩序化身,當人們的行為沒有觸及法律,則國家法律是看不見的,當人們的行為違反法律的時候,國家法律就會經過特定程序顯現出來。習俗的規則也一樣,如果誰違反了規則,那么將導致習俗過程的無效。現今,苗族地區在前所未有發展的同時,人們傳統的意識、觀念也在不斷地經歷新的沖擊。在這一過程中,比如道路交通、電信、通訊、鋼鐵水泥的人居建筑、工業日用品等日益變得必不可少,而地域性的思想觀念和內化了地域性思想觀念的人們的各種行為和風情習俗,也正在面臨著重構、變異甚至迅速消失的現實。比如代表村民原始禁忌和泛靈信仰的敬橋習俗,被暗示成為一種稀有的古代遺風,被引導成為外來游客到達村落中的娛樂視角,原來的橋的“神性”在村民心中的已經不再。敬橋的人越來越少,對橋神祈福的信念越來越淡。而在這時,發生了“敬橋”官司,一向看重“橋的神性”的張家,待法院判決(法院既不支持張家恢復的要求,也不同意李家拆建的行為,而判定應由村委會處置)之后,反而離“自己家”的這座橋越來越遠了。對張家而言,這其實無異于一種敗訴。這個結果對村落內部那些虔誠敬橋的人們的心理沖擊,應該是不小的。而與此同時存在的一個事實是:“敬橋”是苗民為了祈福小孩平安而為的,當小孩長大成人以后,家里就沒必要繼續敬橋了,比如現在的臺江縣城附近的幾個苗族村子,許多人家因為沒有小孩,或者小孩已長大成人,他們已經多年不敬橋。這可以說明,敬橋習俗有的地方一如既往地盛行,有的地方正在受到沖擊,有的地方正在消失。
四、結語
“文革”結束后,黔東南臺江、雷山苗族的許多風俗習慣日益復蘇。“打花貓”習俗一直流行于民間,而“偷婚”“敬橋”不僅在民間盛行,而且先后在1990年代后期發展成為當地官方倡導的民族旅游文化。上述“偷婚”“敬橋”“打花貓”糾紛及訴訟,不僅可以理解成一種行為,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事件。這種行為和事件,在當地尚屬首次的實踐,雖然確實讓很多當地的人感到“不適”,但畢竟不是外來的陌生人而恰恰是內部成員自己的選擇。這些習俗經過法律“判決”后,必將對人們下一次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可看成是具有相同意義的地方文化以不同個體意識的表達方式,正在卷入“國家化”的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內部的一些“有特質”的民族文化成分最終會歸于“沒有替代物的喪失”[6]567。這種變化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其一,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因之文化也必須隨之變化”;其二,“文化內部的人觀察文化特點的方式發生改變,這會導致社會解釋其文化的規范和文化的價值觀的方式發生改變”;其三,“與其他群體的接觸,引進新的觀念及以做事情的新方式,最后造成傳統價值觀念和傳統行為方式的改變”[6]558。可以說,每一種習俗文化的發展,無不以當地社會結構及其文化的變遷為基礎。由于習俗的實踐通常是通過人們一系列行為來表達,當糾紛發生并打起法律官司的時候,與糾紛有關的行為就被分離出來,接受法律評判。但因為這些被法律評價的行為是統一于表達習俗的一系列行為當中的,一旦其中的一個行為被法律評價,則意味著整個習俗行為受到了相應的影響。如果法律的這種評價是否定的,則意味著這種習俗被法律內涵的國家主流文化觀念所否定。而國家法律向習俗的滲透,開始都以規范民間習俗為目的[7]。如此一來,在“急劇性破壞的方式”比如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等被禁止后,當今的習以為常的法律訴訟方式也就可能成為一種使民族風情習俗受到潛在破壞的“合法方式”,而正是這些訴訟直接將法律中的國家觀滲透到這些民族風情習俗之中。由于這種滲透方式具有“合法性”,使得人們不容易反思它對地方民族文化的可能沖擊。如果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不斷介入地方民族風情習俗糾紛的做法成為一種常態,則法律中的國家觀也就更加容易滲透到這些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習俗中。而每個民族地區的生活總是紛繁復雜的,各具特色的,但隨著類似訴訟的增加,那些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習俗將不得不面臨現代的新的變化過程。
本文得到了徐曉光教授、謝暉教授的批評指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 《苗族簡史》編寫組.苗族簡史[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5:111-114.
[2] 蘇 欽.“苗例”考析[J].民族研究,1993(6).
[3] 吳大華.論民族習慣法的淵源、價值與傳承[J].民族研究,2005(6).
[4] 徐曉光.涉牛案件引發的糾紛及其解決途徑[J].山東大學學報,2008(2).
[5] 謝國先.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變遷的幾點原因[J].民族藝術研究,2004(2).
[6] 哈維蘭.當代人類學[M].王銘銘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67.
[7] 趙旭東.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15.
Legal Judgment and Custom Helpless: A Case Study of Miao
Areas of Taijiang and Leishan in Qiandongnan
YANG Daiyun
(Qiandongn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Kaili, Guizhou, 55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law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life values and behavior selec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ethnic cultural customs in Miao life in Taijiang and Leishan involved in national litigation. This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Miao customs and legal disputes and made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generated effect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local Miao communities.
Key words: Miao; customs; legal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