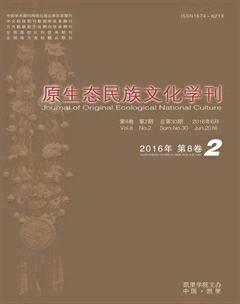鄉村政權結構演變
張光紅+趙歡
摘 要:通過對滇東北林村的考察,認為杜贊奇的“村落組織由血緣集團和家庭集團組成,村政權是政府和宗族共同作用的結果,宗族是鄉村政權運行的重要力量”之見解在現今村政的基本結構和演變上缺乏解釋力。隨著生境的流變,農村政治體系之建構由宗族勢力轉變為社會個體,后者獲取政治地位并非依賴宗族而是依據社會關系和經濟能力。
關鍵詞:鄉村政權;宗族勢力;杜贊奇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6)02-0144-05
一、問題的提出
宗族的產生和延續,在我國歷史上存在已久,從早期文獻中即能窺見一二。在《禮記·大傳》里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同姓為宗,合族為屬”,在《白虎通》里的“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等等,均是講述古人設立宗族制度以此達到敬宗收族的作用。對于宗族的解釋,《白虎通》卷八“宗族”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留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林耀華對我國歷史上有關宗族的理論進行梳理和研究,根據前人的理論積累和自己的理解,指出所謂宗族“大體說起來,宗指祖先,族指族屬,宗族合稱,是為同一祖先傳衍下來,而聚居于一個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緣團體”[1]。杜贊奇通過對中國華北農村的研究,認為宗族是指:“由同一祖先繁衍下來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財產和婚喪慶吊聯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莊。”[2]杜贊奇利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會調查部,根據1940-1942年間調查編輯成的六卷本《中國慣行調查報告》研究中國村級結構。他主要運用慣行調查中有關河北和山東2省6縣6個村莊的資料,對20世紀中葉以前的華北地區國家政權建構中的國家和鄉村關系進行了考察。
中國村莊政治運作模式在杜贊奇之前就有不少研究,其中有馬克思與韋伯的“附屬論”,認為中國鄉村依附于城市,國家政權牢牢的控制著鄉村社會,鄉村精英是國家控制村莊的工具,這一觀點認為傳統中國是“強國家,弱鄉村”。韋伯于《經濟與社會》一書的第2卷中進一步的指出,將地方行政機構正規化,使下層政權與中央保持一致,從而有利于鞏固國家政權。他認為在現代官僚機構下要達到這一目的有3個條件:第一,官員有可靠的薪金;第二,職業必須穩定,并且有向上晉升的機會;第三,官員們須有明確的職位感,做到下級服從上級。以旗田巍、平野義太郎等日本學者認為,中國村落是一個共同體,具有獨特性和自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抗國家[3],學者稱之為“自治論”。瞿同祖、張仲禮等學者采用了一種折中、調和的方式,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既不屬于“附屬論”,也非“自治論”,而是一種“鄉紳社會”,鄉紳在國家和鄉村社會之間起著中介作用。黃宗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國家—鄉紳—村莊”的三角解說模式[4]。杜贊奇在黃宗智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權利的文化網絡”建構自己的解說模型,并認為鄉村社會是國家、鄉紳和村莊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對日本滿鐵慣行調查資料的探究,他提出:中國鄉村治理需依賴國家權力的下沉和地方宗族的調適和整合,兩者的相互調整方能實現鄉村的有序的發展。
杜贊奇認為,中國鄉村是以宗族為基礎而建構起來的,鄉紳是宗族利益的代表。在國家權力下沉的過程中,需借助鄉紳在村莊的影響力,才能使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保持一致。而鄉紳是自我宗族的代表,他代表宗族的利益參與地方政權之中。據此杜贊奇提出中國鄉村村政是地方政府和宗族作用的結果,宗族是鄉村政權運行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生境的流變,村民宗族意識的薄弱,農村政治體系建構的二元主體之一的宗族,在現代化潮流下,其在村政權的地位已逐漸被社會個體所取代,后者在獲取政治地位的過程中,并非依賴宗族而是依據社會關系和經濟能力。因此,杜贊奇之見解在現今村政的基本結構和演變上缺乏解釋力。本文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深入滇東北林村訪問村民、村干部。通過對村莊宗族的歷史與現狀及其連帶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窺見村政權結構由政府-宗族轉變為政府-社會個體的模式。
二、鄉村宗族認同的流變
傳統鄉土社會由于固有基礎條件、生計模式、鄉村主體情感歸屬等原因,形成生于斯、活于斯、死于斯的村民社會。在生計方式單一的滇東北林村社會,土地的開墾和形成是村民世代累積的結果,它不僅是人們最主要生存資料獲取的依據,也是家庭建立和穩定的根基。與此同時,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嚴重地制約了村民居住方式的選擇,家庭成員依據土地而選擇定居方式。傳統社會時期的林村以具體生境下的需求為依據形成了血緣與地緣的重疊,大家庭的析分、新家庭的建構,使林村形成以宗族為主要鄉村組織的傳統村落。宗族的產生和形成,是村民根據需求利用文化與具體生境耦合的結果。宗族于傳統村落社會的重要地位,被持有主體運用到鄉村政權建構之中,形成最初的以政府、宗族為主體的鄉村政權雙軌制模式,隨著社會的變遷宗族于鄉村社會的“潛隱”,鄉村政權結構做出相應的調整,林村于傳統社會時期的村政權結構與宗族密切相關,下文以宗族為切入點對鄉村政權進行闡述。
(一)宗族認同和村落利益共同體的強化
祭祖是林村20世紀最為盛大的活動,它是以宗族為單位而舉行。每年舉行1次,日期選定于清明,同屬一個宗族的村民將到指定地點集合共同祭祖,通過儀式和祭祖中的相互配合,構建宗族成員的共同記憶。在這天,宗族成員為祭祀忙碌不已,婦女留在村中做飯,族中男性成員聚集在一起,為祭拜埋葬在此地的第一代祖先做各種準備。拜祖之前,族中已成年的男子共同商議推選出一名德高望重的族員成為拜祖的主持者,其他成員將會遵照其吩咐進行相應的工作。主持者根據各成員在宗族中的身份地位,讓其承擔祭祀中相應的儀式工作。
祭祖儀式潛意識地塑造宗族成員源于同一祖先的記憶,同一血緣的社會意識加強了宗族成員聯接。林村人認為,宗族的幸與不幸主要由祖先的神靈控制,祖先滿意后人的社會行為,宗族成員就得福,具體表現為家人安康、人丁興旺、財富廣進等;祖先怨恨,宗族成員將會遭受災難,如患病遭災、人丁稀少、不幸遇難等。在林村,每一宗族都有一套據說是由祖先傳承而來的族規,祭祀祖先期間,每一宗族成員則在先人墳前背誦族規。如果族員沒有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族規于宗族中行事,即使族人不知曉,他也將會遭受祖先的懲罰。村民相信祖先注視著后人的一切,很大一部分宗族的活動是由祖先無形的權力控制的。但是宗族成員的年老者認為,族中成員只要按照祖先留下來的族規行事,他將會受到先人的庇佑。而每年清明祭祀祖先之時,正是宗族族規在成員中傳承和強化之時。
在20世紀,林村每個家族男性成員自六七歲起,就會在父親和族中長輩的監督下背誦族規。族規內容繁多,但是真正要求宗族成員熟記的只是極少部分。每年在清明祭祖儀式中,族中所有男性成員將會聚集在祖先的墳前共同背誦族規。若被發現不會背誦必須熟記的族規的族員,他將被單獨叫出來并站在宗族成員的正對面,由族中長輩進行批評,并把這名成員作為離經叛道的例子予以教訓孩子。林村宗族族規以團結族員,共同維護宗族利益為核心,如以下是李姓宗族族規核心:
李姓成員應當相互友愛,彼此互相尊重。族中長者有對晚輩施以教育和幫助的義務,而晚輩則必須尊重長者。宗族成員不能為一己之益,而虧損其他成員的利益。沒有宗族,個人就如無根浮萍,難以尋覓立足之地。宗族成員需彼此互助,同時有能力的成員負有提攜、幫助同族成員的職責,并盡力為族員爭取利益,讓祖先享有更多的香火之食。
從族規可看出,李氏宗族力圖培養族員的認同性。從血緣角度來講,著重強調宗族成員來源的統一性,強化其血緣關系;就經濟方而言,強調利益的共同性和互助性。宗族的族規核心使族員的內聚性與合一性得以強化。在鄉村社會,若村民缺乏社會關聯度,當遭遇突發事件時則難以調動任何有效的關系資源解決問題。而作為血緣和地緣結合體的宗族是村民于特定環境下選擇的結果,宗族成為村中最為主要的村落組織,不僅解決村民之間的矛盾,還成為族群成員利益共同體的代表。
村委會對政府給予林村的資源具有分配權,而村干部是資源分配的直接執行者。由于宗族組織的觸角延伸至林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村干部候選人則由族中長輩推選出而后由家族成員共同投票選舉。村干部數量和所處職位,決定了家族成員資源獲取的數量和名額的多少。因此,宗族于鄉村政權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宗族認同的變遷致使傳統鄉村二元政權的轉變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現代化潮流的急速擴張之下,市場經濟的觸角延伸至鄉村的每個角落。新興的市場經濟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主義迅速占領了農村的生活空間[5]。交通的日益便利和通訊的迅捷,加強了城鄉之間的往來。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以玉米和土豆為主要種植對象的林村,難以滿足村民的生活消費需求,出于生計的訴求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村中出現了第一批務工村民。由于鄉村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村民的生活需求,致使林村外出務工人口呈持續上升的趨勢。當老一代務工者年老之后回到家鄉,其早年輟學的子女已在外務工多年。有的還未成年就隨家人外出務工,對家鄉的記憶早已模糊。多年的生活經歷造就了許多年輕人對經濟的追求超過對家鄉宗族認同的心態。
自21世紀以來,村中超過一半的村民長期在外務工。每到逢年過節之時,加班費高出日常工資的數倍,許多村民長期不回家實屬常態。宗族成員的大量外出,致使每年一次的宗族祭祖大會逐漸衰敗,甚至到了不得不取消的地步。此外,外出務工的族人返鄉后,出于生活便利的需求,許多村民不選擇在林村建房,自己在林村的土地則送給仍居住于此地的人耕種。對村民來說,土地也不再是村民生活的主要生產資料,它已經喪失在傳統社會中對農民的功效。固定財產喪失其原有的功能,對經濟和生活便利的需求客觀上促進了村民的流動。林村許多村民從祖先的故居地遷移到其它村民小組或村落,宗族成員共居一地的現象正逐漸消亡。宗族成員生計方式的轉變(由務農轉向務工)、生活狀態的變更、居住地的遷移、共同宗族儀式的消亡,使宗族族規對其成員的約束和控制日漸減弱。宗族成員的居住形式由聚居轉變為網絡狀的散居,成員居住地就如網上的結點,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林村乃山地地形,多高山峻嶺,村中唯一的公路高低不平,每到下雨天濕滑不堪,這嚴重的影響了宗族成員的交往。
認同并非一成不變,是隨著生境而進行相應的調適和整合。人們會根據自身所處的環境選擇、建構自己的集體認同[6]。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鄉村社會主體生境的極速變遷致使林村宗族認同產生了極大的流變。過去宗族認同依賴的共居地、集體記憶、祭祖儀式、共同財產皆已發生流變,它們在宗族中的功能隨著生境的變遷而不斷地被弱化,以致使宗族成員對宗族的認同逐漸變弱。人有多重認同——家庭的、性別的、階級的、地域的、宗族的。環境在不同的時候,這種或那種認同會優先于其他的認同。在流動性極強的社會中,血緣的差序格局左右著認同的層次性,以自我為中心認同的強弱由內向外遞減,離主體越遠以情感為連接的紐帶越脆弱。另外,當一個宗族擴展至一定的程度時,人員增多,關系網錯綜復雜、利益交織,隨之伴隨而來的是為了利益而產生的沖突、矛盾,此時,維持宗族均衡、統一的因素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宗族的破裂。林村宗族正處于破碎和裂變之中,代之而起的的并不是另一個宗族,而是小家庭。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化的現代社會,林村社會空間充斥著市場消費主義的氣息。家庭成員共同擁有財產、共同生活,并承擔著在經濟領域的功能,宗族原有的社會功能正日漸被家庭所取代。其中最為顯著的是鄉村政體的構成由過去杜贊奇所言的政府-宗族,轉變為如今的政府-鄉村個體。家庭是林村社會的主體,當人們提起村中的某人時,人們往往把他納入家庭之中而非宗族體系。個人獲得極大得聲望人們認為這是家庭努力的結果,家庭的當家之人更是被人們爭相夸獎和學習的對象。家庭從宗族體系中脫離出來,前者具有更大的自由和競爭性。村民從事社會事物時依靠的是經濟能力和社會關系。宗族認同弱化的最直接體現是——村務管理、公共活動以及構成村公所成員名額的分配,由以往的以宗族或亞家庭為劃分轉變為現今的家庭劃分為基礎。
三、鄉村政權二元雙軌制的替換和形成
村治是指村莊的治理,也就是村委會一級的治理。實現村莊的法治是國家追求的目標。法治是農村秩序的保證,但是當法治的成本太高時,傳統的鄉村治理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7]。當然,這種選擇需要與社會本身的慣例結合,也就是說,法治需本土資源。鄉村治理在國家和農村主體的參與之下共同完成。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政治絕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道上運行的。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還自如的雙軌形式。”[8]由此可知,雙軌制是實現農村治理最優化的選擇方式,成功的實現了兩者的對接。然而隨著生境的流變,雙軌制主體將會做出相應的調整。尤其是自下而上一環中農村主體變化更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市場經濟延伸至鄉村各個角落的是國家政權。由于國家權力的極力下沉,農村的一切重要事務始終按照國家的意志在運行,其結果也處于掌控之中。通過在林村的田野調查得知,改革開放以前,村里每次選村支書、村主任時,鄉政府會把選擇人選交給林村自行決定。當時村民宗族觀念極強,每個宗族經集體商議選擇一名德高望重的族人參予村干部競選。一旦宗族參選人員確定,即使族中的其他成員想要參加競選,在集體意志和公共利益之前他也必須放棄,若執意要做將會遭受宗族成員的懲罰。在當時有經濟能力和社會關系的村民不一定會被宗族推選出來競爭村干部,但是他有義務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為家族成員獲取選票,這一選舉方式使當時村中部分有本事但又不能參與競選的村民悶悶不樂。在選舉時為了顯示政府的公平,鄉里將委派一名干部監督選舉。選舉這天,每個宗族將推選出一名成員參選村中主要領導人,獲取選票最多的人將是主要村領導。對地方政府來講,獲得主要領導職務的那個宗族,無疑是地方影響最大的,由該宗族配合地方政府一定能治理好鄉村,使鄉村社會穩定而持續的發展。
然而,隨著林村生境的流變,宗族在鄉村的職能逐漸被家庭所取代。鄉村人口的急速流動和遷移,使宗族逐漸失去其根基——成員。沒有成員的宗族已喪失其原有的功能,并逐漸的退出林村的社會結構網絡之中。由于村莊主體結構由宗族轉變為家庭,因此地方政府逐漸意識到,依靠宗族而推選出來的鄉村領導難以維持林村的社會穩定。所以政府取消鄉村政府-宗族的治理模式,轉而施行政府-鄉村個體雙軌制村政。家庭在林村的主體地位隨著宗族的式微而日漸凸顯,家庭成員依賴經濟和社會關系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在林村頗有聲望的這類家庭主要成員,利用原有的社會關系與地方政府主要職員取得聯系,并獲得政府的認可,這是雙軌制的一軌。該軌的主體是鄉村社會主體,在鄉村政權中處于被動位置。于上,他要獲得地方政府的認可,這樣才會把他納入鄉村政權領導成員的選舉之中;于下,他需要取得鄉村成員的選舉支持。在這期間,該社會主體的社會關系和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關系主要作用的對象是政府,經濟主要運用于鄉村選舉之中。村政權雙軌制中另一軌的主體是政府,它在其中占主導地位。該軌的實施形式主要是從上往下而被呈現,在村莊領導人的選舉中地方政府有優先選擇權,當人選確定后,再由林村村民進行選舉,若通過政府和村民的雙重認可后,那社會主體在接下來的3年內將是村里的主要領導。
從林村選舉過程中,我們可發現村莊政權雙軌制,一軌是至上而下,另一軌是自下而上。在地方政府掌握主動權的語境下,也充分給村民自由選舉的權力。從雙軌制中可看出,與政府-宗族村政權的結構模式相比較,政府-社會個體村政權模式中政府占更大的主動性。之前是由鄉村選出領導人,政府給予許可,從而產生鄉村領袖。而現在是政府指定候選人,由村民選舉,從而政府給予認可。如果政府推選出來的社會個體沒有獲得村民的認可,那么政府將另換他人。沒有獲得村民認可的社會主體,在政府看來他在治理鄉村社會時將困難重重,所以將對他棄之不用。
綜上,鄉村村級行政主體由傳統的宗族演變成如今的家庭,是現代化潮流下農村社會變遷的具體表象。從鄉村政權的轉變模式中可知“一切制度的形式是人在一定的環境之內造下的,不變的并不是它的形式,而是人用它來滿足的根本需要,和滿足時的效力原則”[9]。杜贊奇對鄉村政權的模式解釋在當時的確有一定的普適性,然而任何理論隨著社會的變遷都會顯示出它的局限性,即使頗有前瞻性的理論,也會顯示出對社會解釋不足的缺陷,所以鄉村政權結構的演變實屬常態,我們要做的是對其完善和擴展。
參考文獻:
[1] 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73.
[2]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M].王富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65.
[3] 李國慶.關于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論戰:以“戒能—平野論戰”為核心[J].社會學研究,2005(6).
[4] 鄧大才.超越村莊的四種范式:方法論視角——以施堅雅、弗里德曼、黃宗智、杜贊奇為例[J].社會科學研究,2010:136.
[5] 王 華.農村“高音喇叭”的權力隱喻[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31.
[6] 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M].龔維斌,梁警宇,譯.北京:中央出版社,2002:34.
[7] 賀雪峰.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46.
[8] 費孝通.鄉土重建[M].長沙:岳麓書社,2011:49.
[9] 費孝通.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9.
The Evolution of Rural Power Structure: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Lin Village in Northeast of Yunnan
ZHANG Guanghong,ZHAO Huan
(Humanities College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Lin Village in Northeast Yunnan, this present article held that Prasenjit Duaras viewpoint—“Village organization is comprised by blood group and the family group, the village political power is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of government and clan, clan is an important power of rural power operation.” lacks of explanatory power in todays basic villag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habit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from the clan power to the social individual, the latter depends on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power instead of clan.
Key words: rural power; clan power; Prasenjit Du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