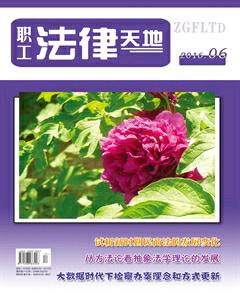簡析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功能
唐枏
摘 要:一般來說,法的價值的實現(xiàn)是法的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的過程和結(jié)果,也是法的價值沖突被解決的過程和結(jié)果。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也正因為激勵功能,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必將對科技進步和社會發(fā)展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其作為一種獨特的法律規(guī)范對知識創(chuàng)新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開發(fā)、轉(zhuǎn)化及保護程度將更為典型地體現(xiàn)當(dāng)代科技行為主體之間的博弈特質(zhì)。文章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對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公平感知、行為強化、成就期望等角度探討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功能及其發(fā)生機制。
關(guān)鍵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激勵功能
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激勵功能的特質(zhì)
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對個體行為的激勵方式多種多樣,激勵方式的運用往往依據(jù)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特質(zhì)而定:
1.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公平激勵功能
公平、公正是法律的最基本功能,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也不例外,正如博登海默所說:“正義具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當(dāng)我們仔細查看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在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時,我們往往會深感迷惑。”我們從公平理論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美國心理學(xué)家亞當(dāng)斯1967年提出了公平理論,主張每個人不僅應(yīng)該關(guān)心由于自己的工作而得到的報酬的絕對值,而且也有必要關(guān)心自己的報酬與他人報酬之間的關(guān)系。如果以O(shè)p代表一個人對自己報酬的感覺,以Ip代表對自己付出的感覺,以O(shè)o代表對他人報酬的感覺,以Io代表對他人付出的感覺,則公平模式為:Op/Ip=Oo/Io.如果Op/Ip小于Oo/Io,就會認為報酬過低而產(chǎn)生被剝奪感,以至于改變行為,如果Op/Ip大于Oo/Io,也會因報酬過高產(chǎn)生內(nèi)疚感,同樣也會改變行為。
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通過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使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創(chuàng)造者的正當(dāng)權(quán)益不受侵害,也正是由于公平杠桿在起作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公平激勵功能主要體現(xiàn)于公平競爭和分配機制上。分配的公平感知主要指對知識創(chuàng)造勞動質(zhì)和量的價值判斷,在“按勞分配”基礎(chǔ)上達到勞動價值含量的平衡,這體現(xiàn)于科技人員付出與報酬比例的合理程度。也就是說,如果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不能體現(xiàn)公平(尤其分配公平)原則,勢必會大大挫傷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積極性。
2.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強化激勵功能
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法律的懲罰功能被視為最主要的功能,而忽略了法律的規(guī)范和獎勵功能,正如弗里德曼所說“法學(xué)研究總的來說對獎賞注意不多”,“法律制度似乎使用懲罰比獎賞多。從某種意義上說,懲罰似乎更有效”。如《刑法》中的刑罰條文主要體現(xiàn)法律的懲罰、威懾功能,而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由于其特定目的則宜以激勵為主。可以預(yù)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懲罰功能將逐漸削弱以致消退,其功能更多地通過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創(chuàng)造主體的認同、獎賞使其行為得到強化而實現(xiàn)。強化理論是美國心理學(xué)家斯金納提出的,他認為當(dāng)個體行為結(jié)果對自己有利時,這種行為就會重復(fù)出現(xiàn),當(dāng)行為結(jié)果不利時,此行為就會減弱或消失。一般將強化分為正強化和負強化,前者指利用特定的刺激因素,使人的某種行為獲得鞏固和加強,使之再發(fā)生的可能性增大,如表彰、加薪、升職等。負強化則相反。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強化功能主要是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創(chuàng)造主體的有效行為的強化,如我國《科技進步法》關(guān)于自然科學(xué)獎、技術(shù)發(fā)明獎、科學(xué)技術(shù)進步獎和國際科學(xué)技術(shù)合作獎的規(guī)定等,都是為了激勵科技人員的創(chuàng)造行為。當(dāng)然,對那些侵權(quán)者的懲罰也是十分必要的,負激勵與正激勵殊途同歸。
3.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成就激勵功能
成就需要是較高層次的需要,與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需求吻合,科技人員一般受過高等教育,在從事智力勞動過程中,有著強烈的創(chuàng)造欲望而不甘于平庸,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為他們?nèi)〉幂^高成就創(chuàng)造了條件。成就激勵理論是美國心理學(xué)家麥克萊蘭提出來的,他認為在基本需求滿足之后,人的行為取決于權(quán)力、友誼和成就需要的滿足程度,高成就需要的人喜歡挑戰(zhàn)性、風(fēng)險性和高目標(biāo)的工作,希望有所作為。在我國,隨著“科教興國”戰(zhàn)略的實施,對科技創(chuàng)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體系的建立健全為我國科技人員施展才華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激勵功能的發(fā)生機制
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功能的發(fā)生是有條件的,受制于社會環(huán)境、立法制度、司法實踐以及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對應(yīng)的行為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能力和價值判斷等諸多因素。要使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保持一定的創(chuàng)造熱情,就必須建立相應(yīng)的激勵機制。根據(jù)美國心理學(xué)家斯克特的“活化理論”和弗魯姆的期望理論,激勵的目的就是要實現(xiàn)一定的績效預(yù)期,績效大小往往取決于個體的能力和積極性,而積極性又取決于行為動機的強度,動機強度與活化程度有關(guān),活化程度又受激勵水平的影響。即:工作績效=個體能力×積極性,而積極性=F(動機)=F(活化程度)=F(激勵水平)。也就是說,當(dāng)一個人的能力是常量時,其工作成績就取決于所受的激勵程度。
另外,根據(jù)心理學(xué)家勒溫的觀點,人的行為是個體(內(nèi)在心理因素)與環(huán)境(自然、社會)的函數(shù),即人的行為=F(個體×環(huán)境),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激勵發(fā)生的程序:
環(huán)境刺激→被感知的需要→引起動機→驅(qū)動行為→指向目標(biāo)
也就是說,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激勵功能發(fā)生機制是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多個變量交互作用的復(fù)雜過程,首先要考慮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在一個崇尚知識的文明社會環(huán)境中,如果知識和人才得到應(yīng)有的尊重,知識產(chǎn)權(quán)容易得到保護,就會極大地調(diào)動人們的知識創(chuàng)造熱情。另外,社會法律環(huán)境對人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完善的立法制度和成熟的司法體系對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激勵作用不可低估。如果立法不合理,司法不到位,缺乏信度,那么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激勵功能就無法保障。其次要分析知識創(chuàng)造主體的需要。關(guān)于需要,國內(nèi)外都有成熟的理論。馬斯洛強調(diào)了人的需要層次性,赫茲伯格則提出除了外部的刺激外,還存在個體內(nèi)滋激勵因素。據(jù)此,對科技人員的激勵必須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為前提,然后引導(dǎo)、滿足他們的高層次需要,并激發(fā)他們的內(nèi)滋激勵因素。如提高成就感,體驗創(chuàng)造的樂趣等。再次要激發(fā)科技人員的優(yōu)勢動機。知識創(chuàng)造動機的強度是指向目標(biāo)行為發(fā)生的條件,需要的滿足使科技人員的創(chuàng)造動機得以確立。最后要引導(dǎo)優(yōu)勢動機向行為轉(zhuǎn)化,科技人員的創(chuàng)造行為受目標(biāo)效價和期望概率的制約,如果目標(biāo)效價不大就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如果目標(biāo)實現(xiàn)的可能性極小又使人望而卻步,誘發(fā)科技人員的創(chuàng)造行為是激勵機制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當(dāng)然創(chuàng)造行為并不代表創(chuàng)造結(jié)果,能否實現(xiàn)預(yù)期的目標(biāo)是判斷激勵作用的實質(zhì)尺度,這一點不言而喻。
參考文獻:
[1]孫珊珊.淺談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激勵功能[J].職工法律天地:下,2015(11):248.
[2]趙麗敏.論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的激勵機制研究[J].特區(qū)經(jīng)濟,2012(1):25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