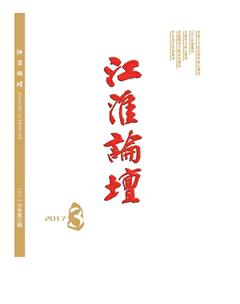文化傳播與地域題材紀(jì)錄片耦合性研究
王莉
摘要:通過(guò)當(dāng)下地域題材紀(jì)錄片熱播的態(tài)勢(shì)分析,結(jié)合文化傳播現(xiàn)狀,從弘揚(yáng)文化、反思文化、塑造形象等方面勾勒其與文化傳播之間的耦合性,并嘗試提出觀點(diǎn),以饗同道,促進(jìn)地域題材紀(jì)錄片在文化傳播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關(guān)鍵詞:文化傳播;地域題材紀(jì)錄片;耦合性
中圖分類號(hào):G206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文章編號(hào):1001-862X(2017)03-0151-004
紀(jì)錄頻道的成功開(kāi)播,優(yōu)秀紀(jì)錄片引發(fā)的熱議,現(xiàn)象級(jí)紀(jì)錄片所帶來(lái)視覺(jué)盛宴及廣泛關(guān)注,使得紀(jì)錄片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呈蓬勃之勢(shì),其中的地域題材紀(jì)錄片也持續(xù)升溫,在展現(xiàn)自然風(fēng)貌的同時(shí),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譽(yù)度、認(rèn)知度和影響力。[1]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紀(jì)錄片傳播文化受幾個(gè)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地域文化紀(jì)錄片在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背景下,對(duì)地域文化進(jìn)行“重塑”和“他塑”;在價(jià)值重構(gòu)的同時(shí),調(diào)節(jié)社會(huì)秩序、保護(hù)民族文化基因,聯(lián)接傳統(tǒng)文化和當(dāng)代社會(huì)。其次,地域題材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們?cè)趯徱曌匀伙L(fēng)貌、地域文化的同時(shí),發(fā)揮著傳播文化的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同時(shí),全新的文化傳播環(huán)境、媒介融合的變革等因素,顛覆了既有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和傳播方式。本文通過(guò)對(duì)多部國(guó)內(nèi)外熱播紀(jì)錄片進(jìn)行梳理和解析及訪談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主創(chuàng)人員,認(rèn)為地域題材紀(jì)錄片應(yīng)從以下五個(gè)文化傳播方面加以強(qiáng)化。
一、弘揚(yáng)文化的創(chuàng)作內(nèi)涵
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使得紀(jì)錄片在弘揚(yáng)文化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不勝枚舉,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在文化戰(zhàn)略的引領(lǐng)下,我國(guó)的文化事業(yè)和文化產(chǎn)業(yè)進(jìn)入了協(xié)調(diào)、快速發(fā)展階段,同時(shí)推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效益和社會(huì)效益的雙提升。紀(jì)錄片人理應(yīng)創(chuàng)新思維,于細(xì)微之處深刻體悟與覺(jué)察當(dāng)下生活現(xiàn)實(shí)、周遭發(fā)展、文化脈動(dòng)、精神風(fēng)貌,記錄一個(gè)個(gè)鮮活的個(gè)體、一次次驟然即逝的歷史瞬間、一場(chǎng)場(chǎng)猝不及防的驚人轉(zhuǎn)變,于宏大敘事中體現(xiàn)細(xì)致入微,從局部真實(shí)中梳理整體認(rèn)知,從現(xiàn)實(shí)中體察出本質(zhì),做到既弘揚(yáng)文化,亦能夠揭示文化內(nèi)涵。
隨著中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的發(fā)展,大量的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入城市,作為承載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場(chǎng)所——農(nóng)村,人口不斷削減,傳統(tǒng)文化亦隨之逐漸消逝。電視紀(jì)錄片作為視覺(jué)媒介的產(chǎn)品,通過(guò)議程設(shè)置,重新建構(gòu)現(xiàn)實(shí)世界。電視紀(jì)錄片《記住鄉(xiāng)愁》展現(xiàn)了200多個(gè)村落,將儒家文化融入鏡頭并貫穿全片始終,通過(guò)紀(jì)實(shí)、記者互動(dòng)等方式,關(guān)聯(lián)了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實(shí)生活。在《城北社區(qū):孝德永彰》這一集中,為了照顧養(yǎng)母,外出打工的李維俊辭職回家這一舉動(dòng),傳達(dá)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傳承了“父母在,不遠(yuǎn)游”優(yōu)良傳統(tǒng)。同時(shí),《記住鄉(xiāng)愁》多次宣揚(yáng)了重歸故土、再建家鄉(xiāng)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頓的精神慰藉,讓人們體會(huì)到回歸傳統(tǒng)村落,既是身體的回歸,也是心靈的回歸,彌合了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文化割裂,喚醒身處飛速發(fā)展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人們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記憶。
紀(jì)錄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國(guó)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記錄了這一文化的起源、興起、發(fā)展的歷史過(guò)程,通過(guò)代表性歷史人物和事件實(shí)現(xiàn)了地域題材紀(jì)錄片文化尋根的重要價(jià)值。紀(jì)錄片《第三極》攝制組經(jīng)過(guò)500多天的長(zhǎng)途跋涉,足跡遍布西藏、青海、四川等60多處秘境,攝取美景的同時(shí),向觀眾展現(xiàn)了當(dāng)?shù)鼐用褡顦銓?shí)、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發(fā)揮紀(jì)錄作品視聽(tīng)語(yǔ)言的優(yōu)勢(shì),促進(jìn)了邊緣文化現(xiàn)象的傳播。紀(jì)錄片《大黃山》摒棄風(fēng)光片的桎梏,從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現(xiàn)具象黃山之美,進(jìn)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載的文化、歷史,蘊(yùn)含的智慧、靈感,深度開(kāi)掘了山地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觀念,發(fā)揮其作為文化載體的顯在優(yōu)勢(shì)。紀(jì)錄片《沙與海》中的牧民劉澤遠(yuǎn),他和后代雖然生活在相對(duì)閉塞的環(huán)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生存理念,這些不同均蘊(yùn)含著濃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們對(duì)于生存與發(fā)展的理念變遷。地域題材紀(jì)錄影像的表達(dá),通過(guò)對(duì)環(huán)境和人物的記錄、重構(gòu),關(guān)照自然環(huán)境的同時(shí),亦聯(lián)接了人物與自然,提煉并傳播了獨(dú)有的地域文化。紀(jì)錄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靜的視角,通過(guò)鄂倫春族最后的薩滿孟金福呈現(xiàn)了其在居住方式變遷過(guò)程中的心路歷程,記錄了大興安嶺地區(qū)即將消亡的文化現(xiàn)象。
二、反思文化的創(chuàng)作“自覺(jué)”
紀(jì)錄片如果僅僅反映現(xiàn)實(shí)圖景、單純地記錄社會(huì)真實(shí),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縱觀一些優(yōu)秀的紀(jì)錄片,“記錄”現(xiàn)象的同時(shí),蘊(yùn)含了思辨和質(zhì)疑的批判精神,引發(fā)觀眾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反思、對(duì)自身行為的反思、對(duì)周遭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反思。費(fèi)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jué)”的理論時(shí)說(shuō)“……要認(rèn)識(shí)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聯(lián)接多種文化,進(jìn)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題材紀(jì)錄片對(duì)于文化的反思,體現(xiàn)了其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自覺(jué)”。
在以往的論著中,關(guān)于紀(jì)錄片中的“文化自覺(jué)”大多停留于“虛構(gòu)”與“紀(jì)實(shí)”表現(xiàn)形式的爭(zhēng)論中,忽視了紀(jì)錄片作為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這種二元對(duì)立的思維模式,固化了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的思維,于其本身所要體現(xiàn)的“文化自覺(jué)”也是相背離的。紀(jì)實(shí)能夠呈現(xiàn)事實(shí),而虛構(gòu)則能將文化內(nèi)涵創(chuàng)作性地蘊(yùn)含于影像之中,凸顯區(qū)域文化與藝術(shù)的張力。其次,在“文化自覺(jué)”的理論框架下,不僅要記錄文化外觀,更要深刻表達(dá)其所依存的文化結(jié)構(gòu);在展現(xiàn)和描繪文化的同時(shí),注重地域文化的時(shí)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維構(gòu)建文化圖景,揭示文化內(nèi)涵。因?yàn)椋挥小白灾保拍堋白杂X(jué)”。紀(jì)錄片《紐帶》運(yùn)用歷史場(chǎng)景再現(xiàn)的方式,協(xié)調(diào)兼顧海外漢學(xué)者的性質(zhì)和趣味、中國(guó)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受眾對(duì)歷史紀(jì)錄片的審美期待等多種因素,是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高度文化自覺(jué)的產(chǎn)物。
紀(jì)錄影片《消失的村莊》中呂氏父子所居的村莊,正如中國(guó)若干的偏遠(yuǎn)村莊一樣,成為老人與兒童的留守地,而作為社會(huì)中堅(jiān)力量的青年男女則隨著經(jīng)濟(jì)大潮奔向城市;而遷徙令的頒布,后代對(duì)城市的認(rèn)同和向往,使村落從物質(zhì)和思想層面不斷衰敗直至瓦解。地域題材紀(jì)錄片以真實(shí)的事件,微觀的人的視角,講述了地域因政治、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文化、思想的變遷,通過(guò)深入記錄和旁觀審視,更有利于觀眾透過(guò)鏡頭反思發(fā)展著的中國(guó)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創(chuàng)作使命
“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推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和整個(gè)世界高度相聯(lián)。地域題材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不但展現(xiàn)人文風(fēng)貌、地域特點(diǎn),更應(yīng)該深刻刻畫(huà)人與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與觀念變遷,塑造區(qū)域文化圖景,探索經(jīng)濟(jì)發(fā)展機(jī)遇。英籍社會(huì)學(xué)家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代文化展示已經(jīng)從嚴(yán)肅的官方描繪轉(zhuǎn)向民間。”[3]而紀(jì)錄片也不僅是顧茲曼眼中的“相冊(cè)”,更是一張文化名片,一張避免被誤讀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麗中國(guó)》被譽(yù)為一張遞給世界的“中國(guó)名片”。如果說(shuō)《美麗中國(guó)》是一張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國(guó)》則是一張中國(guó)自己遞向國(guó)際的“飲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滲透于中國(guó)人生活各個(gè)層面的美食為中心,折射了與美食相關(guān)的人和事,蘊(yùn)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這樣的“名片”越來(lái)越多,才能更為客觀、理性、多角度地展現(xiàn)出豐富立體的中國(guó)。
其次,通過(guò)紀(jì)錄片塑造地域乃至國(guó)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體在國(guó)際社會(huì)相對(duì)強(qiáng)勢(shì)地位,因此對(duì)‘中國(guó)崛起的形象建構(gòu)是其塑造中國(guó)國(guó)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國(guó)媒體在中國(guó)國(guó)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給了西方媒體更多的機(jī)會(huì)。《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jì)錄片對(duì)“中國(guó)崛起”的形象建構(gòu)》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發(fā)達(dá)英語(yǔ)國(guó)家的主流媒體及知名的播出機(jī)構(gòu)的紀(jì)錄片對(duì)中國(guó)國(guó)家形象的建構(gòu),分析了他者視角下“中國(guó)崛起論”、“中國(guó)威脅論”等觀點(diǎn)的建構(gòu)。撇開(kāi)觀察視角、內(nèi)容本身的局限,單從諸如《中國(guó)人要來(lái)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國(guó)人如何蒙騙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聳聽(tīng)的片名中,我們解讀到西方主流媒體并未能呈現(xiàn)真實(shí)中國(guó),展示中國(guó)國(guó)家文化所蘊(yùn)含的應(yīng)有之義。因此,紀(jì)錄片應(yīng)發(fā)揮其題材內(nèi)容真實(shí)、在國(guó)際傳播中的傳播力較強(qiáng)的優(yōu)勢(shì),勇于擔(dān)當(dāng)講述中國(guó)國(guó)家故事、傳播中國(guó)文化內(nèi)涵、樹(shù)立中國(guó)國(guó)家形象的重任。
發(fā)展中的國(guó)家、變化中的國(guó)際環(huán)境,令我們能夠客觀審慎地記錄、呈現(xiàn)、審視乃至傳播我們的文化。進(jìn)入全球化時(shí)代,國(guó)家之間文化的對(duì)話需要更多的平臺(tái)消除彼此間的誤解,達(dá)到互通有無(wú)的目的。具體而言,紀(jì)錄片應(yīng)主動(dòng)向世界展示真實(shí)的中國(guó),在主題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等因素及傳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風(fēng)格,成為傳播中國(guó)文化的有力載體。
同時(shí),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在講述中國(guó)故事、塑造中國(guó)的國(guó)家形象的過(guò)程中,在尊重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則的同時(shí),還需要把握紀(jì)錄片傳播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體系,做好充分的市場(chǎng)調(diào)研,遵循紀(jì)錄片市場(chǎng)規(guī)律,在技術(shù)層面滿足國(guó)際市場(chǎng)標(biāo)準(zhǔn),在內(nèi)容層面繼續(xù)深耕與打磨創(chuàng)作者的講故事水平。西方國(guó)家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理念與市場(chǎng)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戲劇性、邏輯性強(qiáng),兼具娛樂(lè)化的同時(shí),給受眾以很強(qiáng)的代入感,這些創(chuàng)作規(guī)律需要中國(guó)紀(jì)錄片人在不斷的交流和學(xué)習(xí)中吸納和創(chuàng)造性地運(yùn)用。近年來(lái)不可多得的“他者”視角的紀(jì)錄片作品《超級(jí)中國(guó)》在尊重跨文化傳播規(guī)律之下,能夠以懸念的方式揭曉并解讀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政治發(fā)展的多重原因,堪稱跨文化傳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講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實(shí)現(xiàn)有效傳播,國(guó)家的形象在有效傳播中得以塑造。
四、構(gòu)建軟實(shí)力的路徑選擇
尹鴻教授認(rèn)為“提升中國(guó)影視文化軟實(shí)力,需要注重價(jià)值觀的輸出” [5]紀(jì)錄片《西藏的誘惑》在當(dāng)時(shí)被譽(yù)于“散文詩(shī)式”的紀(jì)錄片佳作,但在今天看來(lái),夸張的抒情、空洞的解說(shuō)不僅難以吸引受眾,更難以表達(dá)西藏文化之精髓。對(duì)于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而言,攝像機(jī)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僅記錄文化、表達(dá)文化,同時(shí)也闡釋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環(huán)境不斷發(fā)展的今天,中國(guó)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與傳播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已成功打開(kāi)局面,要作為國(guó)家“軟實(shí)力”一個(gè)窗口,還需要把握當(dāng)前時(shí)機(jī),加強(qiáng)與海外機(jī)構(gòu)的合作,持續(xù)不斷輸出精品。構(gòu)建“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shí)施,也為我國(guó)資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但是,中國(guó)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在紀(jì)錄片傳播過(guò)程中,將獲取影展資格及經(jīng)濟(jì)利益作為主要傳播目的進(jìn)而迎合西方國(guó)家視點(diǎn),將會(huì)失去紀(jì)錄的品格,遑論“軟實(shí)力”構(gòu)建。
約瑟夫·奈認(rèn)為,“軟實(shí)力是一個(gè)國(guó)家的文化與意識(shí)形態(tài)吸引它通過(guò)吸引力而非強(qiáng)制力獲得理想的結(jié)果,它能夠讓其他人信服地跟隨你或讓他們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設(shè)想行事。”[6]《望長(zhǎng)城》堪稱當(dāng)時(shí)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國(guó)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卻習(xí)慣于拋棄受眾意識(shí),以一種無(wú)可辯駁的“宏大”姿態(tài),難以以受眾、市場(chǎng)接受的創(chuàng)作思維構(gòu)建文化軟實(shí)力。除了技術(shù)的發(fā)展,《望長(zhǎng)城》是創(chuàng)作思維的煥新。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在中日合作中,大膽摒棄觀念的窠臼,將《東方老墻》文本、“畫(huà)面加解說(shuō)”的桎梏拋出“長(zhǎng)城之外”,將直觀感性的語(yǔ)言融入恰當(dāng)?shù)奈幕瘋鞑ィ胺Q彼時(shí)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一股清流。紀(jì)錄片通過(guò)視聽(tīng)語(yǔ)言吸引受眾,激發(fā)其感性想象與理性思考,較之博物館式的展示,生動(dòng)而直抵人心,傳播面更廣、效果顯著。然而,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應(yīng)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從感性到理性,是認(rèn)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眾更樂(lè)于在視聽(tīng)愉悅、情感共鳴之后,于“潤(rùn)物細(xì)無(wú)聲”之中接受或領(lǐng)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實(shí)現(xiàn)意識(shí)的感召作用。一個(gè)民族對(duì)其所處環(huán)境及文化的認(rèn)同與共識(shí),形成了這個(gè)民族所共通的記憶和歷史,借助文化的紐帶構(gòu)建文化軟實(shí)力。可見(jiàn),不同時(shí)期的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應(yīng)借助技術(shù)手段和藝術(shù)觀念的發(fā)展,協(xié)同文化的創(chuàng)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構(gòu)建文化中蘊(yùn)含的軟實(shí)力。
五、創(chuàng)新格局下的思維革命
如果說(shuō)技術(shù)和觀念的發(fā)展使紀(jì)錄片從“小眾”走向“大眾”,那么互聯(lián)網(wǎng)的快速發(fā)展,更是以“顛覆”性的飛躍,重構(gòu)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體的時(shí)代,“傳者”與“受者”的概念幾近模糊;“草根媒體”平臺(tái)的涌現(xiàn),豐富了資源,降低了門檻;利益的裹挾、唯“用戶眼球”商業(yè)格局,使得文化傳播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思維框架之下,專業(yè)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終將不保。全新的媒體環(huán)境、多變的智能設(shè)備、新興的媒介組織,用戶主體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信息化進(jìn)程飛速發(fā)展,對(duì)于地域文化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與傳播者而言,既是機(jī)遇也是考驗(yàn)。傳播迅速、便捷、互動(dòng)性強(qiáng)的優(yōu)勢(shì)乃傳統(tǒng)媒體無(wú)法超越,然而浮躁的傳播環(huán)境之下,更加需要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能夠以審慎的態(tài)度書(shū)寫(xiě)文化,以專業(yè)的精神傳播文化。紀(jì)錄片《大秦嶺》通過(guò)逼真的景像還原展示了秦嶺文化,并以專業(yè)的視角解讀地域文化,取得了顯著效果。誠(chéng)然,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終極目標(biāo)。因此,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應(yīng)充分發(fā)揮紀(jì)錄影像的具象連貫、生動(dòng)完整等方面的優(yōu)勢(shì),從對(duì)地域人文地理風(fēng)貌的展示中傳播地域文化,建構(gòu)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學(xué)者劉潔在《活態(tài):紀(jì)錄片中傳統(tǒng)文化的存續(xù)》文章中認(rèn)為:“……傳統(tǒng)文化也是活態(tài)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剝離物。……‘活態(tài)已成為我們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認(rèn)知。”[7]基于“活態(tài)傳承”的視野,在地域題材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中,不應(yīng)止于描述和記錄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關(guān)照歷史與當(dāng)下、人與周圍的環(huán)境同時(shí),創(chuàng)新思維,以媒體人應(yīng)有的專業(yè)策略,重構(gòu)我們的認(rèn)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價(jià)值、獨(dú)創(chuàng)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邏輯、理想、世界觀和道德觀,我們對(duì)文化的理解,應(yīng)該聯(lián)系其所處的時(shí)間和空間,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者也應(yīng)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認(rèn)識(shí)文化的多樣性及合理性。對(duì)于地域文化的敘述,是在國(guó)家歷史的框架中展開(kāi)的,其選題的范圍、創(chuàng)作的視野不應(yīng)受地域的影響,以一種全局思維,無(wú)論在理論研究框架還是在實(shí)踐創(chuàng)作模式上,耦合當(dāng)下文化,發(fā)揮紀(jì)錄片這一片種的優(yōu)勢(shì),促使我國(guó)地域題材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達(dá)到更為理想的境地。
參考文獻(xiàn):
[1]閆偉娜.紀(jì)錄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藝術(shù)研究,2013,(4):32—37.
[2]費(fèi)孝通.費(fèi)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jué)[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馮悅,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曉培.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jì)錄片對(duì)“中國(guó)崛起”的形象建構(gòu)[J].現(xiàn)代傳播,2015,(4):102—106
[5]張國(guó)濤,張陸園,楊賓.中國(guó)影視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理念與路徑——中國(guó)高校影視學(xué)會(huì)第十五屆年會(huì)暨第八屆中國(guó)影視高層論壇綜述[J].現(xiàn)代傳播,2014,(12):136—137.
[6]Joseph,S.& Nye,Jr.Soft Powe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N].Time,1999-02-22.
[7]劉潔.活態(tài):紀(jì)錄片中傳統(tǒng)文化的存續(xù)[J].中國(guó)電視.2014,(8):16-19.
(責(zé)任編輯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