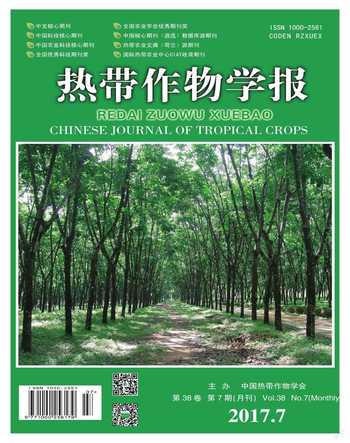秀珍菇遺傳育種研究進展
陳躬國 林原 劉新銳 趙光輝 陳劍
摘 要 秀珍菇是近年來的菌中新貴。從秀珍菇遺傳特性、種質資源研究以及雜交育種、原生質體融合育種、自交育種、輻射誘變育種等綜述了秀珍菇遺傳育種的現狀及進展。開展秀珍菇種質資源收集,進行優異種質資源的創新評價和利用研究,對秀珍菇種質資源的保護,合理開發利用秀珍菇種質資源,促進秀珍菇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秀珍菇;種質資源;遺傳特性;育種;進展
中圖分類號 S646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Pleurotus pulmonarius is an upstart edible mushroom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gress in the genetic breeding of P. pulmonarius from perspectives of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germplasm resources research, hybridization breeding, protoplast fusion breeding, inbred breeding and radiation-induced mutation breeding. To conduct the collec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of P. pulmonarious and performing creative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of P. pulmonarius germpla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P. pulmonarius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 pulmonarius industry.
Key words Pleurotus pulmonarius; germplasm resource; genetic characteristic; breeding; progress
doi 10.3969/j.issn.1000-2561.2017.07.031
秀珍菇,學名為肺形側耳(Pleurotus pulmonarius),隸屬擔子菌綱(Basidiomycetes),傘菌目(Agaricales),側耳科(Pleurotaceae),側耳屬(Pleurotus)。秀珍菇的名稱來源于中國臺灣,20世紀90年代,首先被臺灣農試所開發并商業栽培,1998年首次由臺灣人在福州市羅源縣引種栽培獲得成功,之后迅速得到大面積推廣[1]。在較長一段時間以內,秀珍菇的分類地位并不十分明確,其名稱與學名用法也較為混亂,最早國內文獻上使用的拉丁文學名多為Pleurotus geesteranus(環柄側耳)[2-3],也有Pleurotus ostreatus(糙皮側耳)[4]、Pleurotus cornucopiae(黃白側耳)[5]等。張金霞等[6]通過生物學特性和形態特征鑒定,并應用酯酶同功酶[7]、RAPD[8]等分析秀珍菇遺傳特點及DNA差異,將其歸屬于肺形側耳,認為秀珍菇與鳳尾菇是同種內的不同品種。朱堅等[9]也通過ITS-RFLP、ITS序列分析和交配親和性研究,認為秀珍菇在分類學上屬于肺形側耳。
1 秀珍菇的特性與遺傳研究
秀珍菇屬于雙因子控制的四極性異宗配合擔子菌,其性親和由兩對獨立分離的遺傳因子A與B控制,只有當A因子與B因子都不相同的單核菌株才能發生親和反應,產生具有鎖狀聯合的雙核菌絲體,才有可能完成有性生活史。一般認為A因子控制細胞核的配對和鎖狀聯合的形成,B因子控制細胞核的遷移和鎖狀聯合的融合[10-11]。秀珍菇的遺傳因子A與B均存在復等位基因現象。張黎杰[12]通過對30株秀珍菇菌株進行交配型分析只發現了4個A因子和3個B因子,認為秀珍菇的交配型因子并不具有多樣性的特點,秀珍菇菌株的種質資源較為匱乏。脈沖場凝膠電泳(PFGE)是用于分離20 kb到10 Mb之間的大分子DNA片段的一種電泳技術,已廣泛應用于真菌的核型分析和核型多態性研究,為真菌細胞學和分子遺傳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13]。Sagawa等[14]通過脈沖場凝膠電泳相關技術對肺形側耳進行染色體的核型分析表明,P. pulmonarius有6條分子大小從4.9 Mb到1.6 Mb的DNA條帶,而P. ostreatus有11條分子大小從5.2 Mb到2.1 Mb的DNA條帶,P. cornucopiae有7條分子大小在4.6 Mb到1.8 Mb的DNA條帶,分析結果對秀珍菇在細胞學水平上的特異性鑒定及遺傳分析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分子遺傳學研究方面,近年也取得明顯進展。遺傳圖譜的構建是當前分子遺傳學研究的熱點,高密度的遺傳圖譜能有效地用于控制農藝性狀基因的定位,提高育種效率。Okuda等[15]以150個P. pulmonarius單孢雜交群體,應用300個AFLP標記結合兩個交配型因子和無孢性狀等,構建了包含12個連鎖群的P. pulmonarius遺傳圖譜,圖譜覆蓋總長度為971 cM,標記間平均距離為5.2 cM。
2 秀珍菇遺傳育種進展
2.1 秀珍菇的種質資源研究
秀珍菇種質資源是秀珍菇育種的重要基礎材料,研究和評價秀珍菇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可為發掘優異種質資源和雜交親本遺傳背景的合理選配提供依據。目前,除形態學鑒定、拮抗反應、同工酶等,已見SRAP、RAPD、ITS-RFLP、ERIC-PCR、ISSR和SNP等分子標記應用于秀珍菇種質資源的遺傳多樣性和親緣關系分析。
朱堅等[16]通過對34個秀珍菇菌株的SRAP、RAPD和ISSR綜合分析,發現大部分菌株DNA的相異系數都在0.19以下,部分菌株相異系數等于或接近于0,菌株號卻不同,而有的菌株號相同,但相異系數卻較大,研究結果表明這些秀珍菇菌株遺傳差異小,并且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的混亂現象在秀珍菇上也存在。盧政輝[17]利用SRAP分子標記技術對不同地區的22個秀珍菇及其近緣菌株的進行了DNA指紋圖譜的擴增,獲得了9條SRAP標記條帶,為這些菌株的鑒定、鑒別以及區分秀珍菇和近緣種提供依據。馮偉林等[18]通過原基形成時間、轉潮時間、出菇溫度和產量等方面進行了農藝性狀比較,并與ISSR分子標記結合進行分析,在菌株相似性系數0.87時,將15個秀珍菇菌株聚為3個群,并初步發現秀珍菇不同出菇溫型與ISSR分子標記分類有較高的相關性。李維煥等[19]采用ERIC-PCR技術進行秀珍菇菌株的親緣關系和遺傳多樣性分析,將12個菌株在相似性系數為0.79水平上分為4組,結果與拮抗實驗和同工酶分析基本一致。聚類分析結果表明,來自同一地區的供試秀珍菇菌株聚為一類,也有少數菌株和其他地區菌株聚在一起,這與忻雅等[20]用EST-SSR和RAPD分析秀珍菇菌株進行親緣關系的結果一致。這可能與目前我國各地相互引種、菌種管理混亂等有關。沈蘭霞[21]對8個肺形側耳菌株的2個功能基因共1 013 bp序列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含有的SNP總共162個,對平均不到7個堿基就有1個SNP存在;進一步進行SNP篩選發現,僅需功能基因ste3-like(交配型因子信息素受體)片段上的16個SNP位點即可將8個肺形側耳菌株完全區分開來,具有較高的分辨率,表明SNP可以用于肺形側耳菌株的鑒定工作。
2.2 系統選育
系統選育又稱為選擇育種、自然選育,就是用人工方法定向選擇自然條件下發生的有益變異,進而獲得具有更高應用價值的新品種。系統選育是食用菌中應用最早的品種改良方法,也是最簡單、應用廣泛的選種方法[22]。美國(1950)的奶白、棕色和白色等雙孢蘑菇菌株和香菇優良品種‘7401、‘廣香5號及‘L241等均是通過系統選育篩選得到的[23-24]。系統選育也是秀珍菇常規育種的重要手段之一。上海農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從印度秀珍菇中系統選育出‘秀珍菇5號,杭州市農業科學研究院通過‘秀珍18菌株變異株系統選育出‘杭秀1號。黃良水等[25]以常山縣規模栽培的秀珍菇為育種親本,采用連續組織分離方法,通過拮抗試驗、生物學特性和栽培特性等研究,系統選育出優質高產秀珍菇新菌株‘青秀2號,其在15~35 ℃環境中子實體正常生長,較耐高溫,比原菌株增產6.3%,而且性狀表現穩定。
2.3 雜交育種
雜交育種著眼于雙親性狀的優勢互補,使雜種后代增加變異性,產生雙親優良性狀的組合,甚至是超親代的優良性狀。對于食用菌來說,雜交育種是近些年在新品種選育中使用最廣且卓有成效的一種育種途徑[26],并開展了許多如分子標記、QTL定位[27-28]等相關的基礎研究。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雜交育種培育出雙孢蘑菇、香菇、金針菇等食用菌新品種并陸續投入生產,使我國迅速發展為食用菌生產大國[29]。
雜交育種中能否獲得高產優質的優良菌株,關鍵是具有不同優良性狀雜交親本的合理選配和雜交組合的選擇。Avin等[30]在秀珍菇的雜交育種中首次引入配合力、遺傳力等概念,以3個菌株的22個單核孢子為親本采用Griffing雙列雜交方法Ⅱ進行雜交交配設計,對原基期、產量等12個目標性狀的配合力和雜種優勢進行分析,同時估計遺傳方差分量、遺傳力等遺傳參數,并通過形態學特征和PCR-RFLP鑒定雜交子。李碧瓊等[31]對秀珍菇雜交親本的菌絲生長狀況、生育期、子實體產量和生物學性狀等進行比較,選擇在產量性狀和質量性狀具有優勢互補的菌株作為親本。在秀珍菇雜交育種中,單孢雜交是應用廣泛的育種手段。周莉[32]通過單孢雜交結合RAPD分子標記技術篩選出產量高、抗病性好的優良秀珍菇雜交菌株。浙江省農科院園藝所應用單孢雜交等技術育成首個秀珍菇抗黃枯病新品種‘農秀1號,試驗推廣中表現出商品性狀好、產量高等特性。
2.4 原生質體融合育種
原生質體融合是指通過人工方法,使去除細胞壁后兩個不同遺傳性狀的親本原生質體,在融合劑或其他方法誘導下進行融合,基因部分或全部重組,從而獲得兼有雙親遺傳性狀的穩定融合子的過程[22]。原生質體融合育種有助于克服種屬間雜交的不育性,使遠緣雜交成為可能。原生質體融合育種在國內外有許多獲得成功的報道,目前已從雙孢蘑菇、草菇等幾十種食用菌中制備出原生質體[33],而且種間、屬間甚至目間的食用菌原生質體融合也取得相當大的成功,尤其是PEG融合法在食用菌原生質體融合中有許多成功的應用[34-35]。秀珍菇原生質體的制備與再生是原生質體融合育種的基礎,有關研究探討了溶壁酶、穩滲劑和酶解條件等因素對原生質體形成的影響。于清偉[36]研究秀珍菇菌絲原生質體分離與再生結果表明以0.6 mol/L甘露醇為穩滲劑,在30 ℃、pH6.0、1.5%溶壁酶+0.5%蝸牛酶條件下對培養5 d的秀珍菇菌絲體酶解3.0 h,原生質體產量達到1.86×108個/mL,這與萬南安[37]在對影響秀珍菇原生質體分離與再生的因素研究結果相近。刺芹側耳和秀珍菇同為側耳屬的2個種,不能進行常規手段種間雜交育種[38]。張鵬等[39]以刺芹側耳雙核菌株和秀珍菇單孢菌株為親本,分別制備原生質體,用PEG法進行原生質體融合,通過鎖狀聯合和拮抗試驗得到一株融合子R1,經RAPD、ISSR分子標記證明融合子含有雙親遺傳物質,為真正的融合子。Fukuda等[40]報道了通過原生質體電融合技術將糙皮側耳(甲硫氨酸營養缺陷型和氯霉素抗性株)線粒體DNA成功地導入秀珍菇(野生型)細胞中。與秀珍菇同屬肺形側耳的鳳尾菇與其他食用菌科間甚至目間融合研究亦有文獻報道。肖在勤等[41]用鳳尾菇和金針菇為親本進行原生質體融合研究,獲得了金針菇和鳳尾菇不同科間的核配融合子菌株;王澄澈等[42]對鳳尾菇和香菇原生質體非對稱融合進行了探索研究,篩選出的融合子菌株比供體親本‘L38生長快、出菇早、產量高。
2.5 自交選育
自交在植物育種上的應用較為廣泛,在食用菌遺傳研究與育種工作中,自交的運用則少見報道。自交的遺傳學意義是使雜合基因在經過連續多代自交后分離和純合,形成具有不同性狀的各種株系,并使隱性形狀得以表現,有助于淘汰那些具有不良隱性基因的個體[43]。自交后代整體上相對親本表現出劣勢,但是仍有少數菌株一些性狀表現出超親優勢[44-45],這些超親菌株可根據育種目標為選育更優良株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張俊玲等[46]以秀珍菇‘3108為出發菌株進行多孢自交,發現其自交子代群體出現自交衰退和超親優勢現象。通過對子代群體各性狀的綜合分析,從中選育出生長快、產量高、菇蓋厚且不易碎、柄粗長、抗雜和抗逆性強、栽培周期短等優良性狀的秀珍菇新菌株‘申秀1號,其產量比出發菌株增產7.1%,且種性穩定。ISSR鑒定結果顯示,‘申秀1號菌株與出發菌株有遺傳差異,具有特異性。福建省農科院食用菌研究所通過‘秀57自交選育而成‘秀迪1號,通過多年多點試種其產量表現比出發菌株‘秀57增產8.5%。
2.6 輻射誘變育種
誘變育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某些物理或化學因素使食用菌遺傳基因發生突變,引起遺傳性狀發生變異,從中篩選出符合育種目標優良性狀突變株的育種方法[22]。常用的物理誘變劑包括紫外線、X射線、γ射線(如60Co等)、離子束和激光等;化學誘變劑主要是脫氨基誘變劑、烷化劑、堿基類似物、移碼誘變劑等,它們的誘變機理均為引起基因突變[22]。目前,以菌絲體、孢子和原生質體為誘變材料,通過紫外線、γ射線等輻射后,食用菌生理生化和遺傳特性發生變化及新品種選育研究的報道較多。Adebayo等[47-48]通過紫外輻射誘變的方法篩選出誘變菌株LAU90,其菌絲生長量、干物質重量、子實體產量以及漆酶活性均高于出發菌株LAU09。魯東大學菌物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將‘秀珍菇18(GY18)孢子經紫外線輻射誘變,通過菌絲生長速度、形態特征以及產量等方面的比較分析,篩選出中高溫品種‘秀珍菇LD-1(魯農審2009084),其產量較當地主栽品種增產明顯。梁昌柱[49]利用不同劑量的低能N+離子束注入秀珍菇菌絲體,進行誘變處理,篩選出的誘變菌株產量較出發菌株增產顯著,通過對粗脂肪、粗蛋白、粗纖維以及總糖的測定和分析表明,誘變菌株子實體擁有較高的總糖和粗脂肪,同時具有較高的蛋白質含量。翁伯琦、江枝和等[50-51]首次將60Co-γ射線輻射應用于秀珍菇新菌株的選育,用不同劑量60Co-γ射線輻射秀珍菇菌絲,評價分析輻射新株系的子實體蛋白質營養價值和各類氨基酸含量,選育秀珍菇輻射新品種。
2.7 基因工程育種
基因工程育種是指不經過有性過程,將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基因通過生物、物理和化學等方法導入到受體細胞中進行復制和表達,從而選育出新品種的生物技術。它為那些常規育種手段受到限制的食用菌種類育種開創了新的途徑,但還未見食用菌轉基因菌株用于商業生產[52]。目前,食用菌相關基因的分離與克隆已取得了許多進展,如雙孢蘑菇褐變相關基因[53]、糙皮側耳的漆酶基因[54]和香菇的子實體發育相關基因[55-56]等。秀珍菇是變溫結實性的菌類,溫度是影響秀珍菇生長發育的重要因素。周爍紅等[57]通過TAIL-PCR技術克隆了秀珍菇在變溫結實過程中上調表達的基因Ppcsl-1,熒光定量檢測結果顯示該基因在菌絲經過5 ℃、12 h冷處理之后的表達量最高,表明其有可能被冷刺激誘導表達并在開啟子實體形成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側耳屬的無孢或少孢菌株的相關基因研究也是近來的研究熱點之一[58]。2013年OKUDA等[59-60]通過BSA-AFLP技術從無孢子突變株中克隆獲得P. pulmonarius孢子形成的關鍵基因stpp1。對P. pulmonarius單核菌絲重組敲除stpp1基因后,與無孢子突變株單核菌絲相配合形成突變雙核菌絲,發現子實體減數分裂在減I前期受到抑制,不能正常形成大量孢子,產孢子量下降為0.01%,表明該基因對于維持其遺傳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3 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相對于其他食用菌,秀珍菇在我國的馴化栽培歷史并不長,由于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前景,秀珍菇產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從目前秀珍菇育種的現狀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同名異種或同種異名現象比較嚴重,造成菌種混亂;品種選育研究工作開展仍較為薄弱,遺傳育種基礎研究相對不夠深入;現有主栽品種多從臺灣地區引進看,有的品種在引進多年后出現退化,抗病能力差等。
針對現有秀珍菇栽培品種管理混亂甚至生產上出現用其他平菇當秀珍菇栽培等現象,可通過單核苷酸多態性(SNP)技術等檢測方法進行秀珍菇品種DNA身份鑒定,排除非秀珍菇的近緣菌株,并進行親緣關系分析;對秀珍菇種質資源進行綜合評價分析,發掘優異種質資源,為種質創新提供育種材料。隨著分子育種技術的蓬勃發展,SNP等新興的分子標記技術將被廣泛用于秀珍菇種質資源遺傳多樣性分析、雜交子或融合子鑒定、遺傳圖譜構建與基因定位等方面,相信會給秀珍菇遺傳育種研究帶來巨大進步。
參考文獻
[1] 阮海東, 陳秀娟, 林戎斌. 秀珍菇對生育條件的要求及其栽培技術[J]. 福建農業科技, 2005(6): 24-26.
[2] 翁伯琦, 江枝和, 林 勇. 不同培養料對秀珍菇子實體蛋白質營養評價的影響[J]. 食用菌學報, 2002, 9(2): 10-13.
[3] 馮志勇, 王志強, 郭力剛, 等. 秀珍菇生物學特性研究[J]. 食用菌學報, 2003, 10(3): 11-16.
[4] 覃寶山, 覃勇榮, 劉 倩, 等. 板栗苞殼栽培的平菇和秀珍菇主要營養成分分析[J]. 貴州農業科學, 2009, 37(12): 81-83.
[5] 陳君琛, 沈恒勝, 湯葆莎, 等. 秀珍菇反季節高效栽培技術研究[J]. 中國食用菌, 2003, 22(4): 21-23.
[6] 張金霞, 黃晨陽, 鄭素月. 平菇新品種——秀珍菇的特征特性[J]. 中國食用菌, 2005, 24(4): 26-26.
[7] 鄭素月, 張金霞, 黃晨陽. 中國栽培平菇的酯酶同工酶分析[J]. 食用菌學報, 2003, 10(4): 1-6.
[8] 鄭素月, 黃晨陽, 張金霞. 中國栽培平菇的RAPD分析[J]. 山東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 36(2): 186-190.
[9] 朱 堅, 劉新銳, 謝寶貴,等. 秀珍菇種質資源的ITS-RFLP分析[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9, 38(2): 186-191.
[10] Papazian H P. The incompatibility factors and a related gene in Schizophyllum commune[J]. Genetics, 1951, 36(36): 441-459.
[11] 李莉云, 劉國振, 劉麗娟. 擔子菌交配型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研究進展[J]. 中國生物工程雜志, 1999, 19(1): 19-24.
[12] 張黎杰. 秀珍菇等四種側耳屬食用菌的交配型分析及其基因克隆[D]. 福州: 福建農林大學, 2009.
[13] 邊銀丙, 羅信昌. 脈沖電泳技術及其在食用菌研究中的應用[J]. 食用菌學報, 1996, 3(2): 45-50.
[14] Sagawa I, Nagata Y. Analysis of chromosomal DNA of mushrooms in genus Pleurotus by 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J]. Journal of General & Applied Microbiology, 1992, 38(1): 47-52.
[15] Okuda Y, Murakami S, Matsumoto T. A genetic linkage map of Pleurotus pulmonarius based on AFLP markers,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gene region for the sporeless mutation[J]. Genome, 2009, 52(5): 438-446.
[16] 朱 堅, 盧啟泉, 謝寶貴. 秀珍菇種質資源分子多態性研究[J]. 菌物學報, 2007, 26(增刊): 226-231.
[17] 盧政輝. 秀珍菇及其近緣22株菌株的SRAP分析[J]. 江西農業學報, 2008, 20(11): 8-10.
[18] 馮偉林, 蔡為明, 金群力,等. 秀珍菇菌株主要農藝性狀比較及ISSR分子標記鑒定[J]. 食用菌學報, 2014(2): 14-18.
[19] 李維煥, 蔡德華, 鄭 芳, 等. 秀珍菇菌株的親緣關系分析[J]. 食品科學, 2010, 31(17): 267-271.
[20] 忻 雅, 王偉科, 阮松林, 等. 基于RAPD和EST-SSR標記的秀珍菇菌株聚類分析[J]. 食用菌學報, 2008, 15(4): 20-25.
[21] 沈蘭霞. SNP在平菇菌株鑒別中應用研究[D]. 福州:福建農林
大學, 2013.
[22] 張金霞. 中國食用菌菌種學[M].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11.
[23] 李 琳, 周國英, 劉君昂,等. 雙孢蘑菇遺傳育種研究進展[J]. 食用菌學報, 2007, 14(1): 62-66.
[24] 吳學謙. 香菇生產全書[M]. 北京: 農業出版社, 2012.
[25] 黃良水, 徐立勝, 洪金良,等. 秀珍菇新菌株青秀2號的選育與應用[J]. 中國食用菌, 2011, 30(2): 20-21.
[26] Fan L, Pan H, Soccol A T, et al. Advances in mushroom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J]. Food Technology & Biotechnology, 2006, 44(3): 303-311.
[27] 邊銀丙, 劉 偉, 肖 揚, 等. 大型真菌遺傳連鎖圖譜研究與香菇分子遺傳圖譜構建[C]. 中國菌物學會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學術年會論文摘要集, 2011.
[28] Sonnenberg A S M, Baars J J P, Hendrickx P M, et al. Breeding mushroom: state of the art[J]. Acta Edulis Fungi, 2005, 12(Suppl): 163-173.
[29] 付立忠, 吳學謙, 魏海龍,等. 我國食用菌育種技術應用研究現狀與展望[J]. 食用菌學報, 2005, 12(3): 63-68.
[30] Avin F A, Bhassu S, Rameeh V, et al. Genetics and hybrid breeding of Pleurotus pulmonarius: heterosis, heritability and combining ability[J]. Euphytica, 2016, 209(1): 85-102.
[31] 李碧瓊, 陳政明, 林俊揚, 等. 秀珍菇雜交親本篩選試驗[J]. 中國食用菌, 2015, 34(4): 16-20.
[32] 周 莉. 平菇單孢雜交及其抗病新菌株選育[D]. 南寧: 廣西大學, 2014.
[33] 李守勉, 李 明, 邢 蕾, 等. 食用菌原生質體技術應用的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 2007, 35(25): 7 770-7 771.
[34] Eyini M, Rajkumar K, Balaji P. Isolation, regeneration and PEG-induced fusion of protoplasts of Pleurotus pulmonarius and Pleurotus florida[J]. Mycobiology, 2006, 34(34): 73-78.
[35] Chakraborty U, Sikdar S R. Prod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matic hybrids raised through protoplast fusion between edible mushroom strains Volvariella volvacea, and Pleurotus florida[J]. Worl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08, 24(8): 1 481-1 492.
[36] 于清偉. 秀珍菇原生質體制備研究[J]. 食用菌, 2016, 38(2): 18-19.
[37] 萬南安. 秀珍菇原生質體的分離與再生的研究[J]. 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 21(5): 69-70.
[38] 劉盛榮. 杏鮑菇的遺傳特性及種間雜交研究[D]. 福州: 福建農林大學, 2008.
[39] 張 鵬, 龔玲鳳, 朱 堅,等. 刺芹側耳與秀珍菇細胞融合及融合子的鑒定[J]. 食用菌學報, 2013, 20(3): 1-5.
[40] Masaki F, Masayoshi W, Masayuki U, et al. Introduc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from Pleurotus ostreatus into Pleurotus pulmonarius by interspecific protoplast fusion[J]. Journal of Wood Science, 2007, 53(4): 339-343.
[41] Adegoke A E, Kola O J, Yadav A, et al. Improvement of laccase production in Pluerotus pulmonarius-LAU 09 by mutation[J].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Research, 2012, 2(1): 11-17.
[42] 肖在勤, 周俊初. 金針菇與鳳尾菇科間原生質體融合研究[J]. 食用菌學報, 1998, 5(1): 6-12.
[43] 王澄澈, 梁枝榮. 鳳尾菇和香菇原生質體非對稱融合[J]. 菌物學報, 2000, 19(3): 413-415.
[44] 潘家駒. 作物育種學總論[M]. 北京: 農業出版社, 1994.
[45] 尚曉冬, 程繼紅, 譚 琦. 刺芹側耳菌絲相對生長性狀的研究[J]. 食用菌學報, 2007, 14(4): 9-18.
[46] Chai H, Zhou H, Zhao J, et al. Searching development-deficient genes in edible mushroom by self-crossing[J]. Agricultur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13(10): 2 037-2 043.
[47] 張俊玲, 章爐軍, 李 亮, 等. 自交選育秀珍菇新菌株“申秀1號”[J]. 微生物學通報, 2015, 42(8): 1 539-1 548.
[48] Adebayo E A, Oloke J K, Bordoloi A K, et al. The improvement of Pleurotus pulmonarius LAU 09 through mutation for yield performance[J]. Research Journal of Mutagenesis, 2012, 3(2): 1-13.
[49] 梁昌柱. 秀珍菇N+離子束誘變及銀杏葉栽培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學, 2014.
[50] 江枝和, 雷錦桂, 肖淑霞,等. 秀珍菇輻射新株系蛋白質營養價值的主成分和聚類分析[J]. 激光生物學報, 2009, 18(4): 516-519.
[51] 翁伯琦, 江枝和, 雷錦桂,等. 60Coγ輻射對秀珍菇子實體蛋白質營養水平的影響[J]. 激光生物學報, 2010, 18(2): 184-188.
[52] Chakravarty B. Trends in Mushroom cultivation and breeding[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1, 2(4): 102-109.
[53] 羅志姣. 雙孢蘑菇褐變相關PPO基因的克隆及表達分析[D]. 鄭州: 河南農業大學, 2009.
[54] Pezzella C, Lettera V, Piscitelli A, et al.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of Pleurotus ostreatus laccase genes[J].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3, 97(2): 705-717.
[55] Kajiwara S, Yamaoka K, Hori K, et al. Isolation and sequence of a developmentally regulated putative novel gene, priA, from the basidiomycete Lentinus edodes[J]. Gene, 1992, 114(2): 173.
[56] Szeto C Y Y, Wong Q W L, Leung G S, et al. Isolation and transcript analysis of two-component histidine kinase gene Le. nik1, in Shiitake mushroom, Lentinula edodes[J]. Mycol Res, 2008, 112(1): 108-116.
[57] 周爍紅, 沈穎越, 蔡為明,等. 肺形則耳變溫結實相關基因Ppcsl-1的克隆及功能預測[J]. 菌物學報, 2016, 35(8): 946-955.
[58] 何瑩瑩, 陳衛民, 周德群,等. 擔子菌孢子缺失菌株相關研究進展[J]. 食用菌學報, 2013, 20(1): 106-110.
[59] Okuda Y, Murakami S, Matsumoto T. Development of STS markers suitable for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of sporeless trait in oyster mushroom, Pleurotus pulmonarius[J]. Breeding Science, 2009, 59(3): 315-319.
[60] Okuda Y, Murakami S, Honda Y, et al. An MSH4 homolog, stpp1, from Pleurotus pulmonarius is a“silver bullet” for resolving problems caused by spores in cultivated mushrooms[J]. Applied &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3, 79(15): 4 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