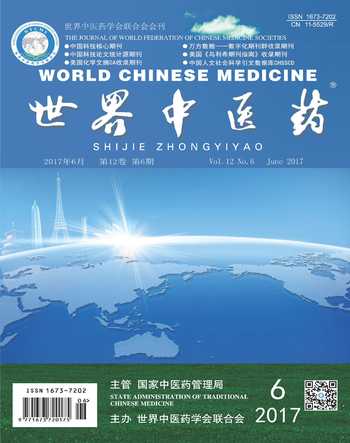針刀—整脊技術治療頸源性頭痛前瞻性多中心臨床研究
喬晉琳 丁宇 張秀芬

摘要 目的:探討王燮榮針刀-整脊手法治療頸源性頭痛的臨床療效。方法:選取2013年12月至2016年1月多中心收治的頸源性頭痛患者300例,隨機分為針刀整脊組150例和神經阻滯組150例。分別給予針刀聯合王氏頸椎整脊手法和神經阻滯組治療,治療1次/周,3次為1個療程。觀察治療結束后3個月、6個月VAS評分及臨床療效,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針刀整脊組治療頸源性頭痛近期、遠期總有效率分別為97.3%、92.0%,較單純神經阻滯組治療91.3%、68.7%,治療前后及組間比較VAS評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針刀聯合王氏頸椎整脊手法治療頸源性頭痛臨床療效滿意,安全有效,療效穩定,值得推廣。
關鍵詞 頸源性頭痛;針刀;整脊手法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ang Xierong′s acupotomy and chiropractic manipulation in treating cervicogenic headache. Methods:A total of 300 patients with cervicogenic headache admitted to Navy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from month, 20 to month, 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cupotomy-chirapractic group (n=150) and nerve block group (n=150), each of which was treated respectively with acupotomy combined with cervical spinal manipulation and the injection of nerve-numbing substance (one time a week, three times a course for both treatments). The VAS score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acupotomy-chiropractic group treating cervicogenic headache were 97.3% and 92.0% respectively, with those of nerve block group being 91.3% and 68.7%. Through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s of VA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s well as between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Acupotomy combined with Wang′s cervical spine manip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ogenic headache has satisfactory, safe and stable curative effect that is worth application.
Key Words Cervicogenic headache; Acupotomy; Chiropractic technique
中圖分類號:R245.31+9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7.06.057
頭痛是臨床疼痛診療時遇到的常見病,其病因很多,其中有一類頭痛與頸神經受刺激有關,稱頸源性頭痛(Cervicogenic Headache,CEH)。CEH臨床表現復雜,其疼痛持續時間較長,治療較困難,易被誤診偏頭痛、叢集性頭痛[1]等疾病。目前關于該病的治療相關文獻報道較多,但隨機對照研究較少,為科學評價國家級名老中醫王燮榮教授針刀聯合頸椎整脊手法治療CEH的療效,本研究采用隨機對照設計,進行了多中心臨床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2月至2016年1月海軍總醫院150例、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80例、北京望京醫院40例、北京電力總醫院30例,按多中心隨機分組法將患者隨機分為針刀整脊組150例,神經阻滯組150例。研究采用中心分層、區組隨機化方法,應用SAS軟件產生序列號為001~300所對應的隨機化方案,以序列編號的不透光的密封信封隱藏,志愿簽署知情同意書后按照被納入研究的順序進入不同的處理組。2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等經統計學分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診斷標準 參照國際頭痛協會診斷標準[2-3]:頸枕部疼痛,放射至額、眶、顳、頂或耳,至少符合以下一項:1)頸部活動時抵抗或受限;2)頸部肌肉的輪廓、硬度、緊張程度及在主動和被動活動時的反應性有改變;3)頸部肌肉存在異常的壓痛;4)同側的頸、肩或上肢呈非根性疼痛,或偶有上臂的根性疼痛癥狀。
1.3 納入標準 1)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年齡18~70歲;2)治療前1個月內未針對頸源性頭痛采用其他治療措施者;3)知情并自愿參加試驗,能積極完成臨床觀察者。
1.4 排除標準 1)排除其他病癥如藥物性頭痛、外傷、顱內感染、顱內占位病變、腦血管疾病、顱外頭面五官疾病以及全身疾病如急性感染、中毒等因素導致的頭痛;2)嚴重骨質疏松癥、腫瘤及結核等疾病不宜行手法治療者;3)對治療藥物過敏者;4)妊娠期及哺乳期婦女。
1.5 剔除與脫落標準 1)剔除標準:納入后未接受過試驗方案所規定的治療措施;未按規定方案治療,或合并使用其他療法或藥物而無法判定療效;2)脫落標準:未完成試驗而中途退出;出現不良事件或不良反應;3)中止標準:出現嚴重不良事件或不良反應,需中止試驗者及失訪病例。
1.6 治療方法
1.6.1 針刀整脊組 患者俯臥于治療床上,胸前墊枕,使頸部前屈,下頜置于床緣外,頭自然下垂,充分顯露頸枕部,確認C1-6棘突,于項韌帶、小直肌、斜方肌筋膜、寰椎后弓等處尋找陽性反應點,每次選取4~10個點,消毒鋪巾,選用Ⅰ型4號針刀(0.6 mm×50 mm),刀口線與患者身體縱軸平行,針體垂直皮膚表面緩慢探索進針,針刀到達骨面后縱切3~5刀,橫行剝離2~3下,刀下有松動感時出針,在針眼處用無菌紗布壓迫1~3 min,用無菌敷貼固定于施術點。針刀治療后立即采用頸椎整脊復位法:患者取仰臥位,術者立于患者頭部正上位,雙手頜-枕牽引,令患者頭自動轉向一側至最大限度,胸鎖乳突肌放松,頭頸完全放松,術者一手掌托住枕部,拇指輕輕定位于患椎橫突,另一手將下頜繼續向該側輕巧用力,雙手調整屈頸度數,使成角落于患椎并用適當的力快速旋轉一下,即可聞及彈性復位聲響,復位即告成功。對側也行相同手法復位,繼而應用拔伸手法軸線牽引頸部2~3次。以上治療1次/周,3次為1個療程。
1.6.2 神經阻滯組 選取以上相同治療點,2%利多卡因5 mL,曲安奈德5 mg,鹽水稀釋至20 mL,每點注射2 mL,2~4個點/次,1次/周,3次為1個療程。
1.7 觀察指標 1)疼痛分級標準:采用VAS評分法,以0~10數字標尺表示疼痛強度,“0”表示無疼痛,“10”表示極度疼痛,所有患者在治療前及療程治療結束后及結束后6個月分別標出與自己疼痛相匹配的分數。2)病情分級:主證(依病情輕、中、重分別給予2、4、6分,無癥狀者給予0分):偏頭痛、額痛、眼眶痛、枕下痛、頸部活動受限。次證(依病情輕、中、重分別給予1、3、5分,無癥狀者給予0分):眩暈、頸部僵硬、肩臂麻木疼痛、失眠、視物模糊。間歇性發作時長5~30 min,30~60 min、1~3 h、12~24 h、數天。兼證(依病情輕、中、重分別給予1、2分,無癥狀者給予0分):神經組織激發試驗(陽性6分,陰性0分);頸部屈曲-旋轉試驗(陽性6分,陰性0分)。
1.8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中醫病癥診斷療效標準》:痊愈:癥狀體征均消失,頸部功能恢復正常,疼痛癥狀未再復發;顯效:癥狀體征部分消失,功能基本恢復正常,不影響日常工作;有效:癥狀好轉,體征未完全消失,功能不完全恢復,勞累后加重;無效:癥狀體征無變化[4]。分別觀察療程結束后(近期療效)和療程結束后6個月(遠期療效)跟蹤隨訪,并統計療效。總有效率=(痊愈+有效)/例數×100%。
1.9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對2組數值變量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2.1.1 近期療效比較 療程治療結束后,2組患者近期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051,P<0.05)。見表2。
2.1.2 遠期療效比較 療程治療結束后6個月,2組患者遠期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846,P<0.05)。見表3。
2.2 2組患者治療前及療程治療結束后VAS評分 治療前2組VA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治療后近期與遠期療效分別與治療前比較,針刀觀察組與保守觀察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3 討論
對于CEH的發病機制、診斷及治療,臨床仍處于探索與研究階段,目前較為統一的觀點認為,C1-C3神經根或其支配的組織結構異常是誘發頸源性疼痛的解剖基礎。C1神經后支分布到頭后直肌、頭上斜肌和頭下斜肌,C2神經內側支與來自C3神經的纖維共同組成枕大神經、枕小神經和耳大神經,這些神經是傳導CEH的主要神經,外側支分布到頭最長肌、頭夾肌和頭半棘肌。C3神經后支的內側支分布到多裂肌,外側支分布到頭最長肌、頭夾肌和頭半棘肌。上述頸神經離開椎管后行走在椎管外肌肉組織內,如受寒、長時間的慢性勞損等,使肌肉供血減少,繼發肌痙攣,并使韌帶、肌筋膜等軟組織產生無菌性炎性反應,從而釋放炎性遞質,在軟組織內穿行的神經干及神經末梢處產生激惹而引發頸源性頭痛[5]。也包括椎管內的炎性刺激或椎間盤機械性壓迫高位頸神經根;頸椎小關節紊亂、枕部肌肉痙攣以及韌帶筋膜的炎性刺激或卡壓C1-C3神經根的分支如枕大神經、枕小神經所致[6],表現為上頸部及枕部疼痛,嚴重著可放射致整個頭部,所以患者疼痛主要表現在額、顳及眶部,可伴有上頸段疼痛不適。長期肌肉軟組織失衡,可導致頸椎小關節錯位,嚴重導致頸椎管狹窄癥。
名老中醫王燮榮教授認為,各種風寒濕邪的侵襲、長期的不良姿勢、不恰當的用力方法等均會導致脊柱內外平衡“失穩”,造成頸部軟組織損傷、勞損及頸椎關節的紊亂,特別是與寰椎、樞椎及枕骨下項線周圍的肌肉的痙攣、勞損等原因導致壓迫或刺激枕大神經、枕小神經、耳大神經等,最終導致頭痛的發生。王燮榮教授創造性的提出了“脊椎內外平衡理論”,首創“七論”學說,即:骨架-軟組織:電桿理論;脊柱-骨盆:高樓理論、桅桿理論、平臺理論、脊柱曲線-弓弦理論;尾骨-脊柱:船舵理論;脊柱整體:等腰三角形理論(疊羅漢理論)。在脊柱病內外力平衡失調理論的論述中,王燮榮教授指出:內平衡系統由椎體-椎間盤-小關節-前后縱韌帶及胸廓與骨盆構成(又稱骨性平衡系統,剛性平衡系統,靜力性平衡系統);外平衡系統由肌群及其他軟組織構成(又稱肌性平衡系統,柔性平衡系統,動力性平衡系統),從而解釋了頸源性頭痛發生的病因主要是脊柱內外平衡系統失調所致。
目前關于CEH的治療方法多種多樣,常見的保守治療如藥物口服、物理療法、針灸治療等,保守治療不容易從根本上解除枕神經的卡壓,臨床上針對枕大、枕小神經阻滯治療較常用,我們通過前期觀察發現,藥物口服治療CEH臨床療效不及針刀聯合整脊手法治療[7],主要原因是針刀對軟組織進行剝離松解,解除局部組織高應力,緩解神經的卡壓,這是藥物治療不能達到的效果。針刀一方面可起到粗針作用,針感較強,在治療過程中刺激機體,使中樞神經系統啡肽類物質含量升高,可達到即時鎮痛的作用,且針刀還能起到松解減壓作用,具有療程短,療效好的優點[8]。根據針刀的網眼理論[9],通過點-線-面針刀綜合治療,破壞了疾病的病理構架,針刀可直接深人到病變局部,對被卡壓的枕大神經、枕小神經以及高位頸神經支配的周圍組織直接進行剝離松解,解除神經的卡壓,通過針刀的切割、剝離局部的軟組織,解除局部的痙攣和攣縮,減輕局部的軟組織張力,打破局部的惡性循環,恢復重建人體力學平衡。針刀也可通過調控體內DRG內p38MAPK、CREB信號通路,抑制各種致痛的疼痛因子、生長因子的合成與分泌,從而提高痛閾起到鎮痛的作用[10]。此外,針刀還能激發體內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11],產生鎮痛物質,達到鎮痛作用。
通過針刀治療,可迅速改善和解除局部軟組織的粘連、攣縮、瘢痕、堵塞等病理變化,緩解局部軟組織的張力,使血管、神經等卡壓得以解除。在針刀松解治療完畢后,即刻應用王氏頸椎整脊手法,進一步使攣縮的軟組織瘢痕徹底松解,脊柱小關節紊亂得以糾正。王氏頸椎整脊手法不可扳動幅度過大、力度過猛,避免意外發生。該手法治療結合了傳統中醫整脊手法,是秉承中醫學的“筋骨并重”治療理念的具體體現,可使疼痛迅速緩解。杠桿理論既保證了手法的輕巧,又確保了療效,證實了王燮榮老師的脊柱內外平衡學說的獨創性和科學性。
本研究結果表明,針刀聯合手法治療CEH近期、遠期總有效率分別為97.3%、92.0%,較單純神經阻滯治療療效更好,且療效穩定。治療后近期、遠期VAS評分分別為(2.62±0.63)、(1.76±0.43),與神經阻滯治療有統計學意義。綜上所述,針刀觀察組治療CEH總有效率及VAS評分改善情況均優于保守觀察組及治療前,針刀聯合頸椎整脊手法治療本病的優勢在于能明顯改善患者疼痛癥狀、生命質量以及增加患者的社會適應性,無不良反應且快速、安全有效,避免了服用止痛藥物給患者帶來的損害,在治療時值得選用。本研究不足的是未對整脊手法力量的具體數值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毛希剛,肖克,唐偉偉,等.神經阻滯聯合小針刀治療頸源性頭痛療效觀察[J].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13,19(8):469-471.
[2]Sjaastad O,Fredriksen TA,Pfaffenrath V.Cervicogenic headache:diagnostic criteria.The Cervicogenic Headac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J].Headache,1998,38(6):442-445.
[3]姜磊,于生元.頸源性頭痛[J].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06,12(3):175-178.
[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S].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l996:204-205.
[5]田有糧,張昕,韓煥萍,等.手法松解配合頭頸部磁療治療頸源性頭痛臨床分析[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16,40(4):312-313,316.
[6]何亮亮,倪家驤.頸源性頭痛診斷及治療研究進展[J].中國全科醫學,2016,19(12):1392-1395.
[7]賈杰海,喬晉琳,丁宇,等.針刀聯合頸椎整脊手法治療頸源性頭痛的臨床療效觀察[J].中國中醫急癥,2015,24(10):1824-1826.
[8]丁宇,王燮榮,阮狄克,等.脊柱相關性疾病針刀微創綜合治療療效觀察[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21(25):2746-2747,2755.
[9]姚振江,肖榮,李玉琴,等.網眼理論對針刀治療的指導作用[J].河南中醫,2011,31(5):532-533.
[10]朱波,趙力,趙金巖.尺骨撞擊綜合征的關節鏡治療[J].中華骨科雜志,2016,36(15):980-987.
[11]額爾敦桑.針刀治療頸源性頭痛的臨床療效觀察[J].內蒙古中醫藥,2014,33(25):40.
(2017-05-02收稿 責任編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