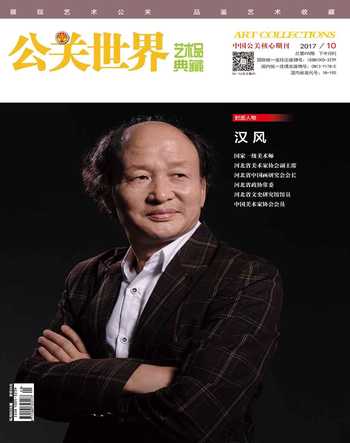唐宋山水自然的觀照與山水審美意識的覺醒
山水畫是一個(gè)龐大的課題,也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深度與廣度的畫種,配合將于9月17日在中華藝術(shù)宮開幕的“文心雕龍——上海山水畫邀請大展”(這也是上海歷史規(guī)模最大的山水畫大展之一),中華藝術(shù)宮近期舉辦了一系列山水畫講座,其中包括9月16日下午兩點(diǎn)知名畫家江宏的“中國畫的筆墨與心性”。
本文刊發(fā)的是畫家邵仄炯在中華藝術(shù)宮以“獨(dú)立與輝煌——唐宋山水畫經(jīng)典解讀”為名的講座實(shí)錄。
中國山水畫自魏晉興起,到隋唐逐漸獨(dú)立,再經(jīng)五代兩宋發(fā)展完備且成熟,并走向輝煌。至此山水畫占據(jù)了中國畫的主流地位。
晉代山水畫興起的主要背景是源于老莊玄學(xué)與山水詩的發(fā)展。當(dāng)時(shí)政局動蕩,很多士人避世隱逸,他們尚老莊玄學(xué)又與自然接觸后相互映發(fā),從山水的色、聲、形、貌之中,啟迪出對自然之道、理的領(lǐng)悟。南朝宋炳在《畫山水序》中就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的言論。至此,士人越過了老莊玄虛說理的抽象概念,直接從自然的變化中體悟闡明宇宙之道,于是山水詩得以發(fā)展。南朝重要的一位文學(xué)理論家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中有一句話“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即老莊玄言逐漸消退,山水詩開始盛行了。如陶淵明在《歸去來兮》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王羲之《蘭亭序》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些關(guān)于山水的名句名篇都是作者對自然的直接觀照而激發(fā)出對山水獨(dú)立審美意識的覺醒。
晉代,作為人物背景的山水畫
晉代山水畫是中國山水畫的孕育期,山水畫主要作為人物畫的背景出現(xiàn),有一些類似地形圖的山水圖像,還包括魏晉時(shí)期的畫像磚,敦煌壁畫中的樹石山圖像。
晉代繪畫中山水形貌的特點(diǎn):一、景物不講求比例關(guān)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二、樹石的造型具有很濃的裝飾味,圖案化、無立體感。三、山、樹排列無遠(yuǎn)近、大小的空間感,自由安排組合。四、山水中以人物為主,還出現(xiàn)禽獸之屬。五、畫法以線勾形或以色彩平涂為主。壁畫中的色彩較厚重,線條也較隨意。這些特點(diǎn)可以從南博藏的畫像磚《竹林七賢·榮啟期》,顧愷之《女史箴圖》、《洛神賦圖》中可窺見早期山水畫的雛形。山、石、樹、云、水皆造型古拙具有濃重的裝飾趣味,其中散發(fā)出早期藝術(shù)的想象力和欣欣向榮的生命力。
隋唐時(shí)期,山水畫成為獨(dú)立門類
隋代山水畫是六朝與唐的重要橋梁,隋唐很多畫家也并不是所謂的專工山水的畫家,他們更多仍以人物畫與宮苑、樓閣建筑畫見長。隋代展子虔就是其中一位,文獻(xiàn)記載其“尤善樓閣”,又有“模山擬石,妙得其真”。可見其不僅善畫樓閣,山水也已初具規(guī)模了。
《游春圖》是展子虔的一幅以山水景物為主題的作品,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幅獨(dú)立卷軸山水畫,內(nèi)容描繪初春之時(shí),游人騎馬,游船賞春的情景。此圖仍以線條勾勒山石、林木,但已與顧愷之《洛神賦》中的游絲描大為不同,其線用筆有勁挺之力,圓中帶方,山體造型也豐富自然,空間處理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點(diǎn)景的人物、建筑比例和諧,坡腳赭石,山體青綠,有輝煌富貴之氣。主峰山頭粗筆花青點(diǎn)出,略有幾分寫意的感覺。此圖為溥儀從清宮帶出流入民間,愛國人士張伯駒恐國寶流失,以170兩黃金收藏,后無償捐贈故宮博物院。
唐代多為建筑畫的宮廷畫家,山水景觀多與宮觀、樓閣相結(jié)合,如李思訓(xùn)、李昭道,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畫家閻立本都是“精意宮觀”后又能“漸變所附”。他們精于建筑畫中的山石樹木,并逐漸改變了山水圖像依附于宮觀樓閣等建筑為背景的這一狀況,逐漸讓山水畫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畫種。
傳世《宮苑圖》為李思訓(xùn)作,樓觀宮殿在自然山水之間。其中可見金筆勾線,顯得富麗而華貴。又有《江帆樓閣圖》,此圖景物繁密,樹的品類形態(tài)豐富,體現(xiàn)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表現(xiàn)的能力,用筆遒勁,精巧細(xì)密而又不失力度。
唐代山水畫山石還沒有筆墨的皴法,畫中山體結(jié)構(gòu)脈絡(luò)的繁密線條可作為皴法的過渡狀態(tài)。因此,最重要的技法是勾勒取其形填彩取其質(zhì)。青綠重色再加上金碧勾填,有陽光照耀閃爍的效果,顯出輝煌富麗的特點(diǎn)。也正與二李將軍富貴出身的氣質(zhì)相合,同時(shí)也表現(xiàn)出大唐帝國的繁榮,富足的氣象。明代董其昌創(chuàng)“南北宗”將李思訓(xùn)列為“北宗”之祖,后繼者又有趙伯駒、趙伯嘯,以至劉松年、馬夏之輩。
《明皇幸蜀圖》傳為李昭道畫,安史之亂,唐玄宗避難蜀地,皇帝駕臨一個(gè)地方叫“幸”。李昭道隨之入蜀畫了這張主題性的歷史畫,但今天我們看到這張畫更愿意將它作為青綠山水畫來欣賞。此畫的重點(diǎn)在于山石結(jié)構(gòu)空間的營造,山路的盤旋崎嶇體現(xiàn)了“蜀道難”的特點(diǎn),山勢高而險(xiǎn),奇而絕,氣勢雄強(qiáng),林木安排、云煙穿插自然而合理地表現(xiàn)出山水畫空間轉(zhuǎn)換的關(guān)系。《歷代名畫記》中說小李將軍“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我的臆想是昭道不僅技藝比父更為精妙,而且從此圖中對山體“勢”的營造上來看是更為出色的。
王維的水墨山水畫是作為唐代主流青綠山水的一個(gè)重要的補(bǔ)充。王維的詩與畫皆受禪宗思想影響,故崇尚“淡”的意境,他以水墨渲淡之法(渲染)開拓了水墨山水的新境界。在唐代可以說設(shè)色法成于李思訓(xùn),水墨法成于王維。雖王維山水也能體涉古今(古為青綠,今為水墨),但他的創(chuàng)造與貢獻(xiàn)在于水墨畫,因此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中列為“南宗之祖”。
王維是一位歷史上重要的山水詩大家。“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等名句都成為了山水畫的母題,蘇東坡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可謂詩畫合一由此始矣。可惜他的真跡罕見,《雪溪圖》為其傳世之作。
五代兩宋,山水畫的全盛
唐末五代戰(zhàn)亂頻繁,名士多隱跡山林,故畫家與自然更為緊密地接觸。山水畫成為了他們精神的重要寄托。五代宋初的山水畫家多以一種樸素的心理去敬畏,探索自然,從自然中發(fā)現(xiàn)整理出了山水畫的筆墨語言和語法,這些內(nèi)容為后世的山水畫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可以說這一時(shí)期的山水畫家是最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各種皴法、樹法、云水法,既豐富又系統(tǒng),將中國山水畫帶入了一個(gè)全盛時(shí)期,直至輝煌的巔峰。
如果說唐代山水畫的技法以空勾、填彩為主,那么五代、宋的山水畫家探索了筆墨表達(dá)的多樣化和可能性,他們脫下了華麗的裝飾外衣,走進(jìn)自然,作品盡物性、重氣韻,體格宏闊,勢質(zhì)俱佳,是真正得到了山林之氣的。
五代宋初南北各有大家,并各自創(chuàng)立了不同風(fēng)格。
北方山水畫因其地理環(huán)境特點(diǎn)表現(xiàn)出“雄健、峻厚”的特點(diǎn),代表畫家荊浩、關(guān)仝、李成、范寬。荊浩,河南人,號洪谷子,避亂隱居太行山之洪谷。他的《匡廬圖》在宋代定為真跡。雖畫的是廬山但仍有北山的氣勢,石質(zhì)堅(jiān)硬,山體雄厚。技法已從設(shè)色轉(zhuǎn)為筆墨,他的作品既開創(chuàng)了北方的山水畫派,又標(biāo)志了山水畫筆墨的全面成熟。荊浩不僅是位畫家還是一位理論家,他的山水畫論《筆法記》是他實(shí)踐的重要總結(jié),其中“圖真”、“六要”、“四品”、“四勢”對后世影響很大。關(guān)仝從荊浩學(xué),后并稱荊關(guān),有《關(guān)山行旅圖》、《秋山晚翠圖》有出藍(lán)之美。李成,五代末人,因居山東營丘又稱李營丘。他曾師關(guān)仝,然變其雄闊為清曠,故多畫平遠(yuǎn)寒林有《讀碑圖》、《喬松平遠(yuǎn)》、《晴巒蕭寺圖》。其筆致勁挺,墨色清潤。米芾贊為:“秀潤不凡”,又有“格老墨清,古無其人”之說。范寬是北方山水畫派最重要的一位畫家,初師李成后對景造意,寫山真骨,自成一家。其代表作《溪山行旅圖》中巨大的山頭占據(jù)畫面三分之二的位置,頂天立地又似撲面而來,極具震撼力。他以方直短促、有力量感的稱之為“豆瓣皴”或“雨點(diǎn)皴”的線條先皴后染、反復(fù)密集疊加,墨多而沉顯得山石蒼茫渾厚。前人比較李成和范寬的筆墨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yuǎn),范寬之筆遠(yuǎn)望不離坐外”。北宋大畫家王詵曾同時(shí)看了李、范的畫認(rèn)為李成“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范寬則“如面前直列,峰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可謂“一文一武”。

南方有兩位重要的山水畫家:董源、巨然。董巨可謂是江南山水畫派的代表人物。江南山水的特點(diǎn):山勢平緩、連綿,氣韻靈動,意境悠遠(yuǎn),筆墨更趨自然而抽象,技法以水墨為主。江南山水是米芾極為推崇的,后元四家、明四家、到董其昌及四王均為南北宗論中的“南宗一脈”此系畫家多為文人,于是元以后文人山水占據(jù)了山水畫的主流。南宗的領(lǐng)袖人物雖為王維,但真跡幾乎不存,實(shí)則多以董巨為宗。董源官居“北苑副使”,是負(fù)責(zé)園林的工作,生活在南京。他的畫“著色如李思訓(xùn),水墨類王維”,但其主要成就在其水墨,并創(chuàng)造了線型的披麻皴。披麻皴成為了元以后最重要的文人筆墨標(biāo)志。它與面型的斧劈皴一同構(gòu)建南北兩大筆墨形態(tài)。《瀟湘圖》《夏山圖》《夏景山口待渡圖》等為董源的代表性作品,多作平遠(yuǎn)山景,山峰舒緩連綿,遠(yuǎn)樹茂林,一派平淡幽深。南方松軟的土石結(jié)構(gòu)適用披麻皴表現(xiàn),山頭墨點(diǎn)積加顯得圓渾厚實(shí),并參入干濕及破筆的豐富運(yùn)用。米芾稱之平淡天真、一片江南、唐無此品。巨然是個(gè)出家人,師董源,他的皴筆在董的基礎(chǔ)上又有變化,出現(xiàn)了長披麻皴,線條連綿有韌性,山頂多礬頭。他的《秋山問道》是這一特點(diǎn)的代表作。還有《層巖叢樹圖》氣格清潤,有煙嵐氣象,作者的筆墨樸實(shí)無華地積加、點(diǎn)染,處處留心于自然的細(xì)微變化。體積、空間、虛實(shí)、疏密等關(guān)系精心體味并樸素地寫出,絲毫不見經(jīng)營的痕跡,靜觀畫面林壑間蘊(yùn)含了空氣的流動,宋初的畫家處處以一種無我的姿態(tài)來觀照對象,因此他們的山水真正有一股山林之氣。
在中國繪畫史上兩宋的繪畫以尚“理學(xué)”重“格物”思想,以真為貴。無論一石一樹、一花一鳥或工或?qū)懢浴案裎镏轮钡木癖憩F(xiàn)出大千世界的真實(shí)與精妙。從大眾欣賞的角度來看,兩宋的繪畫最易欣賞因?yàn)槭菍憣?shí)與圖真。晉唐的繪畫屬少壯期元?dú)饬芾焓翘炝Υ笥谌肆Γ谡瓶嘏c失控中博弈。元后的山水出彩的作品是人力與天力參半,如大癡的《富春山居圖》。只有兩宋的畫,因多院體皆是人力大于天力,技與藝、理法兼?zhèn)洌锵笮紊癖M在掌控之中。
北宋畫家郭熙,天性喜畫,供奉朝堂,授御書院待詔之職。他的畫備受皇帝的喜愛,在宮廷中重要的地方都讓他來畫。所繪《早春圖》為大幅的絹本,筆墨淋漓,線條粗細(xì)變化極大,樹木造型嚴(yán)謹(jǐn),鹿角、蟹爪程式分明。山石皴法為卷云皴或云頭皴,側(cè)鋒鋪毫,利用水分在絹面上托滑出筆觸,既有質(zhì)感又具體量。宋畫的筆墨在高超技藝的把控之中理性地造型狀物,筆墨緊緊地與物象的形交織在一起不分彼此。郭熙此畫筆力健壯,氣格雄厚。尤其是其構(gòu)圖:嚴(yán)整、堂皇。景物安排極具次序感,象征宋帝國的莊嚴(yán)與穩(wěn)固。 他和他的兒子郭思合著了一本山水畫史中的重要論著《林泉高致》,其中有些重要的觀點(diǎn):一,強(qiáng)調(diào)繪畫是有為的述作及其價(jià)值。二,畫山水要有親身的體驗(yàn),要注重景的選擇和取材。三,提出了三遠(yuǎn)法。四,概括了畫山水筆墨的多種方法。五,總結(jié)了山水畫的審美價(jià)值。全書對今天的學(xué)畫者仍有借鑒的意義。還有一位北宋的天才少年畫家王希孟,他十八歲時(shí)在宋徽宗的指導(dǎo)下畫出了《千里江山圖》卷,此圖構(gòu)圖遠(yuǎn)闊,空間變化繁復(fù),筆墨融五代勾皴并能回望唐代青綠的輝煌,在筆意周詳、色彩艷麗中盡顯華貴祥和的帝國氣象。這是中國山水畫史中青綠山水畫的輝煌之作。
李唐是一位跨越北宋、南宋兩朝的院體畫家。《萬壑松風(fēng)圖》為絹本大軸,是全景式的大山水,大氣、中正類似《早春圖》。但在技法上有很大差異,李唐概括出小斧披皴這一重要的山水皴法,不同方向的斧劈組合很好地表現(xiàn)出山石不同塊面的轉(zhuǎn)折,有強(qiáng)烈的立體效果,且具堅(jiān)硬的質(zhì)感。他的《江山小景》空間營造也極為復(fù)雜,樹木的穿插、山體的疊加、道路的縱深均組織有致,是學(xué)習(xí)經(jīng)營位置的極好范本。南宋以后李唐的畫風(fēng)有了變化,不同與以往的層層積加而是以飽含水墨的大筆酣暢淋漓的一遍而過,正如《清溪漁隱》等,風(fēng)格簡練,頗有天趣,這些特點(diǎn)影響到后世的馬遠(yuǎn)、夏圭等。南宋的山水畫到了馬遠(yuǎn)、夏圭的筆下又是另一番意境了。北宋山水多全景到了南宋則趨向局部的邊角,似乎暗喻國勢的衰落。馬夏的山水多以局部取勢,以一角半邊為景,線條硬勁,墨法蒼潤變李唐的小斧劈為蒼勁的大斧劈,如馬遠(yuǎn)《踏歌圖》、夏圭《溪山清遠(yuǎn)》其間筆墨均清曠爽利,意境悠遠(yuǎn),似有淡淡哀傷的情調(diào)。
中國山水畫帶有濃郁的人文精神,宋代以丘壑為勝,元人則以人品為尚,明清則側(cè)重筆墨,以傳統(tǒng)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