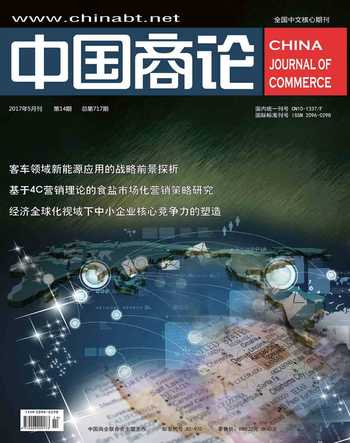“環(huán)境新常態(tài)”下科技人力資源是否發(fā)生轉(zhuǎn)移?
劉子扣
摘 要:在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下,環(huán)境同樣面臨“新常態(tài)”,而在這樣一個(gè)時(shí)期,對(du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的科技人力資源是否會(huì)受生存環(huán)境的影響而改變其生活地域,轉(zhuǎn)向環(huán)境質(zhì)量相對(duì)較優(yōu)的地區(qū)呢?本文正是以此展開,運(yùn)用OLS估計(jì)方法,選取科技人力資源相對(duì)富足的6個(gè)地區(qū),探究從2005年~2013年各地科技人力資源占全國(guó)比重變化原因。結(jié)果顯示,科技人力資源的轉(zhuǎn)移受到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就業(yè)機(jī)會(huì)、薪酬待遇的影響較大,而環(huán)境因素對(duì)其轉(zhuǎn)移所起到的因素微乎其微。這也告訴各區(qū)域政府,發(fā)展經(jīng)濟(jì)和提升科技人力資源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才是吸引其的關(guān)鍵點(diǎn)。
關(guān)鍵詞:科技人力資源 轉(zhuǎn)移因素 環(huán)境新常態(tài)
中圖分類號(hào):F272.9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0298(2017)05(b)-150-02
1 引言
當(dāng)今我國(guó)已經(jīng)進(jìn)入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階段轉(zhuǎn)換的關(guān)鍵期,經(jīng)濟(jì)增速換擋,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向均衡期逐漸過渡,能源消費(fèi)增速趨緩,被人們稱作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常態(tài),而隨之帶來的是環(huán)境的“新常態(tài)”,其表現(xiàn)在污染物新增量漲幅進(jìn)入收窄期,同時(shí)污染排放疊加進(jìn)入平臺(tái)期。創(chuàng)新是發(fā)展的主要?jiǎng)恿Γ谥袊?guó)目前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的發(fā)展背景之下,需要利用科學(xué)技術(shù)進(jìn)行創(chuàng)新,發(fā)展新動(dòng)能,促進(jìn)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有主觀能動(dòng)性的科技人力資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gè)方面,因此,我們需要調(diào)查科技人力資源在“環(huán)境新常態(tài)”下的時(shí)空流動(dòng)趨勢(shì)。
2 文獻(xiàn)綜述
在科技人力資源的研究上,眾多學(xué)者主要將目光集中于兩點(diǎn):科技人力資源的集聚效應(yīng)和科技人力資源對(duì)經(jīng)濟(jì)的貢獻(xiàn)。在科技人力資源的集聚上,王奮和韓伯棠(2006)構(gòu)建了基于科技人力資源區(qū)域集聚指數(shù)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模型,并通過近四年的數(shù)據(jù)分析了不同區(qū)域的科技人力資源的集聚效應(yīng);袁建明、潘偉偉和湯玉坤(2010)實(shí)證分析了中部六省科技人力資源集聚和優(yōu)化配置的現(xiàn)狀,并提出了相應(yīng)對(duì)策和建議;王巍(2015)實(shí)證檢驗(yàn)了西部地區(qū)各種資源的集聚效應(yīng),揭示了西部地區(qū)各種資源的集聚程度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促進(jìn)作用。在科技人力資源對(duì)經(jīng)濟(jì)的貢獻(xiàn)方面,張喜照(2005)發(fā)現(xiàn)我國(guó)研究與試驗(yàn)發(fā)展(R&D)人員全時(shí)當(dāng)量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之間存在長(zhǎng)期穩(wěn)定的動(dòng)態(tài)均衡關(guān)系;姜玲(2010)研究表明環(huán)渤海地區(qū)科技人力資源具有全國(guó)性比較優(yōu)勢(shì),但其集聚程度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聯(lián)動(dòng)趨勢(shì)不顯著;薛俊波(2010)指出中部主要省份的科技人力資源在近10年獲得了較快發(fā)展,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逐步提高。針對(duì)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很少有文章探究影響科技人力資源的轉(zhuǎn)移因素,特別是環(huán)境因素對(duì)于科技人力資源的轉(zhuǎn)移影響。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影響科技人力資源的轉(zhuǎn)移因素,特別探究在“環(huán)境新常態(tài)”下,科技人力資源是否發(fā)生了轉(zhuǎn)移。
3 實(shí)證數(shù)據(jù)分析
3.1 模型構(gòu)建和樣本選取
在問卷調(diào)查和以往文獻(xiàn)閱讀的基礎(chǔ)上,本文選取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流動(dòng)影響最大的幾個(gè)因素作為自變量,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占全國(guó)比重進(jìn)行OLS回歸分析。在自變量的選取中,本文認(rèn)為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動(dòng)受到經(jīng)濟(jì)性因素與非經(jīng)濟(jì)性因素的影響。其中,經(jīng)濟(jì)性因素指經(jīng)濟(jì)動(dòng)機(jī),包括所得、就業(yè)機(jī)會(huì)與生活成本因素。而非經(jīng)濟(jì)性因素主要有生活質(zhì)量與舒適性、信息、不確定性及風(fēng)險(xiǎn)。在具體指標(biāo)的選取上,經(jīng)濟(jì)性因素選取GDP總量、城鎮(zhèn)單位就業(yè)人口平均工資、CPI指數(shù)、單位就業(yè)人口/總?cè)丝冢环墙?jīng)濟(jì)性因素選取AQI和教育發(fā)展水平。樣本主要選取科技人力資本占比較大的六個(gè)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山東省,時(shí)間跨度從2005年~2013年。其中,教育發(fā)展水平的測(cè)度通過多指標(biāo)的極值標(biāo)準(zhǔn)化和加權(quán)相加得到,具體指標(biāo)選取為:小學(xué)專任教師數(shù)量比重(0.2)、初中專任教師數(shù)量比重(0.1)、中學(xué)專任教師數(shù)量(0.1)、大學(xué)數(shù)量(0.3)、研究生培養(yǎng)單位數(shù)(0.3),括號(hào)中為具體分配權(quán)重。
3.2 實(shí)證分析
對(duì)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回歸分析,結(jié)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在回歸結(jié)果中除CPI和AQI外,其他結(jié)果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證明科技人力資源確實(shí)受到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GDP)、薪酬與福利水平和就業(yè)機(jī)會(huì)的影響,同時(shí),我們還可以看出,因變量對(duì)自變量的解釋結(jié)果較好,調(diào)整后的可決系數(shù)達(dá)到0.96。但從表1中也能夠看出,物價(jià)水平和空氣質(zhì)量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動(dòng)影響并不顯著,這與文章初始設(shè)想的結(jié)果相反,在“環(huán)境新常態(tài)”下,科技人力資源并未受到環(huán)境影響而發(fā)生轉(zhuǎn)移。
經(jīng)過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1)本文由于AQI數(shù)據(jù)獲取受限,數(shù)據(jù)時(shí)間跨度較小,同時(shí),該時(shí)間段內(nèi)未包含近年來空氣質(zhì)量急劇惡化的時(shí)間段。(2)年度數(shù)據(jù)精細(xì)度不夠,不能即時(shí)反映情況。(3)空氣質(zhì)量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的轉(zhuǎn)移是一個(gè)長(zhǎng)期過程,季節(jié)性因素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流動(dòng)會(huì)產(chǎn)生較大影響,但空氣質(zhì)量不好的季節(jié)集中于冬季,而科技人力資源轉(zhuǎn)移的時(shí)間通常是春季,春季來臨,空氣質(zhì)量轉(zhuǎn)好,科技人力資源改變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的意愿減弱。(4)選取的科技人力資源充裕地區(qū)的空氣質(zhì)量基本無極差情況。(5)科技人力資源主要分布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這些地區(qū)經(jīng)濟(jì)收入水平相對(duì)較高,受提升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的驅(qū)動(dòng),企業(yè)對(duì)創(chuàng)新型人才需求旺盛,加上科研環(huán)境和工作條件較優(yōu)厚,市場(chǎng)對(duì)人力資源的配置能力較強(qiáng),因此,相對(duì)其他地區(qū)對(duì)科技人員的吸引力也更強(qiáng)。
4 結(jié)論與建議
4.1 結(jié)論
(1)與影響一般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因素相比,影響科技人力資源集聚和流動(dòng)的因素同樣可以分為經(jīng)濟(jì)性因素和非經(jīng)濟(jì)性因素兩個(gè)方面。但我們可以看到經(jīng)濟(jì)因素的影響占據(jù)絕大部分地位,同時(shí),在非經(jīng)濟(jì)性因素中,教育水平也十分顯著。
(2)“環(huán)境新常態(tài)”這一假設(shè)下的情況很大可能并不成立,在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文的AQI對(duì)于科技人力資源轉(zhuǎn)移影響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科技人力資源并未將環(huán)境作為其轉(zhuǎn)移的關(guān)鍵影響點(diǎn);同時(shí),環(huán)境的惡化時(shí)間和科技人力資源的流動(dòng)時(shí)間并不匹配。
4.2 建議
對(duì)于政府來說,首先,應(yīng)當(dāng)留住當(dāng)?shù)厝瞬牛诒疚闹锌梢钥闯觯逃龑?duì)科技人力資源影響顯著,科技人力資源愿意留在其原本接受教育的環(huán)境中,因此,對(duì)于在當(dāng)?shù)孬@得教育的科技人力資源,政府應(yīng)當(dāng)通過各類優(yōu)惠政策將其留在當(dāng)?shù)兀@樣能夠防止人才流失;其次各地政府應(yīng)當(dāng)實(shí)施科技人力資源的補(bǔ)償和激勵(lì)政策,補(bǔ)償政策主要指物質(zhì)方面的補(bǔ)償,因?yàn)榻?jīng)濟(jì)性因素對(duì)科技人力資源流動(dòng)的影響不可忽視,同時(shí),激勵(lì)則針對(duì)其心理?xiàng)l件,為科技人力資源提供更多地就業(yè)機(jī)會(huì)、發(fā)展機(jī)會(huì),同時(shí),提升他們的社會(huì)地位和社會(huì)認(rèn)同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diǎn),當(dāng)?shù)卣畱?yīng)當(dāng)注重發(fā)展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水平,切實(shí)提升當(dāng)?shù)氐纳姝h(huán)境,這樣才能真正達(dá)到良性循環(huán)的實(shí)現(xiàn),確保科技人力資源的正方向和可持續(xù)流入。
參考文獻(xiàn)
[1] 王奮,楊波.科技人力資源區(qū)域集聚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研究——以北京地區(qū)為例[J].科學(xué)學(xué)研究,2006(5).
[2] 姜玲,梁涵,劉志春.環(huán)渤海地區(qū)科技人力資源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研究[J].中國(guó)軟科學(xué),2010(5).
[3] 張?zhí)m霞,付競(jìng)瑤,姜海滔.我國(guó)區(qū)域中心城市科技人力資源競(jìng)爭(zhēng)力評(píng)價(jià)[J].東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