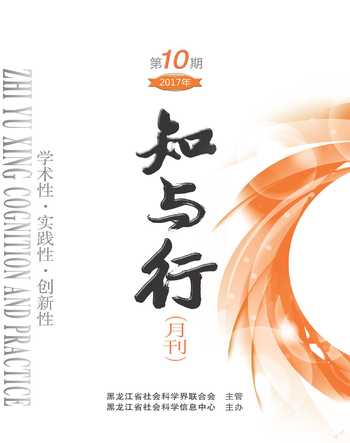論互聯網時代普法困境與出路
馮碩
[摘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為新形勢下我國的普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這一新要求,長期以來收效甚微和流于形式的傳統普法模式已然走入了困境。而在互聯網時代社會權力變遷和自組織社會逐漸形成的情況下,更是讓傳統普法模式的不適應性日漸突出。因此,互聯網時代的普法模式應當契合互聯網的特性,引入以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為特點的互聯網思維或許是普法模式的新出路。而在互聯網思維影響下,“人物型”普法模式更是在傳統普法模式基礎上依托互聯網時代社會結構的新變化而建立的。其以去中心、分布式和離散化為特點建構的新的普法模式,其力圖回避法律家長主義的局限,實現知識與權力的雙向結合,從而培育法治土壤以找尋實現時代發展需要、培養法治文化、提高普法效率等多維目標的普法新出路。
[關鍵詞]普法困境;互聯網思維;“人物型”普法
[中圖分類號]D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284(2017)10-0062-05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精神文明創建內容,開展群眾性法治文化活動”。其將普法目標定位為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樹立法治意識,強調要充分發揮群眾的自主性,引導群眾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意識,逐步改變社會上那種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現象。而想要達成這一普法目標,傳統的普法模式顯然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互聯網時代陷入困境的普法模式的出路在哪需要我們予以關注,這決定了普法目標能否實現。
一、互聯網時代傳統普法模式的困境
縱觀過去三十年的普法工作,普法的特點可以總結為政府主導性、社會參與性、目的性和公益性。可見傳統模式下突出強調政府主導,形成了依靠司法行政系統由組織中心統一設計安排的普法模式。然而伴隨著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離散性、交互性、便捷性等特征日益突出,傳統普法模式已難以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潮流,從而陷入普法困境。
(一)傳統普法模式的固有困境
傳統普法模式走入困境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因看,其運作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中心化趨勢明顯,以量化標準進行考核使得普法工作流于形式。所謂量化標準,是一種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以賦分考核的方式衡量普法效果的體制。這種普法工作的考核標準已將普法變成了行政任務,完全依靠各級政府的行政主導,從而使得普法工作止于表面,流于形式。量化標準指引下導致長期以來的普法機械化地執行上級任務,從而使得普法內容脫離實際,普法形式強調灌輸。
從普法內容上,多數人認為在普法中所接受的信息更多是時下較為關注的幾大熱點,但熱點問題是否與受眾本身有關卻往往被忽視。并且更多的選題側重于政策宣講或政治學習,讓受眾難以區分究竟是普及法律還是學習新指示精神。從普法形式上,筆者通過分析相關基層政府的普法評分細則發現,在基層普法中組織者最樂于進行且賦分較高的普法方式便是課堂型普法,資金花銷最大的也是購買普法課本與材料。課堂上專家結合課本講一講,下面的聽眾隨便翻一翻,老百姓領本書就回家的比比皆是。最終錢也花了,書也發了,但法真的普了嗎?有外在的灌輸,卻無內心的改變。作為理念的和由國家推進的法治的正當性確乎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法治的實惠卻并沒有落實。
所以,傳統普法模式的行政化趨向,使其在量化標準的指引下變得流于形式。從而使得普法內容脫離實際、普法形式強調灌輸,既難以調動群眾主動性,也不可能進一步培養法治精神。
(二)權力變遷下的普法困境
傳統普法模式自身的缺陷尚難彌補,而時代的變遷更是加速了其走向困境的步伐。傳統普法模式在本質上是依靠行政權力推動下的單向普法,承襲了我國“以法為教”的傳統,強調統治者有責任主導教化民眾的“法律家長主義”[1]。也正是在這種政府主導下的單向普法,才實現了以知識為載體的國家權力的延展。但這也往往落入了普法即為運動的怪圈,在力圖否定普法是政治運動的同時又難逃普法運動的魔爪。在強調政府主導的多元運作口號下,仍然刻意回避了時代的多樣性,只要一種聲音、一個精神,試圖加強整個社會當下的共時性。這種帶有訓斥意味的普法簡單地將受眾客體化,單從現實操作層面,就讓一場普法變成了“包公戲”般的呵斥與教訓[2]。
然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社會關系網絡與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的雙重轉型,讓權力從共同體向個體開始轉移。從信息資源上,互聯網打破了民眾與權力中心之間的信息藩籬。一方面,權力中心的崩塌釋放出大量的“自由活動的空間”與“自由流動的資源”,使個人對國家、組織的依附程度減弱,組織框架之外的生存空間與路徑日益增多[3]。另一方面,這種權力向個體的轉移表現出互聯網的“賦權”本質,這一特質將引發積極的社會變遷,在數字化的未來人們將找到新的希望與尊嚴。所以,在個體崛起的互聯網時代,法律是按照復線展開的社會不同角色之間的對話關系,所有人的意見和正義觀念都應該得到表達從而形成普遍接受的法律框架。因此,傳統普法模式的推進已然失去了其運行的權力基礎,依靠行政權來主導普法工作并以教化和規訓為中心的普法思路已成強弩之末陷入了困境。
(三)自組織結構下的普法困境
互聯網時代的權力變遷使得個體承接了原有權力中心所占有的社會資源,而伴隨權力的轉移,相應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得以重構。就在這種重構當中,互聯網時代正在實現從被組織向自組織的跨越。
自組織結構主要指系統在獲得空間、時間或功能過程中,沒有外界的特定干預而自發形成結構[4],與之相對的他組織結構則是依靠設計與控制形成的關系結構。計劃經濟下的我國社會是典型的他組織系統,龐大的社會關系被單位制逐漸分割。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個體開始脫離單位尋求自我關系網絡的重構。而互聯網的開放和交互更是讓關系網絡門檻日益下降,權力的變遷更是打破了固有社會關系格局,進一步增強了他組織的破裂和自組織的形成。反觀普法,傳統模式是典型的他組織結構,整個系統的運行依靠著組織中心在信息和資源等方面的供應、分配和控制。然而,由于人口流動性的不斷增強,行政組織對于人口的管理越發困難。加之當今社會多元化、破碎化、風險化而形成的不同階層、群體和個人利益和訴求[5],即使足以依靠行政權實現對個體的管理,也難以應對如此多元的利益訴求。
所以,伴隨著互聯網時代自組織模式的逐步發展,組織的形成和運轉越發脫離了行政權的干預,轉而向著共同的利益和訴求進行自我演化。社會大格局的變革趨勢令傳統普法模式無所適從,被組織的框架正在崩塌而自組織的時代已然到來,通過行政權力來控制個體進行普法的方式已陷入困境。
二、走出普法困境的新出路: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原有普法模式陷入困境,想要實現中央對于普法工作的新要求就要順應時代進行改革。而引入互聯網思維對普法模式進行改革,或許會探索出新的出路。
(一)互聯網思維中的不可預測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是世界是可知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認識之物,而無不可認識之物。基于這一觀點,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才會充分的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實踐去發現一些規律并以此規律來預測未來。這種依靠所謂的“規律”進行對未來的預測,是一種建構在因果律認知上的,是在事物推進較為緩慢的過程中所建立的認識思維。但互聯網大大縮短這一過程,導致了整個社會系統的復雜性與可變性不斷升級,我們想要通過簡單的因果律來對當下加速的社會進行預測可謂難上加難。
在社會發展面前我們應認清自己的局限,重新審視我們當前的普法工作。我們要認識到,傳統普法模式中的組織中心是無力設計并預測出整個普法工作進程的。即使是在層級組織中層層細化的設計,到了具體實施中我們也無法預測出其中的變數。這也讓我們的普法工作常常陷入一種社會關注、群眾關心但我們的普法組織又無從下手的尷尬境地。我們的組織中心在規劃中并未涉及也不可能涉及這些問題,這體現了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傳統普法模式的局限。
(二)互聯網思維中的不可控制性
預測是在靜態下進行的,而在活動的執行過程當中不可控制性便隨之出現。互聯網聯通了整個世界,它讓事物在加速發展中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而這種變化一旦發生在整個社會組織當中,便會形成一種巨大的變革,從而讓原有的組織中心失去對整個或部分系統的有效控制。
例如著名的沙堆實驗,正是通過力學的計算發現當沙堆堆積到一定程度后,每一粒沙子的下落都有可能造成整個沙堆的崩塌。將沙堆比作整個社會組織,那么某一個組織成員的變動都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組織的變形,這便是自組織臨界理論所涉及的問題。自組織臨界理論更多的是討論系統內部的問題,強調到達一種臨界狀態下整體結構的變化。互聯網的加速功能,使得這個社會沙堆堆積的速度越來越快,其到達臨界狀態的時長不斷縮短。而互聯網時代更是讓每個元素的作用不斷放大,形成了一種個體崛起的大趨勢。在互聯網世界里,每一個個體都可能借助整個系統發揮出其難以預估、組織中心更是難以控制的力量。
(三)互聯網思維指導下的“人物型”普法
互聯網時代的個體崛起和自組織擴張,導致了圍繞個體產生離散化的多點分布小組織的形成。但當互聯網社交疊加在傳統社交網絡之上時,這一社交網絡則被擴大。而形成的新型組織模式,便是以去中心、分布式、離散化為突出特點的。
1.去中心強調各負其責。信息流動成本的降低,令信息“中心化”不可逆轉的轉向信息的“去中心化”,信息傳遞方式的改變深刻變革了社會深層結構,使得原有的組織中心與新生中心之間的矛盾得以凸顯,本質上反映了個體崛起中原有體系的權力分配問題。正如喬姆斯基所說“通常一個中心化的權力體系會為其中最有權力的因素進行高效的服務”,而當個體權力通過互聯網擴大之后原有中心再無力預測和控制之時,自組織就會形成新的中心并與原有組織中心形成權力上的重新分配。這種分配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平衡性的分配,而非消滅性的分配。所謂的去中心,實質上是將原有的組織中心的地位降低,將其原有權力重新分配,讓其成為新的組織結構中的一個普通中心。
“人物型”普法模式正是在此方式上建立的,是在個體崛起的前提下每一個基層中心對原有的組織中心某些普法職能進行再分配的過程。也就是發現基層普法的中心人物,將普法內容的確定、方式的決定等具體權力賦予他。而對于原有的組織中心也就是各級政府主管部門或NGO的領導部門,由于在國家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獲取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所以其仍要保留方向的確定、法律與觀念的更新等抽象權力。
2.分布式促進多中心共享。去中心化后產生了許多新生的中心導致原有結構被打破,而如何處理這些中心的關系,則引出了分布式結構。所謂的分布式是指要求整個組織放棄原有的層級關系,而是轉為構建基于互聯網平臺上各個中心平等的信息交流與協作的關系。互聯網的出現,實際上是將系統中的個體進行松綁,在松綁中形成新的中心并分布開來。分布式狀態下的組織結構,更多的是一種動態變動的模式,也正是這種可變性才讓每一個新生中心在預測與控制上有著更強的能力,能夠以自身的能力或利用自組織的資源進行快速反應。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布式結構并不是徹底割裂原有組織體系,而是將原來依靠行政控制的組織聯系轉為依靠網絡等新興技術進行聯系,弱化自上而下的強制力,更強調一種共享、共生、共融的運行模式。
因此,以共享為前提的分布式結構,其每一個分布出去的自組織中心都會在具體的普法工作中面臨不同問題。這些不同的問題,在自我處理的同時也會通過互聯網上傳到整個系統進行共享,其他的自組織中心可以加以利用。而傳統組織中心更可以將其抽象化進行研究總結,服務于國家立法與行政等多個領域。
3.離散化調動基層能動性。離散化的基礎在于信息的逆向二級傳播,它不同于由傳統的中心階層掌握信息并有選擇性的向一般受眾傳播的模式,而是由底層群體的網絡傳播并借助互聯網來影響中心階層。這種離散化的狀態與分布式的結構形成互補,如果說分布式是從橫向角度闡述,那么離散化則是從縱向結構對信息發布與反饋過程進行變革。
互聯網時代的不可預測與不可控制,導致傳統普法模式難以對基層普法實際問題進行前期預測和及時反應。而“人物型”普法模式引入的離散化思維,將大組織從縱向層級緊密控制中進行疏離,更加強調基層中心人物在普法中的能動性。其核心原理也在于當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遞方向發生逆向,我們便也要將反應與處理的模式進行轉變。而“人物型”普法這種前期鋪墊教育,及時反應并運用自身知識儲備進行熱點普法,不僅會控制住這種極端觀點的擴散,也有助于受眾進一步理解我國的法律制度,更可以進一步塑造公民性品格,促進理性規則秩序的建立。
三、“人物型”普法模式的構建意義
互聯網思維指導下的“人物型”普法模式從本源上是順應互聯網時代的基本發展方向,并針對傳統普法模式的固有局限而展開的。是一個開放、互動的平臺更是一個“活的結構”,并試圖針對中央普法新精神來突破原有困境。
(一)從主導變引導,回避“法律家長主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政府在普法工作當中的作用開始變主導為引導。政府放下的姿態,恰恰順應了去中心的要求。政府主動找到自己在社會網絡當中的位置,強調社會自身治理的重要性,讓渡出的權力由普法中心人物予以承擔,從而實現受眾的崛起。
去中心的方式,實際上是從權利本位展開的敘事,這種定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社會黏合”功能之上的,其看到了普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灌輸,普法的效用應建立在“良性互動”的普法實踐之上。通過減少政府在普法工作當中的權力,釋放更多活力給基層普法核心人物。在制度層面告誡政府回避“法律家長主義”傾向,不要事事都管,無孔不入。要充分的相信群眾并依靠群眾,敞開大門讓群眾參與進來,并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引導,把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團結起來,建構更大更深的聯系網。
(二)從生人變熟人,實現知識與權力的雙向結合
從“知識—權力”分析的角度出發,普法的過程就是送權利和奪權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將受眾從地方性知識中拉出,把特殊的個人與統一的尺度結合起來。當你與這一尺度不符,便把你放逐到“法律意識”之外,并通過訓練和制裁塑造某種客觀化的新人形象[6]。當你帶著新形象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時,“法治”接受了你但鄉土卻將你遺忘。我們每一個人無不處在這樣一個矛盾體當中,左顧是“法治”的召喚,右盼是“鄉情”的眷戀。
分布式組織形式的建立,通過在每一個普法核心人物身上播撒法治的種子,讓它在地方性的土壤當中成長,實現統一與多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合。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對每一個受眾來說,發自地方知識的親切感讓他們相信并樂于求教于核心人物,而核心人物所具有的知識,又讓受眾在親近之時與法治相連接。這種權力的過渡與融合,弱化了普法過程當中的二元對立,給予受眾足夠的空間來接受,也給予法治足夠的時間來調整,以防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 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7]。
(三)從灌輸到啟蒙,培育法治土壤
我們應明確,中央對于新形勢下普法的要求直指培育法治土壤,提高權利意識與法治意識。以法治意識弘揚核心價值,更以法治精神填補法律疏漏。法律天生具有不周延性,防止法律的規避與合謀,更多的要依靠每一個公民內心的稱量。只有真正樹立法治意識,培養出權利義務分析為線索的法律思維[8],才能從末端降低法律規避的可能性。
培育法治土壤,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首先要改變原有的灌輸式普法。灌輸總帶有強制的意味,本身便具有明顯的外迫氣質[9]。這極易讓受眾做出反抗,更難以播撒法治種子以期實現內化。相較于灌輸式的普法,“人物型”普法模式借助互聯網思維的離散化,將普法核心人物散落在生活的每個角落,用自己去影響和啟蒙受眾。因為法治啟蒙的目標不在于將人置于法律的專制之下,而在于將法治的理想、法治的規則以及法治的好處向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按照自己的理性而選擇。它不同于灌輸的外迫與施舍,它給予每個獨立個體運用理性自主判斷的空間,由其自己做出選擇。也正是在這種身邊的啟蒙下,法治種子落地生根,逐漸地適應土壤并改變土壤,培育出普法所希冀的法治文化。
四、結語
我們應看到,對模式的革新實質上是對權力結構的重構。想要突破原有模式困境,首先要看到推動原有模式變動的權力結構發展的趨勢。互聯網時代的權力變遷和自組織發展使得傳統普法模式陷入困境,而對其的革新更應當對癥下藥,以互聯網思維指導其變革,來促成“人物型”普法模式的建立。而這也符合發揮群眾自發性,促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中央精神。互聯網時代的普法,組織中心要敢于放權,這一時代異軍突起的“人物”更要善于用權。在承接普法權力的同時提高自身法治素養,帶動周圍進行法治建設,最終在全社會形成群眾性的法治文化,為我國的轉型升級培養符合現代國家發展規律的法治土壤。
[參考文獻]
[1]黃文藝.作為一種法律干預模式的家長主義[J].法學研究,2010,(5):6-9.
[2]蘇力.中國傳統戲劇與正義觀之塑造[J].法學,2005,(9):50.
[3]孫立平.“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J].探索,1993,(1):64-68.
[4]吳彤.自組織方法論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5.
[5]馬長山.法治中國建設的“共建共享”路徑與策略[J].中國法學,2016,(6):6.
[6]馮象.木腿正義——關于法律與文學[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23-24.
[7]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8.
[8]鄭成良.論法治理念與法律思維[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7):7.
[9]高鴻鈞.現代法治的出路[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54.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a's legal work in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with this new request, the traditional law popularization model, which has long been ineffective and has gone from formality, has entered a dilemma. In the era of Internet, social power changes and self-organized society is gradually formed, so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law popularization model to adapt to all these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law popularization model in the internet age should f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Introducing Internet thinking characterized by unpredictability and uncontrollability may be a new way out for the law popularization mode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thinking, the "figure-based" legal literacy mode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law popularization mode by relying on the new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Internet age. It tries its best to evade the limitations of legal paternalism and achieve a two-way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power so as to foster the soil of the rule of law so as to find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new law popularization model with multidimensional goals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times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 the culture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e popularization efficiency and so on.
Keywords: law popularization dilemma; internet thinking; "figure-based" law popularization
〔責任編輯:張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