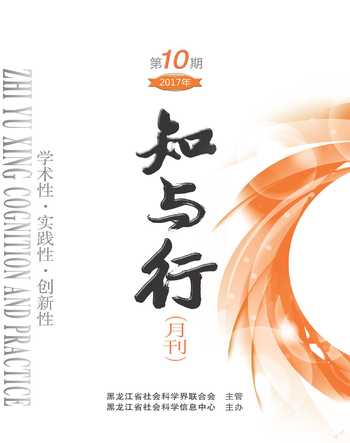康有為對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與闡釋
李洪楊
[摘要]在對諸子之學進行考辨和梳理的過程中,康有為對董仲舒推崇有加,將其看作是“漢世第一純儒”。這不僅緣于董仲舒在孔門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對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至精闡發,也緣于董仲舒春秋學的宗旨要義為康有為變法維新的主張提供了理論參考和思想來源。在對董仲舒及其思想進行研究與闡釋的過程中,康有為一是對董仲舒的思想來源及其在孔門中的地位進行了研究與闡釋。康有為認為,董仲舒的思想淵源于孔子,是孔子之學特別是《春秋》改制之學的直接承續者和闡揚者,并將董仲舒界定為孔子之后學、孔門中人。由于董仲舒不僅發現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同時也將其闡釋得淋漓盡致,其對孔子思想中所深隱的微言大義的體認超過孟、荀,康有為賦予了董仲舒在孔門中極為重要的地位。二是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人性說、歷史觀等思想進行了研究與闡釋。康有為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闡釋是其進行董仲舒思想研究和把握的題中應有之義。他認為,董仲舒在對《春秋公羊傳》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闡釋過程中,不僅揭示出了孔子的改制思想,闡明了孔子改制的深層原因,也揭示出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將孔子思想的根本之道進行了深入的發掘。在人性學說中,康有為對董仲舒關于人性是天生的,而善是后天的看法較為贊賞,認為董仲舒的人性學說最為精致和完備。在歷史觀中,康有為認為,“惟董子乃盡聞三統”,看出了孔子所托夏、商、周三代以言大義的做法,“夏、殷、周為三統,皆孔子所托”。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推崇與其所處的特定時代和歷史背景息息相關,在對變法維新和托古改制求索的過程中,董仲舒的思想與康有為化解時代危機和社會現實問題的想法相互契合。
[關鍵詞]康有為;董仲舒;《春秋》;春秋學
[中圖分類號]B25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284(2017)10-0144-04
“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語出《春秋董氏學》,是康有為對董仲舒的總體評價和基本態度。在對中國本土文化源流進行考辨的過程中,康有為不僅致力于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厘定和探尋,得出了“‘六經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學”、孔子乃“大地教主”、孔子作《春秋》是為托古改制等結論,而且對先秦以后承續孔子思想的諸多人物均予以梳理和審視。在承續孔子思想的先秦后學中,康有為對董仲舒推崇有加,將其看作是“漢世第一純儒”。這不僅緣于董仲舒在孔門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對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至精闡發,也緣于董仲舒春秋學的宗旨要義為康有為變法維新的主張提供了理論參考和思想來源。
一、康有為對董仲舒思想來源及其地位的研究與闡釋
對某一思想家、哲學家的思想體系進行研究和把握的前提是理清和辨別其思想的主要來源。康有為對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康有為看來,作為春秋公羊學家的董仲舒,其思想淵源于孔子,是孔子之學特別是《春秋》改制之學的直接承續者和闡揚者。對此,康有為斷言:“董子為漢世第一純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當新王之說。”[1]18在康有為看來,董仲舒之所以成為“漢世第一純儒”,其緣于董仲舒秉持和承續孔子改制、《春秋》“新王”的思想。他是以孔子作《春秋》以言改制為視角對董仲舒思想進行審視的。沿著上述思路,康有為對董仲舒承續孔子思想的具體脈絡和其在孔門中的地位進行了系統梳理。
在分析董仲舒承續孔子思想的具體脈絡中,康有為一方面宣稱:“文王之文傳諸孔子,孔子之文傳諸董仲舒”[1]122,另一方面又認為:“董子只傳荀子之學”。這就是說,在他看來,董仲舒通過兩種方式沿襲了孔子的思想:一種是直接得到孔子思想的真傳,另一種是通過對荀子思想的沿襲間接地承續了孔子的思想。在論證和闡釋第一種觀點時,康有為指出:“《春秋》之意,全在口說。口說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1]151孔子《春秋》中所體現出的微言大義,是通過口說而傳授給后世的,記載孔子口說內容最為完整的是《春秋公羊傳》,而對春秋公羊之學理解至精、至深的莫過于董仲舒。此外,康有為還提出:“董子曾見河間獻王,豈有古經而董子不知者乎?”[1]188就董仲舒曾拜謁獻王劉德這一論點來看,足以證明董仲舒直接接觸和閱讀了先秦古籍經書,因此,他涉獵廣泛,學識廣博,無所不知。對于董仲舒直接得孔子之學的說法,并不是康有為的一面之詞,而是出自王充之口,康有為說道:“《論衡》謂文王之文傳于孔子,孔子之文傳仲舒。”[1]189綜合來看,康有為認為,董仲舒對孔子思想的繼承是沿著孔子口說傳授——《春秋公羊傳》記載孔子口說傳授——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學這一邏輯展開的。在對第二種觀點,即“董子只傳荀子之學”進行論證和闡釋時,康有為認為,在孔子之后,《春秋》雖得以流傳,但孔門后學對《春秋》的把握和闡釋都沒能言盡孔子之意。例如,在“百家皆孔子之學”的前提下,墨子雖然承續了《春秋》,但只是“偷得半部”。在墨子之后,康有為又指出:“孟傳《公羊》,多發大義。”[1]151作為孔門后學的孟子,只是發現了孔子《春秋》中所蘊含的思想,但并未進行闡發。不僅孟子對孔子《春秋》進行了傳承與闡釋,與其并列的另一派代表人物荀子也傳承了孔子的《春秋》之學,指出:“傳《詩》則申公,《禮》則東海孟公,《春秋》則胡母生,皆荀子所傳。”[1]182這表明,在戰國時,承續孔子《春秋》的是孟子與荀子。對于孟子與荀子之后身處漢代的董仲舒而言,他所得孔子思想只是來自荀子,康有為說:“董子只傳荀子之學,不傳孟子,可見荀子之后盛,孟子之后微。”[1]206在康有為看來,“讀《深察名號篇》,知董子傳荀子之學,不傳孟子之學。”[1]188董仲舒《深察名號篇》中的“辨物之理,以正其名”與荀子《正名篇》中的“制名以指實”觀點一致,都是涉及名實關系、禮制規格的著作。此外,“禮學重師法,自荀子出,漢儒家法本此”[1]184。在傳孔子《春秋》之學的孟子與荀子中,康有為認為,董仲舒的思想接近于荀子,所以將其定位為荀子之后學。
無論是直接得到孔子思想的真傳還是間接通過荀子對于孔子的思想進行承續,出于“‘六經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學”的觀點,康有為將董仲舒界定為孔子之后學、孔門中人的事實,毋庸置疑。不僅如此,康有為賦予了董仲舒在孔門中極為重要的地位,指出:“康先生論十哲當以顏子、曾子、有子、子游、子夏、子張、子思、孟子、荀子、董子居首,蓋孔門論功不論德也。”[1]229根據上述康有為對孔門“十哲”的界定可以看出,除董仲舒之外,其余“九哲”大多都是孔子親自口說授課的嫡傳弟子或與孔子生活年代距離較近的后學。只有董仲舒既不是孔子親自口說授課的嫡傳弟子,又不是與孔子生活年代相距較近的后學。但康有為卻將董仲舒與其余“九哲”相并列,體現了他對董仲舒在孔門中傳承孔子思想功勞的高度認同和充分肯定。不僅如此,他還再三強調,董仲舒對于孔子思想的闡發超過孟子和荀子,并斷言:“董子微言大義,過于孟、荀”[1]188,“董子窮理過于荀子,荀子過于孟子”[1]188,“《繁露》傳先師口說,尊于荀、孟”[1]187,“董子傳微言過于孟子,傳大義過于荀子”[1]204。康有為認為,孟子只是看到了《春秋》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闡發,而董仲舒不僅發現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同時也將其闡釋得淋漓盡致。董仲舒體認和闡釋了孔子思想中所深隱的微言大義超過孟、荀。在康有為看來,董仲舒不僅在孔門“十哲”中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在其所處的漢代也是如此。康有為一再宣稱:“孔子微言大義,至董子始敢發揮,漢朝孔學已一統,人皆知尊孔子也”[1]188;“漢之文章,董仲舒為義理之宗,賈長沙為奏議之宗,司馬相如為詞賦之宗”[1]242。與后世被奉為“集諸儒之大成者也”的朱熹相比,董仲舒更是表現突出,康有為指出:“董子解經,能通天人。朱子專解人事,故朱子只得孔子一半。”[1]204在學術研究領域,康有為不僅認為:“董子為《春秋》宗,所發新王改制之非常異義及諸微言大義,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圣,猶未傳之,而董子乃知之”[1]357,并且把董仲舒在春秋學上的貢獻等同于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在幾何學上的貢獻,“言《春秋》以董子為宗,則學《春秋》例亦以董子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歐幾里得之于幾何也”[1]323。
因此,在對孔子《春秋》微言大義的發揮上,康有為賦予了董仲舒在孔門中極高的地位,并對其作了如下的總體性評價:
“至于漢世,博士傳‘五經之口說,皆孔門大義微言,而董子尤集其大成。劉向以為伊、呂無以加。《論衡》所謂:孔子之文傳于仲舒。《春秋緯》謂: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于天,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朱子極推其醇粹。”[1]416
“董子接先秦老師之緒,盡得口說,《公》、《榖》之外,兼通‘五經,蓋孔子之大道在是。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全體不可得而見,而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后一人哉!”[1]416
二、康有為對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與闡釋
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時代。面對化解漢王朝內外沖突,謀求思想、政治大一統的社會現實,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傳》為詮釋文本,探賾文本背后深隱的微言大義,為國家政治的大一統尋找文本依據,以此化解時代的沖突與危機。康有為大體從春秋公羊學、人性說、歷史觀等三個方面對董仲舒的思想進行了闡發和介紹。
(一)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研究與闡釋
康有為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闡釋是其進行董仲舒思想研究和把握的題中應有之義。孔子作《春秋》,但并未將其全部思想寫入書中,他通過口說的方式將要表達的深隱之意講授給弟子們,即所謂的《春秋》微言大義。《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左傳》盡管詳細記錄了《春秋》的基本內容,但并沒有明確闡發孔子所傳授的微言大義。董仲舒專治春秋公羊學,系統發揮了孔子在《春秋》中“借事名義”之“微言”和“正名為本”之“大義”,其學、其言都是圍繞孔子《春秋》中的改制思想而展開的。《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體現了董仲舒對孔子《春秋》改制思想的繼承與闡揚。康有為通過對《春秋繁露》的閱讀和研究,闡釋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思想。他說:“《公羊》、《繁露》所以宜專信者,為孔子改制之說也”。[1]18“故《春秋》專為改制而作。然何邵公雖存此說,亦難征信,幸有董子之說,發明此義,俾《大孔會典》、《大孔通禮》、《大孔律例》于二千年之后,猶得著其崖略。董子醇儒,豈能誕謬。”[1]365康有為認為:“《春秋繁露》四本,若聰敏之士,得傳授而提要鉤元,數日可通改制之大義。”[1]19在他看來,聰明敏銳之士在傳習《春秋繁露》這部著作時,只要深刻領略到書中的主旨之言,就能夠在幾日內通曉孔子改制的微言大義。康有為認為,《春秋繁露》中的《俞序》篇是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學的總綱要旨,它不僅揭示出了孔子的改制思想,更闡明了孔子改制的深層原因。在康有為看來,“《春秋》體天之微,難知難讀,董子明其托之事以明其空言,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一國以容天下,而后知素王改制,一統天下,《春秋》乃可讀”[1]310。董仲舒在《俞序》篇中,明曉了《春秋》中“難知難讀”的微言大義,得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根本原因在于“疾時世之不仁”,所以才借《春秋》明王道、倡愛人。康有為指出,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學就在于體認到了孔子假托敘事之名以正人倫的本意,闡揚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故《尸子》謂:孔子貴仁。孔子立教宗旨在此,雖孟、荀未能發之,賴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也。”[1]375這就是說,董仲舒在對《春秋公羊傳》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闡釋過程中,揭示出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將孔子思想的根本之道進行了深入發掘。
(二)對董仲舒人性說的研究與闡釋
董仲舒言孔子《春秋》改制之說,目的在于為漢朝謀求思想、政治的大一統尋找歷史根據。要實現思想、政治的大一統,對人的王道教化是不可或缺的。人性說是董仲舒為實現大一統而從事王道教化的理論基礎。康有為對董仲舒的人性學說推崇有加,斷言:“董子‘性之名非生焉,與告子同義。又謂‘性者,質也,又與《孝經緯》‘性者,生之質也同,多是孔門嫡傳口說。”[1]203康有為認為,董仲舒把人性看作是人生來具有的自然品質,在這一觀點上,與告子的“生之謂性也”論述是一致的。董仲舒所謂“性者、質也”,即人的本性就是天生所具有的自然品質,與《孝經緯》中“性者,生之質也”的說法相同,康有為將這些觀點看作是孔子嫡傳弟子口說傳授的內容。董仲舒“性者,質也”的觀點,沒有將善與性等同起來。董仲舒認為,人性的本質不應在人與禽獸間的比較而得來,人性的善也不能通過與禽獸之性的對比而界定出來,因為人性是高于獸性的。董仲舒通過禾與米的關系比喻人性與性善的關系,來說明人性非善,但善是出于人性中的,亦即認為人性是先天的,而善是后天的。康有為對董仲舒關于人性是天生的,而善是后天的看法較為贊賞,說道:“《孝經緯》、《繁露》皆言‘性者,生之質也,言性以董子為至。”[1]173“董子言生之謂性,是鐵板注腳。”[1]184康有為對董仲舒人性說的認同和肯定與他早年對告子和莊子的推崇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董仲舒的人性說與告子和莊子的觀點較為接近,所以,康有為對董仲舒的人性學說關注較多。不僅如此,康有為看到了董仲舒所講的人性是圍繞中民之性展開的,指出:“董子言性,為中人言之也,故孟子言‘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不盡言性善。”[1]174董仲舒將人性區分了上中下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以名性”的,因為二者是不可改變的且不是普遍的人性,只有中民之性是普遍的。與圣人之性的絕對善和斗筲之性的絕對惡不同,中民之性是可善可惡、善惡相混的,如果使其向善而為,就必須依靠王道教化。康有為看到了董仲舒所說的,關于中民之性可以通過王道教化使之向善而改變的可能,體認到了通過激發人性而為實現近代社會救亡圖存的可能路徑。在康有為所處的人文語境中,哲學家們用對人性的苦與樂問題探討取代了對人性的善與惡問題的探討。康有為秉持“求樂免苦”的人性說,把追求快樂看作是人的本性,反對“絕類逃倫而獨其樂”,所以他將“求樂免苦”推及國家、社會上,鼓勵人們通過發揚“不忍人之心”來實現“相與共其樂”。可以說,康有為通過激發人們“求樂免苦”“不忍人之心”的本性來實現救亡圖存與董仲舒通過王道教化來使中民之性向善的做法是相互契合的。
(三)對董仲舒歷史觀的研究與闡釋
“三統”“三正”說是董仲舒歷史觀的核心內容。董仲舒依據《春秋公羊傳》中的“三世異辭”說,提出了“三統”“三正”說。“三統”“三正”說圍繞夏、商、周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演變而推出歷史“三而復”的規律性改變。董仲舒認為,新王朝的出現,其在服色、正朔上必有改變,這就是所說的“新王改制”。董仲舒“三統”“三正”說的實質在于論證王者只能改制,而不能改變歷史“三而復”之道,即“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歷史的演進規則就是“三統”“三正”的不斷交替、循環。康有為認為,“惟董子乃盡聞三統”,看出了孔子所托夏、商、周三代以言大義的做法,“夏、殷、周為三統,皆孔子所托。《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發之最詳”[1]150。他認為,董仲舒對于“三統”的含義理解最為深刻,闡述最為詳細。進而,康有為說:“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統,又作《易》以言變通,黑白子丑相反皆可行,進退消息變通而后可久。”[1]81“《春秋》為改制之書,包括天人,而禮尤其改制之著者。故通乎《春秋》,而禮在所不言矣。孔子之文傳于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孔門如曾子、子夏、子游、子服、景伯,于小斂之東西方,立嫡之或子或孫,各持一義,尚未能折中。至于董子,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豈徒可止禮家之訟哉?其單詞片義,皆窮極元始,得圣人之意,蓋皆先師口說之傳,非江都所能知也,不過薈萃多,而折中當耳。”[1]330-331康有為認為,董仲舒對于孔子“三統”“三正”大義的理解,深入到了孔子對于禮制的看法,即歷史雖不斷演進變化,但人倫、政治、道德、教化、習俗之禮是不變的。董仲舒“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的論述得出的必定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結論,這當然是康有為所反對的。但是康有為在董仲舒對于“三統”的理解中,沒有糾結于對其歷史循環論的批判和反對,而是看到了董仲舒“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即董仲舒對歷史變化本身的看法。
三、結語
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推崇與其所處的特定時代和歷史背景息息相關。從康有為早期思想的核心主題來看,康有為將孔子看作是改制“鼻祖”和“大地教主”,孔子之后一定有承續其思想的思想家來發現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義,闡揚孔子改制的舉措,董仲舒便是這位思想家,因為只有“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1]307。從康有為變法維新所依托的文本來看,他借發揮《春秋公羊學》的改制思想為其變法維新尋找文本依據,而這樣必然將專治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推向較高的地位。從現實的人文語境看,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推崇有其變革政治現實的指向性,是為變法維新所做的理論準備。因此,在康有為的視界中,董仲舒被列為孔門中擁有極高位置的“十哲”之一。
[參考文獻]
[1]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徐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