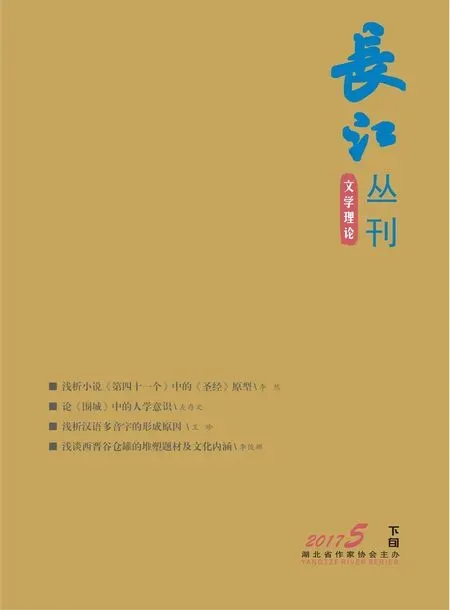文化領導權與蘇東劇變
王晨陽
文化領導權與蘇東劇變
王晨陽
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在當今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熱議,受到了文化學、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高度重視。這篇文章將對東西方社會結構進行具體而深入分析,葛蘭西將市民社會凸顯出來,由于東西方市民社會地位的不同,從而導致東西方在選擇革命道路上出現了差異。
文化領導權 市民社會 知識分子
安東尼奧…葛蘭西(Аntоniо Grаmsci,1891—1937)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意大利的創始人和早期領袖之一。他主要活動于20世紀社會大動蕩的20、30 年代,他那短暫而輝煌的一生是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最好詮釋。在1926年葛蘭西深陷監獄但他并沒有因此停止在理論上的思考,他歷盡艱辛寫下了長達2844頁的書稿和論文,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獄中札記》,在這部書中他進行理論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在此書中涉及了極為廣泛的理論問題,如歷史唯物主義和許多其他的哲學問題,意大利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知識分子等問題,以及工人階級政黨、階級和階級斗爭、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等問題。葛蘭西在監獄中,創立了“文化霸權”、“市民社會”、“陣地戰”、“知識分子”等一系列知名理論,成為了身陷重圍的無產階級的航行標和明亮的燈塔,照亮了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命志士前進的道路。
一、市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的凸顯



市民社會和文化領導權構成了葛蘭西的西方革命觀的核心,市民社會在東西方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的不同直接影響了東西方革命道路的不同。市民社會并不是葛蘭西的獨創,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有其獨特之處。我們知道中世紀末期的城關市民是市民社會的最初階段,在那時他們以簡單的手工業加工和商業貿易活動為主業,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關市民也就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在階級觀念相對淡化的今天,市民社會又與公民社會又近乎相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到,市民社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與物質生產領域或者經濟領域密切相關,因此,當我們在談到市民社會時,它所隱含的因素就是“四大關系”即財產關系、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關系,它并不具備政治上的含義。市民社會與國家到底具有什么樣的關系呢?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國家觀念的外化,國家產生市民社會。而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的主賓倒置法顛倒了黑格爾的國家觀,認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1],“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2]。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在葛蘭西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認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國家。在社會中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國家功能的發揮,最終在政治上也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并同時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社會的強制機構。馬克思與黑格爾在國家觀上的對立實質上反映的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兩種世界觀在國家形成理論上的根本對立。葛蘭西最大的突破就在于他并沒有局限于唯物與唯心這種對立的二分中,而是隨著這種突破,市民社會從社會存在領域上升到上層建筑領域,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相并列共同從屬于上層建筑領域。市民社會實質上也因此成為了政治活動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緩沖地帶,“市民社會不再單純代表傳統的經濟活動領域,而代表著從經濟領域中獨立出來與政治領域相并列的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它既包括政黨、工會、學校、教會等民間社會組織所代表的社會輿論領域,也包括報刊、雜志、新聞媒介、學術團體等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領域。”[2]這就決定了國家行使職能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以往國家傳統的統治方式已經不再適應于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也要求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方式只能是領導而不是統治。葛蘭西把領導和統治區分開來,并進一步強調了領導的作用。葛蘭西認為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市民社會是一個歷史上的范疇,它是商品經濟伴隨著生產力發展到一個特定階段的產物,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葛蘭西認為,東方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商品經濟比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所以東方社會沒有形成獨立的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在西方國家發展卻相對完備且在現實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東西方市民社會地位的相異的決定了東西方國家的性質和差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各自革命道路的不同。正在此基礎上,葛蘭西提出了與馬克思不同的暴力革命觀即西方革命觀。爭奪市民社會的領導權是西方革命觀的核心,而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實質上就是文化領導權,因此爭奪文化領導權就成為了西方革命的核心。“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初生而未形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調整了的相互關系。假使國家開始動搖,市民社會這個堅固的結構立即出面。”[3]我們從這段論述中能看到在一個市民社會相對完備的國家中,對市民社會的領導實質上占據著更加重要的地位,市民社會成為國家更具內核性的因素,并且思想意識形態一旦占據人的頭腦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就是思想的“物質性”甚至比物質更加堅固的一面。思想意識形態對人頭腦的控制,是文化領導權最重要的一面。
葛蘭西認為,誰能掌控文化領導權誰就有可能贏得并鞏固政權。一個社會集團只有首先奪取了文化領導權,即在精神文化領域、意識形態上取得“霸權”地位,才能最終掌控政權。西方無產階級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客觀上革命條件的不成熟,而是在于工人運動不能強有力的抵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滲透和控制。葛蘭西認識到了文化領導權在現代社會中的所發揮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在一個市民社會相對成熟的國家里,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與統治階級爭作堅決的斗爭去奪文化領導權。對于統治階級本身來說,市民社會和文化領導權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在一個通過暴力革命取得統治地位的國家,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統治階級往往忽視獲取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我認為這就是東歐乃至蘇聯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
二、蘇東劇變的啟示
英國在1825年爆發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次經濟危機,這證明了馬克思所預測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是正確的,資本主義國家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都對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了深刻的社會危機,但出人意料的是,不管經濟危機的破壞性有多大,沒有一次能夠威脅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霸權統治地位。葛蘭西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深受災難而沒有崩潰,根本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通過“文化霸權”對“市民社會”的控制,而文化霸權歸根結底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領導的權利也就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西方文化主要維系的自由、民主、平等能夠追溯到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立國之本,在資產階級獲得統治前及穩固統治后,貫穿于其文化始終的基本精神始終沒變,圍繞這一自由、民主、平等的主線來進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用了巨大的艱辛努力去奪取文化領導權以及在文化上的統治,資產階級在其歷史長河中已經形成其文化的靈魂,并依靠它獲得了人民群眾的心。正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反觀無產階級,從爆發工人運動至今,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穩固的具有普適性的文化內核,更不用說將無產階級的革命理念深入大眾的內心。因此,在整個歷史大背景下資產階級就牢牢的掌控著文化領導權。這個外在的歷史背景就構成了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受挫的客觀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對自身文化的建構僅僅邁出了一小步,相對于奪取葛蘭西所認為的文化領導權來說,無產階級的文化更是具有后天發展的嚴重不足。 奪取文化領導權,很多人往往把重點放在了人身上,反而忽視了文化本身的重要性。在葛蘭西看來,文化領導權的根本特征是一種“軟權力”的“同意”,“‘同意’是對某種社會政治秩序、某一種政治決策、某種政治行為或某一領導者的認可、贊同、或支持。”[4]很明顯,這種“同意”具有自發的非強制性,它比那些外在的強制暴力更具統治力。

東歐劇變以及蘇聯的解體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國家領導人對文化領導權的忽視和誤解。不論是蘇聯還是東歐各國社會經濟都相對落后,甚至有許多國家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壯大到足以推翻本國的封建統治,還沒有堅固的實力去奪取國家的政權,更不能去奪取在文化上的領導權。蘇軍的鐵犁鏟除的只能是封建勢力的外部工事,卻忽視了潛藏在內部城堡中的毒瘤,當蘇東領導人忙于經濟建設時,毒素開始擴散,最終蔓延至整個地區,時刻準備癱瘓整個國家。因此,從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文化傳統上看,封建反動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仍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市場。其次西方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演變,從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建立開始時,西方國家自始至終就從來沒有放棄或遺漏過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深入滲透,占據著對意識形態的領導。這種對意識形態的占據,對于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導權尚未建立的初生時期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但蘇東恰恰又忽視了文化領導權,這也是導致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應該認識到,這些都是外在的客觀原因,不足以主導整個局面的發展。 其根本原因就是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在決策上的嚴重失誤。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以后,領導人將國家的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這符合當時的特殊國情,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在不斷的形成,市民社會的地位在不斷凸顯,很顯然這一點又被黨的領導人忽視了。經濟在不斷的發展但其他社會事務卻相對的滯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其有限,一旦經濟的發展遇到瓶頸,即使稍遇挫折,也會造成社會的極大動蕩。經濟斗爭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相對局限性,而意識形態有時卻發揮著物質性的政治力量,這也是資產階級政權在飽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轟擊下毅然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首先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內的一些領導人對文化領導權的占據缺乏重視,其次黨內的領導人對文化領導權有極大誤解和看法。他們不能理解占據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葛蘭西認為“文化是一個人內心的組織和陶冶,一種同人們自身的個性的妥協,文化是達到一種更高的自覺境界,人們借助它懂得自己的歷史和價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權力和義務。”[5]人和動物的一個最大區別就在于人是文化的動物,文化塑造了人內心中的人性的部分,一個人價值的依托和歸宿就是文化,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領導權的“同意”這一根本特征。徐崇溫說:“群眾信奉不信奉一種意識形態是思維方式的合理性或真實性的真正的批判和檢驗。”首先一種文化之所以被稱之為文化它必須是通過了人民群眾自覺的“同意”,其次是人民群眾對其文化的自覺信奉。當人們開始自覺地信奉一種文化的時候,文化的穩定性與物質性的力量就能顯現出來。因此,統治階級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把重心放在創造真正符合大眾需要的文化上,而非利用統治權力來鉗制人民的思想。蘇共和東歐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將黨的領導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建國初期這種措施確實有其必要性。但這種外在的“全方位的領導”卻給自身造成一種牢牢掌控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假象,僅僅依靠制度上的強制措施及大眾傳播媒介形成一種表層的霸權文化,這完全無法掩蓋人與社會深層的根本的內核性的缺失。人民大眾與統治階級主導文化的斷裂將整個社會推入到了一個相當危險的境地,面對這種文化窘境也就不難理解東歐各國共產黨在短期內紛紛喪失政權。實際上我們會發現,不僅僅是人民群眾會對社會主義缺乏認同感,就連共產黨內的一些重要領導人的社會主義信念也不夠堅定,這也就是為什么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以及眾多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會自己主動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真正原因。統治階級的主導意識形態脆弱到不堪一擊,這種近乎專制的文化統治策略不僅扼殺了文化的豐富多樣性,也閹割了自身的生命力,將文化的領導變成了粗暴的統治,對統治階級文化的這種心照不宣的不接受,只需要一根很小的導火索就足以結束一切。因此,社會主義的生命必須以維系文化的建設與文化領導權的占據為根本。
三、當今文化知識分子使命探究
意大利文”еgеmоniа”翻譯為“文化領導權”,這個詞所表達的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兩個方面,“文化領導權”指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領導權,現階段對于葛蘭西思想的研究人們認為其重要于文化領導權。當然這與當今的國際局勢緊密相關,不可否認的是對統治階級內部文化領導權的忽視確有舍本求末之嫌。在東歐與蘇聯革命的教訓之下,應該引起世人的警醒。卡爾…利維認為在葛蘭西那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是一種對意識形態領域即文化的啟蒙和拓展。因此,在葛蘭西的內心深處,革命的行動和革命的政治實踐并不是以奪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為最終目的的,他認為是要通過革命對人民群眾進行啟蒙運動,也就是創造嶄新的新文化,創造新文明,創造新人類。 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仍有不足,沒有真正的達到文化發展的大發展大繁榮,文化建設不全面、不牢固、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葛蘭西所提出的“市民社會”也在不斷地日益顯現和成熟。文化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顯著。通過一系列的宣傳,馬克思主義滲入了社會的各個層面,黨領導的涉及生產生活的各個重要部門。葛蘭西認為:“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錯誤便是在知識分子的本質上去尋求區別的標準,而非從關系體系的整體中去尋找,這些活動(以及體現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團體)正是以此在社會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6],在此我們能看到,對于知識分子的界定標準,不是在掌握知識的多少,而是在于相對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的位置及其他所要擔負的責任和作用。一方面人民大眾需要知識分子的引導,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也應該融入大眾,從人民大眾中不斷充實武裝自己。知識分子不僅需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的,積極地介入現實社會,深入大眾的現實生活中,而且還需了解大眾的精神疾苦,探索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據人民群眾的需要去創造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食糧。其次我國的知識分子要勇于擔當傳播文化知識先鋒,這是知識分子不容推卸的責任。知識分子不能棄人民大眾而不顧,自己卻沉溺于學術研究之中,不能不進行社會實踐,而在書房中享樂。最后“學科邊界的消解和公共領域對知識分子的呼喚,要求知識分子從自己狹窄的專業領域走向廣闊的公共領域,成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或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7]可見,文化領導權的獲得對知識分子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但知識分子也只有承擔這些職責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從文化的批判到文化的創新再到文化的傳播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構成了文化領導權的基礎性因素。
文化滿足的是人的精神性和超越性的需求,文化領導的基礎是人民大眾基于自身需要的一種認可,所以它必須以人為本,在文化建設中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文化領導權的獲得也只能從人本身出發。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衣俊卿,等.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
[3]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4]王曉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5]葛蘭西,李鵬程.葛蘭西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孫晶.文化霸權理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7]和磊.葛蘭西與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