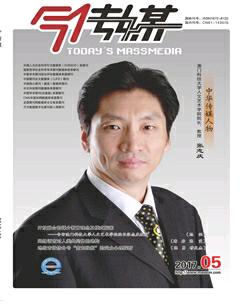淺析《布達佩斯大飯店》的隱喻意味
郭萌
摘 要:作為美國主流體制中的獨立電影導演,韋斯·安德森幾乎參與到自己電影作品攝制的各個層面,而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幾乎涵蓋了其所有鮮明的創作個性,雖然在視聽藝術上延續了以往的“形式主義”,但在敘事層面上卻打破了傳統的敘事結構,將歐洲古老的歷史、文化、藝術、美學等融入在具有好萊塢娛樂精神的喜劇情節之下,這種具有濃厚隱喻意味的敘事方式使得這部影片極具個人特色。
關鍵詞:布達佩斯大飯店;韋斯·安德森;隱喻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5-0109-02
怪才導演韋斯·安德森對歷史、文學、美術、音樂都頗有鉆研,在《布達佩斯大飯店》中,導演將其“作者導演”的身份展示的美妙絕倫。2015年由其自編自導的影片《布達佩斯大飯店》獲得了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服裝設計、最佳藝術指導,同時安德森也因為本片獲得了最佳導演提名的殊榮。《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故事創作以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說《昨日的世界》為藍本,力求再現茨威格筆下歐洲傳統文明的衰亡史,通過講述上個世紀歐洲的一家大飯店的主管和門童的傳奇經歷,映射出歐洲將近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變幻。導演將對于歐洲傳統文明多層次的展示和闡釋隱藏于極具戲劇性的情節之下,將靜心安排的隱喻隱藏在碎片化的故事敘述當中,頗具美學風格。
作為一種修辭手段,隱喻最早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而現在隱喻不僅是文學著作里的常用手法,也是現代電影中最常用到的表現手段,這種獨特的表現技巧使得影片整體在視覺感官上給觀眾帶來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在影片主題的展現上也更加深刻。《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多層次隱喻為本片賦予了深刻的含義,在這里,空間、器物等不只是電影的場景背景與道具,更具有了隱喻性、線索性,反映了人物的關系與劇情的發展。
一、空間隱喻
空間隱喻是隱喻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在電影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電影作為一種視覺藝術,通常會利用空間作為電影的感染形式,空間不再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電影中的故事劇情發生的鋪墊與電影中人物關系與社會關系的反映[1]。在對一部電影進行解讀和分析時我們會發現,場景空間的布局和設計其實是對影片主題的一種再創造,在影片各個元素的構成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布達佩斯大飯店》中的不同人物出于對不同欲望的追求,反復穿梭在各式各樣的空間中。電影的主人公古斯塔夫和其門童零穿梭于飯店大廳,為四面八方而來的客人服務;德米特里派來的殺手喬普林騎著摩托車不停地穿梭在城市之中,為追名逐利、尋找名畫奔波;古斯塔夫與零在遭到喬普林的追殺時,皚皚白雪中夾雜著幾支干枯的枝丫,三人在白茫茫一片大地中奔馳,這種大與小的視覺沖擊力極為震撼。在韋斯·安德森眼中,即使靜止的畫面也會因為連接著不同的空間而顯得別出心裁。
不得不說,安德森的對稱式構圖極富盛名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中的酒店大門、樓梯、火車、監獄等建筑的設計都遵循了對稱式構圖原則。古斯塔夫越獄的橋段是影片中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段,帶有節奏感的音樂伴隨著這種本該是及其冒險的動作反而有點喜劇色彩。古斯塔夫和獄友從監獄里逃出來,在不同的房間中來回穿梭,一個空間到下一個空間,像通往未知的世界一樣。逃獄過程中一行人忽然遇到獄警這段戲設計的也極具戲劇性,導演把出后安排在一個可以隨時移動的地板上,然而更加荒誕的是,只要掀開這塊地板,逃獄者俯視的角度正好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獄警。正在圍成一圈打麻將的獄警與這群逃獄者四目相對,面面相覷,一個“回”字形的構圖恰到好處的把這種戲劇性完美的呈現給觀眾。安德森在這里再現了《肖申克的救贖》中越獄的橋段,其實這種曲折的越獄過程,也正是古斯塔夫從入獄到出獄,從限制到解放的象征,同時也形象生動表達出那個時期的歐洲人在傳統與現代交疊過程中的彷徨、無奈與不安。
二、器物隱喻
器物,本是來源于現實之中,是戲劇賦予了它們獨特的魅力,在不同的電影中,導演安排的各種器物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它們有時作為線索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有時可以作為點綴深化影片主題,但其實不管哪種器物,都是作為一種特殊的造型在影片中顯現出來,在這里器物拋開了固有的實用功能,而是潛移默化中添加了一種審美和美學價值。
在《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故事敘述中,貫穿整體的是導演安排的名畫《蘋果少年》遺失案,而這副所謂的名畫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本片一個重要的器物。這幅畫是歐洲貴族D夫人的遺產,古斯塔夫憑借自己無微不至的服務贏得了D夫人的信賴和傾慕,并得到了這副名畫的繼承權。而在這個關鍵時刻,D夫人的兒子卻對這副名畫的繼承權產生了疑問,在這個只關心財富,貪婪至極的人看來,《蘋果少年》的繼承權無論如何都應該屬于他,于是為了拿到這幅畫,他架空法律,為了得到財產不惜對律師行刺,謀殺證人。
古斯塔夫曾在過境列車上對零說,我要抱著這幅畫死掉,因為我跟蘋果男孩很像。 其實這不是古斯塔夫隨口說的玩笑話,而是導演隱晦安排的故事前奏,就連古斯塔夫駐足在《蘋果男孩》面前的發式和著裝都與“蘋果男孩”有幾分相似。但是轉念之間他又改口說:“我打算賣掉這幅畫。”這種即便擁有財富但卻會因為巨額財富而感到心驚膽戰,把當時歐洲人處于傳統與現代更迭時期的憂心忡忡變現的尤為精彩。
無疑,韋斯·安德森是一個對影片細節極度在意的“怪胎”導演,然而正是這些精致的細節、精心的器物設計和安排才給《布達佩斯大飯店》帶來了更加不凡的魅力。
三、文化隱喻
1.對茨威格人格與信仰的致敬。由于《布達佩斯大飯店》是以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說《昨日的世界》為故事藍本,所以在影片結尾,韋斯安德森專門安排了一個單獨的字幕畫面向其表示感謝和致敬。在柏林電影節的首映儀式上,導演韋斯·安德森更是戲稱“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在剽竊原著”[2]。 1881年,茨威格出生于一個闊綽的猶太人家庭,他的父母親都屬于奧地利上層社會階層的人群,良好的成長環境讓他衣食無憂,生活富裕,并且受到了教育、文化、藝術上的熏陶。十分具有才氣的他在成名以后開始游歷各國,安德森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也正是以他下榻的飯店為創作靈感,將片中所講述的故事背景設置在虛構的一間門庭若市的大飯店中。這個飯店外表富麗堂皇,各個部門之間遵循著一定的規矩,有條不紊的運作著。這個具有錦繡前程的大飯店其實是20世紀30年代傳統歐洲文明的縮影和象征。
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三位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有茨威格的影子,分別是青年作家、老年作家和古斯塔夫,他們三位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茨威格的生平。影片敘事中年輕作家在離開布達佩斯大飯店后便坐船去南美進行治療,自此開始了在國外居無定所的漂流,其實這也是茨威格親身經歷的真實寫照。1934年他遭到了納粹分子的驅逐,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鄉奧地利,輾轉流亡于英國和美國,最后定居巴西。而老年作家的墓志銘上的文字——“紀念我們國家的寶藏”,則形象概括了茨威格作為“天才作家”的巨大人生成就以及其為后世留下來的巨大財富。而電影的主人公古斯塔夫先生則映射了作家茨威格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崇高人格和信仰。影片結尾,他為了維護自身尊嚴和保護零而被敵人射殺,也從側面暗示了茨威格人生的悲慘結局——1942 年2月22 日晚,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在寓所內自殺,并在遺書中寫道,“我的母語世界已經沉淪并拋棄了我”,“而我的精神家園歐洲亦已自取滅亡” ,這是茨威格作為歐洲知識分子對于心靈自由的捍衛。而韋斯·安德森在這部影片中也恰好把對茨威格的懷念與致敬隱藏在戲謔的情節里,并流露于每一幀鏡頭。
2.對逝去的歐洲文明的緬懷與反思。作為一位個人風格辨識度極高的作者導演,韋斯·安德森的電影無論是處女作《瓶裝火箭》,還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月升王國》等都從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導演對于家庭問題和個體成長問題的關注。在以往的影片中,我們只能看到導演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精彩絕倫的小故事,而對于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卻沒有太過于清晰的認知。但是在《布達佩斯大飯店》中,我們卻能明顯的感受到導演在著力復原故事發生的大的時代背景——20 世紀30年代的歐洲社會,這也正是茨威格小說中曾經所描繪的“二戰”前的歐洲社會。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戰剛結束不久,這時納粹剛剛覺醒,歐洲大陸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在這種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下,曾經門庭若市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也難逃厄運,昔日的大飯店早已不再。為數不多的幾個老顧客每天來來回回的打著照面,早已熟悉了彼此,他們表面看上去安逸平靜,若無其事,但其實是這樣的時間荒野把他們從搖籃帶到了墳墓。年邁的零和作家面對面坐著,將曾經發生的故事娓娓道來,空蕩的飯店大廳把兩個人的孤獨拉的更長了。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工業化勢不可擋的侵入,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以前那種人文關懷,極富秩序化的傳統開始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快餐化的東西。歐洲這塊文化底蘊深厚的土地被鐵蹄蹂躪,理念與現實的分離使得歐洲傳統文明消亡速度更加迅速。科技的進步,使得人與人的相處完全被媒體和電子科技所替代,相比起起過去神話、史詩、童話的口口相傳,急速發展的現代世界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隨著實用關懷的消失,歐洲文化的精神支柱也就倒塌了。雖然《布達佩斯大飯店》力圖再現舊時歐洲文明的秩序、藝術等等,但其實這一切都是一種優雅的幻象,兩次工業革命推動了西方工業的飛速發展,經濟的發展使得理性、集權等主流意識形態崛起,人們已經不再滿足于過去那種有安全感的黃金時代,那種貴族式的、儀式般的傳統歐洲文明早已成為處于從屬地位的“他者”。
韋斯·安德森通過《布達佩斯大飯店》把茨威格對于這種歐洲傳統文化沒落的現實的惋惜赤裸裸的展現給觀眾看,激起太多感慨和反思。
四、結 語
《布達佩斯大飯店》是韋斯·安德森的巔峰之作,從另外一方面來講,也是他導演生涯的突破。跟他以往的電影作品相比較而言,這部影片不僅僅局限于以往熱衷的家庭和成長主題,而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導演站在主流立場以外對歐洲文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冷靜探討和思考,巧妙的將歷史、文化、種族等元素隱藏于荒誕的喜劇情節之下,并且把人物的心理力量極為巧妙的表達給觀眾,也正是這種方式給這部影片帶來了更加深刻雋永的隱喻意味。
參考文獻:
[1] 王亞瓊.《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電影空間的隱喻性[J].西部廣播電視,2014(24).
[2] 斯蒂芬·茨威格. (英)馬修·安德森.王琪峰 編譯.《布達佩斯大飯店》的靈感來源[N].中國藝術報,2014-03-02.
[3] 劉俊杰.布達佩斯大飯店敘事風格與美學特征[J].電影文學,2016(1).
[4] 丁楨楨.韋斯·安德森式電影畫面的敘事風格——以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為例[J].2015(3).
[責任編輯:傳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