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古文理論新辨
◎潘佳佳 潘 瑩 張博宇
姚鼐古文理論新辨
◎潘佳佳 潘 瑩 張博宇
桐城派是清代人數(shù)最多、地域最廣、存時最長、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之所以能開宗立派在于既有完整系統(tǒng)、一脈相承的古文理論,又有大量優(yōu)秀的具有美感特性的散文作品。而其中姚鼐的貢獻(xiàn)至大,前承方苞、劉大櫆,后啟方東樹、曾國藩。他在繼承乾嘉樸學(xué)家考據(jù)思想;中國傳統(tǒng)的文道觀以及方苞“義法”說的前提下,對它們進(jìn)行改造和發(fā)展,提出了自己完備的古文理論,即“義理、考據(jù)、文章”。他出于自身對君子人格理想的終生追求和對程朱品行、學(xué)識的極力推崇和敬仰;幼、青年受堅守理學(xué)思想的姚范及方苞的影響以及個人所存的門戶之見,在考據(jù)之學(xué)成為學(xué)界主潮流的乾嘉之際,仍然固守程朱,獨行宋學(xué)。
桐城派是清代人數(shù)最多、地域最廣、存時最長、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具體明確、系統(tǒng)嚴(yán)密且前后一脈相承的理論和豐富、優(yōu)美的作品兩面旗幟占據(jù)我國散文史上乃至文學(xué)史上一個重要地位。而姚鼐在該派得以成立、發(fā)展和壯大的過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前承方苞、劉大櫆,第一次響亮喊出“桐城派”的口號,后啟方東樹、曾國藩,使其派源遠(yuǎn)流長;他提出的“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統(tǒng)一的古文理論成為桐城派古文創(chuàng)作的指導(dǎo)思想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他創(chuàng)作的大量優(yōu)秀古文成為我國散文園林中一棵獨具美感的奇葩。
最先提出義理、考據(jù)、文章的雖系漢學(xué)家戴震,而將這一讀書治學(xué)的研究方法延伸到文藝創(chuàng)作中,并作為作文指導(dǎo)思想的則是姚鼐。關(guān)于此說前人早已證實,吳孟復(fù)在《桐城派三題》中對戴、姚二人的話作了三種解釋:一、義理指哲學(xué),考據(jù)(制數(shù))指科學(xué),詞章(文章)指文學(xué);二、義理指理論,考據(jù)指資料(搜輯、鑒別),詞章指文理、文法;三、義理指宋學(xué),考據(jù)指漢學(xué),詞章指古文。按一言,是學(xué)科分類;按二言,是指治學(xué)的方法;按三言,是就學(xué)術(shù)的流派而言之。戴震講的重在二,即治學(xué)方法。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后有訓(xùn)詁,有訓(xùn)詁而后有義理。訓(xùn)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xùn)詁之外。”(《經(jīng)籍纂詁序》)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即為由考據(jù)而明義理的典型。而姚鼐重在寫散文,如《登泰山記》,不涉神怪,不事阿諛,既非“廟堂文學(xué)”,亦非“山林文學(xué)”,就義理而言,是純正的;對泰山地理沿革,以目擊與古書相參證,是有所考據(jù)的;而文字尚簡潔,描寫生動。這是他理想中的“三者合一”的典范。
我這篇小文寫作的中心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考察姚鼐提出“義理、考證、文章”的古文理論的背景緣由;二是討論在“為考證而考證,為經(jīng)學(xué)而治經(jīng)學(xué)”的乾嘉之際,姚鼐何以要“固執(zhí)己見”,獨守理學(xué),奉行程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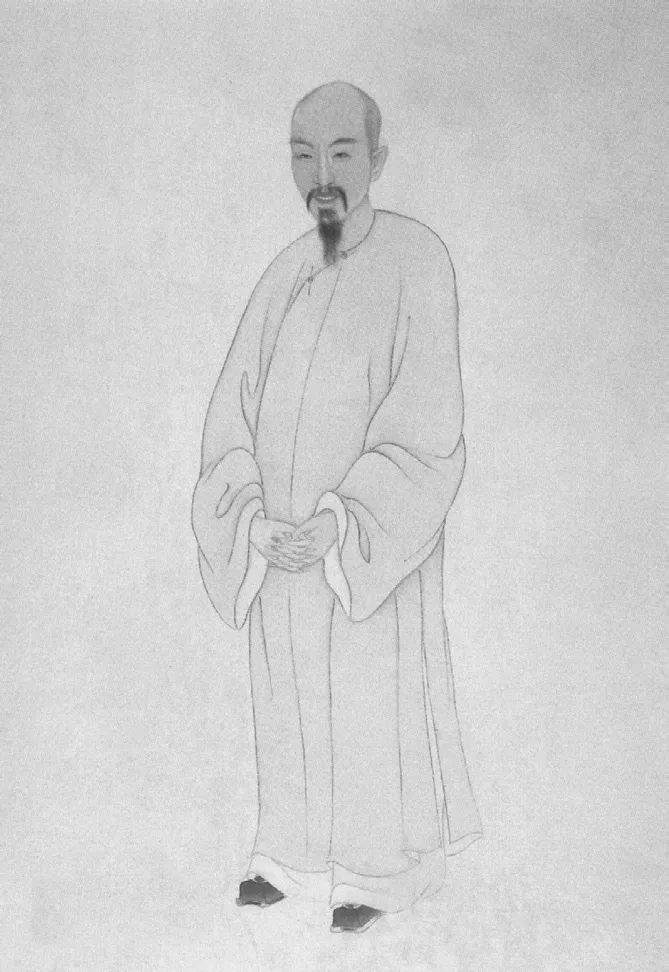
一
首先,姚鼐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并重的古文理論,明顯受到當(dāng)時樸學(xué)家的影響,這毋庸置疑。戴震作為乾嘉考據(jù)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在《與某書》中第一次提出“古之學(xué)問之途,其大致有三”的說法,他說:
古之學(xué)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義理,或事于制數(shù),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之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為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子之文,亦惡睹其非藝歟?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諸君子不愿據(jù)其末,畢力以求據(jù)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藝也。……圣人之道在六經(jīng),漢儒得其制數(shù),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shù)。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巨觀,目不全收,其可哉?
姚鼐在《述庵文鈔序》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他的古文論觀,他說:
余嘗論學(xué)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jì);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dāng)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太過,而智昧于所當(dāng)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為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
姚鼐所提出的“義理、考據(jù)、文章”三方面內(nèi)容,從字面上理解與戴氏的并無多大差別。戴震所說的“制數(shù)”也即考證。而姚鼐之所以提出“考證”與“義理”、“文章”并重,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是對當(dāng)時樸學(xué)勢力過大所作的一種退讓。曾國藩指出姚鼐此說初出,頗遭文壇的冷遇,甚至陷入“孤立無助”的境地。他說:
當(dāng)乾隆中葉,海內(nèi)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博引,考核一字,累數(shù)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xué),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fù)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zhì),而后文有所附,考據(jù)有所歸。一編之內(nèi),惟此尤兢兢。當(dāng)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xué)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這都足見姚氏“義理、考證、文章”的提出確是受到當(dāng)時炙熱的考據(jù)學(xué)風(fēng)的影響。但同中有異的是兩派對于“道”與“藝”關(guān)系的不同觀點。姚鼐認(rèn)為,“道”與“藝”不可分,道是藝的所指,而藝是道的彰顯,二者猶人之兩腳,缺一不可。他說,“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重。”“吾嘗以為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cè)岫选F堄械煤蹶庩杽側(cè)嶂钥梢詾槲恼轮馈!弊詈米蠲赖奈恼卤厝皇堑琅c藝的完美結(jié)合,偏廢其一則非至文。而考據(jù)學(xué)家崇尚的是“文”的內(nèi)涵,而非“文”的表現(xiàn)方式。如王昶所說“湛于經(jīng)史,以養(yǎng)其本。”焦循更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辭章之有性靈者,必由于經(jīng)學(xué)。”戴震主張“以道為本”,認(rèn)為學(xué)問之事,有本有末,道為本,藝為末。程廷祚認(rèn)為,文章“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于是體例繁興,篇章盈溢,徒敝覽者之精神,而無補(bǔ)于實用,亦奚以為!”
姚鼐的“義理、考證、文章”之說雖受戴震的啟發(fā),但他認(rèn)為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相濟(jì)”、“兼長”,而“義理”與“考證”也需有一個度,否則便“其辭蕪雜俚近”,和“繁碎繳繞”,不重視文辭而一味講求義理、考據(jù),不僅影響文章的美感,而且直接關(guān)系到明志達(dá)道。“明道義,維風(fēng)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dá)其辭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戴震則認(rèn)為三者之中,考證、義理占首位,而文章之得道與否,取決于考據(jù)功夫以及對義理的理解,文章是“等而末之者也。”樸學(xué)家是通過訓(xùn)詁考據(jù)的方式探尋六經(jīng)蘊(yùn)意以窺圣人之道。恰如鄔國平指出,戴震文論的首要看法是“求義理也就是求大道,考核、文章都要服從于‘聞道’的目的”,但是“考據(jù)是探求義理的基礎(chǔ)和保證”,而“與義理、考據(jù)相比,從事古文之學(xué)是‘等而末者’”。
段玉裁說:
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作者胥是道也。……后之儒者,畫義理、考據(jù)、文章為三,區(qū)別不相通,其所為細(xì)已甚焉。夫圣人之道在六經(jīng),不于六經(jīng)求之,則無以得圣人求之義理,以行于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姚鼐提出“義理、考證、文章”的古文理論受樸學(xué)家戴震的啟發(fā),但二者所指稱的對象不同,戴是就治學(xué)而言,而姚所指的乃是古文創(chuàng)作。無論是戴震所說的治學(xué)還是姚鼐所講的古文創(chuàng)作,最終目的是一樣的,即通達(dá)“義理”,也就是所謂的“道”,而考證、文章都只是途徑,也就是所謂的“藝”。但在對于“道”與“藝”的關(guān)系的問題上兩派又存在巨大分歧,姚鼐認(rèn)為“道”與“藝”,“義理、考證、文章”不可偏廢其一;樸學(xué)家則認(rèn)為,文章依附于義理,而義理又必由考據(jù)得之。
其次,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道觀”的因革。在天人合一、自然萬物一體的哲學(xué)思想的基礎(chǔ)之上,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出現(xiàn)了一個自始至終、前后相續(xù)、牢固不破的重要命題,即“文——道”觀。
我從何處而來,去往哪里?天地萬物、宇宙眾生都由誰所生?四時交替、日出日落都由誰來掌控?這類最原始、最根本性的問題是哲學(xué)思考的終極目標(biāo)。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思維中存在著一二三的概念。“一”是所有客觀存在的事物的源頭,包括物質(zhì)的、精神的,即所謂“道”,它非可親聞目睹的具體實物而又真實的存在并起著決定性作用,“道”的具體化即為“氣”,它通過不同形式的組織創(chuàng)造眾生萬物。“道”和“氣”都具有“一”的特性,但又有各自的特點,“道”具有形而上的特征,而“氣”則具有形而下的特點,“道”是“氣”的統(tǒng)領(lǐng),“氣”是“道”的具體化。“二”本身并非物或概念,而是指形成萬事萬物的“氣”所具有的兩種特性,即陰、陽。所有客觀存在的事物都可以按陰陽進(jìn)行分類。天、日為陽,地、月為陰;雄性為陽,雌性為陰。“三”是泛稱概指,統(tǒng)稱一切為人所知、不為人知的存在。因此,在中國古代哲學(xué)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便成了蒂固根深的思路。在這種哲學(xué)思想的指導(dǎo)下,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道觀”便應(yīng)運而生。在古文論家們看來,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鳥蟲魚,文章藝術(shù)都由道而生,而這種觀而不得、測而不知、觸而不及的“道”只有先賢圣人才能洞察透析。先賢圣人為了眾生可以了解“道”,于是著書立說,發(fā)言闡論,這樣,任何讀書人、立言者、著文之徒都必須遵圣人之旨以達(dá)大道。劉勰在《原道篇》中將這種思路表達(dá)得淋漓盡致。他說: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jié)響,調(diào)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瑝:故形立而章成矣,聲發(fā)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之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為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八卦,《洛書》韞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明而已。
至唐代中葉,伴隨著思想混亂、王朝衰微、民風(fēng)退化,傳統(tǒng)儒人挺身而出,重新扛起救道裨世的大旗,而韓愈則是此陣營中的典型代表。他以孔孟的正統(tǒng)傳人自命,以古文為思想變革的武器,“文以載道”的口號雖非出自他之口而實由他肇其端。他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書》)
桐城派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勢力最大、分布范圍最廣、參與人數(shù)最多、影響最大的古文派別,他們堅守的是正統(tǒng)儒家思想,以繼承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而自負(fù),在其骨髓深處是要肩負(fù)起“衛(wèi)道”的使命。方苞說:“學(xué)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認(rèn)為程朱是得孔孟道統(tǒng)的真?zhèn)鳎娜藢W(xué)士只能頂禮膜拜,“推其緒而廣之”,而“文”的功能也被概括為“因文以見道”。而姚鼐對于做純粹的文人很是不屑,他說:“是故君子求乎道,細(xì)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xì)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志于道者是君子,志于技者是細(xì)人,文章即使達(dá)到司馬相如、司馬遷、班固、李杜、韓柳歐曾蘇氏之“至”而不以明道、發(fā)道為目的亦“猶技也”。所以方苞打出“義法”的旗號,姚鼐迫于當(dāng)時學(xué)界思潮的巨大壓力雖對方氏“義法”理論進(jìn)行調(diào)整和改造,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位一體說,但核心仍是“義理”和“文章”,“考證”與“文章”一樣,只是發(fā)明義理、通達(dá)道的手段和途徑,所謂“文章、學(xué)問一道也”。但應(yīng)指出的是,方苞、姚鼐雖走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道觀的老路,雖以韓歐古文的繼承者自負(fù),但二者的“道”所指稱的對象不同,韓愈、歐陽修所謂的“道”指的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孟之道;而姚鼐等心目中的宗主是程朱,因此所謂的“道與藝合”亦即文學(xué)創(chuàng)作需與程朱理學(xué)相統(tǒng)一。姚鼐對程朱理學(xué)雖也有懷疑,但基本立場是肯定的,并且對所守的“道”即理學(xué)是十二分堅定的,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動搖,“大丈夫?qū)幏柑煜轮豁t,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由于他與此前的理論家或古文家所堅持的“道”不同,因而偶爾出現(xiàn)相矛盾的言語,即他雖以韓歐古文的繼承者自命而又對韓歐有所不滿。他說:
夫之技耳,非道也,然古籍以達(dá)道。其后文至而漸與道遠(yuǎn),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而況以下者乎?(《復(fù)欽君善書》)
最后,是對方苞“義法”說的繼承與發(fā)展。方苞是桐城派的初祖,他所提出的“義法”說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lǐng)和旗幟。“義法”一詞,最早見于《墨子·非命》。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表序》中說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但把“義法”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法度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卻始于方苞。他說: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fā)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
方苞的這段話為后來桐城文章定下了基調(diào),無論劉大櫆、姚鼐如何豐富發(fā)展其文論,卻始終以是否有物、有序——尤其以是否有序作為得文章正統(tǒng)與否的基本準(zhǔn)則。劉大櫆說:“古人文字最不可攀處,只是文法高妙”,姚鼐說:“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吳德旋稱“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強(qiáng)調(diào)的都是“法”,而所謂的“法”即姚鼐所說的“命意、立格、行氣、遣詞,理充于中,聲振于外,數(shù)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這是理論上的主張,實際學(xué)習(xí)的范本是歸有光、方苞圈點的《史記》和姚鼐圈評的《古文辭類纂》。按方苞的見解,“義法”有廣狹之分,所謂廣義“義法”就是以“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這是一切“深于文者”最為理想的“成體之文”;狹義的“義法”主要指來自史傳的敘事傳統(tǒng),即文章寫作中的具體法則,諸如剪裁、謀篇、提挈、頓挫以及古文中碑傳表書一類的藝術(shù)技巧等。從他的創(chuàng)作實際來看,方苞本人其實偏向于“義法”的狹義之說。
方苞“義法”說一出即遭到漢學(xué)家們的抨擊和嘲諷,他們明確地反對古文義法,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兩點:一是雙方立場和所指對象不同;二是輕視方氏的學(xué)問。惠棟的好友、吳派學(xué)者的前驅(qū)之一沈彤,既有扎實的考據(jù)功夫,對“三禮”有精湛的研究,又曾經(jīng)從方苞學(xué)習(xí)文章義法,劉聲木稱其文“深厚古質(zhì),格律端謹(jǐn),不事文飾,務(wù)蹈理道,無嘩囂浮侈之習(xí)。”他一方面贊賞方苞,肯定其“義法”說,在《沈師閔韓文論述序》中,他說:“今天下之善論古文者,吾得二人焉,曰方公靈皋,曰沈君師閔。二人者,皆能上下乎周漢唐宋元明名世之文,較其利與病之大小淺深而辨析之。而其為教也,方公舉左氏、司馬氏之文以為文章之歸極,而詳明其義法;師閔則舉韓文公之所作以為著作之軌范。……蓋方公為成學(xué)者設(shè),而師閔與始學(xué)者謀。”另一方面他又從經(jīng)學(xué)研究的立場對“義法”的使用重新規(guī)范,以求得學(xué)術(shù)與文章的折中,在沈彤看來,文應(yīng)與學(xué)相濟(jì),他說:
讀古書獲其意義之真,凡所發(fā)明,皆大有裨于后學(xué),則其言不可不及時以著于篇。夫古書自群經(jīng)、諸子而外,其意義之深且遠(yuǎn)者,莫若左之《傳》、屈之《騷》、司馬之《史記》、杜之詩、韓之筆。讀之者必求之訓(xùn)詁與夫名數(shù)、象物、事故之屬,而后其文辭可通;必求諸抑揚(yáng)輕重疾徐出入明晦,與夫長短淺深縱橫斷續(xù)之際,而后其神理可浹。文辭通、神理浹,而后其意義之真者可獲。
沈彤對自己的這段論述很是得意,認(rèn)為其“頗詳為學(xué)與立言之道,與其所論古文制法相濟(jì),所謂著述,如斯而已。”可見沈彤的根本目的是求真,而“為學(xué)與立言”是求真的途徑,他認(rèn)為只有通過求疏訓(xùn)詁、解釋名物,才能通文辭,這是學(xué)的一面;而只有通過對“義法”的把握,于“抑揚(yáng)輕重疾徐出入明晦”與“長短淺深縱橫斷續(xù)”等修辭之中才能理解古書之“神理”,這是文的一面。如此文、學(xué)相濟(jì),“而后其意義之真者可獲。”這是站在經(jīng)學(xué)研究的立場上,以闡明經(jīng)學(xué)為目標(biāo)對“義法”說作了重新的解釋,與方苞源自史傳之學(xué)而立足古文自身的狹義“義法”的概念顯然風(fēng)馬牛不相及。劉奕認(rèn)為“當(dāng)義法從文之法變成研經(jīng)之法時,也就為后來學(xué)者否定義法埋下了伏筆。”
錢大昕是繼沈彤之后明確反對方苞古文“義法”的,他在與朋友論古文的書信中輕蔑地說:“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于義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
應(yīng)該注意的是,錢大昕對“義法”的理解與方苞有根本的不同,他所說的法并非“言有序”之法,而是古書義例、通例,是一朝制度、百代沿革。他強(qiáng)調(diào)“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在他的《潛研堂文集》中,很多是發(fā)明義例,以資考證之作,嚴(yán)密精確。此外,錢大昕還特別重視制度沿革,他說:“竊謂史家所當(dāng)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在錢看來,這三端不僅是史學(xué)基礎(chǔ),也是文章“義法”之所在,方苞未能究心于此,所以才被嘲笑為不懂“古文之義法”。
由以上例證可以看到,由于經(jīng)學(xué)家站在學(xué)術(shù)古文的立場之上對方苞所提的“義法”說竭力攻擊,以學(xué)術(shù)文章的標(biāo)準(zhǔn)去要求文學(xué)化文章,這顯然是不得當(dāng)?shù)摹N覀冋f古文的應(yīng)用范圍極廣,兼有實用與抒情的功能,寫作者盡可以各取所需,各執(zhí)一端。漢學(xué)家往往從學(xué)術(shù)考論的角度出發(fā),考慮的是考訂和析理的充分有效和清晰明徹;而方苞所提的文法主要來自史傳的敘事傳統(tǒng),講求的是章法結(jié)構(gòu)、技巧布局,兩者雖格格不入但可以并存共融,各發(fā)揮其所長,問題在于方氏要標(biāo)榜自己為古文正宗,以裁定天下文章,這自然會招致經(jīng)學(xué)家不客氣的批判。
方苞受到經(jīng)學(xué)家們非議的另一原因在于他好在理論上標(biāo)榜文與學(xué)的結(jié)合,以顯示自己同樣具有大學(xué)問。他說:“茍無其材,雖務(wù)學(xué)不可強(qiáng)而能也;茍無其學(xué),雖有材不能驟而達(dá)也。……若古文則本經(jīng)術(shù)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偽。”他自己也以經(jīng)學(xué)自負(fù),從他對劉大櫆、沈彤二人的評價中也可看出方苞在古文寫作中重視學(xué)問的自覺意識。他說:“今文士惟耕南、冠云足語此。耕南才高而筆峻,惜學(xué)未篤;冠云特精潔,肯究心于經(jīng)。”本來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增強(qiáng)學(xué)習(xí),擁有深厚的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對于加深文章的厚度與深度是有益無害,旁人也無可厚非,但倘若越俎代庖,以己之短較他人之長還以己說號召文壇,自居宗主則是不明智的選擇,因此他受到以學(xué)問見長,功底深厚的考據(jù)家的非議也在所難免。許宗彥《杭太史別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說方苞常以經(jīng)學(xué)自負(fù),結(jié)果遇到杭世駿就相形見短了。“國子監(jiān)嘗有公事,群官皆會,方侍郎以經(jīng)學(xué)自負(fù),諸人多所咨決,侍郎每下己意。太史至,征引經(jīng)史大義,蜂發(fā)泉涌,侍郎無以對,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仆為?’遽登車去。太史大笑而罷。”
方苞以古文家的面孔出現(xiàn)在文壇上,他提出的“義法”說主要來自史傳文學(xué)的敘事傳統(tǒng),他本可以在文學(xué)化古文的領(lǐng)域里縱橫議論、抒情言性,而他卻偏要向?qū)W術(shù)古文靠攏,并以具有理論性質(zhì)的“義法”說去衡量、裁定包括學(xué)術(shù)古文在內(nèi)的所有文章。此外,方苞常以學(xué)問自居,在作品中逞才使學(xué),結(jié)果遭受到求真務(wù)實、考據(jù)功夫深厚、堅守學(xué)術(shù)古文規(guī)范的經(jīng)學(xué)家們的強(qiáng)烈抨擊,也讓煢煢孑立于東南的姚鼐感到苦惱。姚鼐在給劉大櫆的信中將這種心境表露無遺,他說:“鼐于文藝,天資學(xué)問本不能逾人,所賴者,聞見親切,師法差真。然其較一心自得,不假門徑,邈然獨造者,淺深固相去遠(yuǎn)矣。……而流俗多持異論,自以為是,不可與辨。”姚鼐始終以方苞作為桐城派的初祖,以“義法”說作為其派的旗幟與口號,有承續(xù)方、劉遺韻而開宗立派的自覺意識,面對當(dāng)時學(xué)界對方苞及其“義法”說的批判聲,姚鼐一方面以筆代舌、著言立說,與反對者互相辯論;另一方面吸收經(jīng)學(xué)家們的意見,對方苞的文論加以調(diào)整。其實,姚鼐對文學(xué)趣味的欣賞要高于他對學(xué)術(shù)真知追求的熱情,在方、劉二人中,他的實際偏好在劉而不在方。我們看在《古文辭類纂》中選入的劉大櫆的文章遠(yuǎn)多于方苞即一目了然。但迫于當(dāng)時學(xué)界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對方苞的“義法”說進(jìn)行改造和完善,目的在于使方苞作為古文宗主的地位合法化,使“義法”說的理論合理化。正如郭紹虞先生說:“他(姚鼐)不必復(fù)據(jù)義法之說,而所言無不與義法說合。他不言義法,即因‘義法’二字不足以盡之;但是仍合義法,即因基礎(chǔ)依舊筑在義法上面。”
姚鼐說:
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為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yuǎn)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崖便不能細(xì)受繩墨,不及望溪矣。(《與陳碩士》)
從這段論述中,我們看到姚鼐一方面肯定文家“義法”,認(rèn)為“不能細(xì)受繩墨”的梅崖不及望溪,這實際上是文的部分;另一方又認(rèn)為方苞的《太史公書》有不足之處,“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yuǎn)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這講的是學(xué)的部分。姚鼐此舉實際上是一種折中的辦法,面對學(xué)界的壓力不可能置若罔聞,但又不能放棄古文的審美性,完全丟掉古文家立身的根本。恰如劉奕所說,“為了獲得時代的認(rèn)同,為了增強(qiáng)古文的表現(xiàn)力,姚鼐于是同時從兩方面著手,一面肯定發(fā)揚(yáng)古文的審美性,一面強(qiáng)調(diào)義理、考證、辭章的結(jié)合,其實即文與學(xué)的結(jié)合,這是要打通古文的文學(xué)與學(xué)術(shù)兩端,以文學(xué)一極為立身之本,同時不斷增強(qiáng)自身的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融通學(xué)術(shù)古文,使得古文家真正獲得古文創(chuàng)作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姚鼐一面堅守古文審美的特性,一面吸收來自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的要求,指出文與學(xué)并存,將方苞的“義法”說發(fā)展為“義理、考證、文章”。他說:“且夫文章學(xué)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jù)者,每窒于文詞;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矜于一者則為“淺學(xué)小夫”。對于兼學(xué)者與詩人于一身的謝蘊(yùn)山,姚鼐表示虔誠的佩服與推崇。“鼐于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非如淺學(xué)小夫矜于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在《述庵文鈔序》中,他再次表述了自己的文與學(xué)并重的古文觀,他贊許王蘭泉先生之文,說:“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考覆,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所謂“高韻逸氣”指的是風(fēng)格,屬文的部分,持的是審美標(biāo)準(zhǔn);而“議論考覆”則就學(xué)術(shù)言,是學(xué)的部分,堅守的是辨真衡博的準(zhǔn)繩。《登泰山記》則是其將文與學(xué)并重,融“義理、考證、文章”于一體的古文理論落實到創(chuàng)作實踐的典范代表。不僅有明麗如花的泰山日出勝景的描繪,還有泰山古長城位置的詳實考證;不僅予人以美的享受,又提供了豐富廣闊的歷史知識。此外,如《游靈巖記》《泰山道里記序》等也是將“義理”、“考證”和“辭章”結(jié)合得較為完美的篇章,既有充實的內(nèi)容,又有較高的審美情趣。
這樣,我們就基本梳清了姚鼐“義理、考證、文章”三位一體的古文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歷史淵源和師承關(guān)系,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單一因素起的作用,而是時代參考、傳統(tǒng)繼承、師承總結(jié)三者綜合影響的必然結(jié)果。文道一體的文論觀讓以君子人格要求自身和規(guī)范社會的正統(tǒng)文人姚鼐義無反顧地肩負(fù)起載道、衛(wèi)道的責(zé)任,明確肯定文應(yīng)載負(fù)道義,發(fā)宣儒家孔孟思想;對方苞的充分認(rèn)同和絕對追從,讓姚鼐有了開宗立派、發(fā)揚(yáng)光大的強(qiáng)烈意識,自覺地接過“義法”的旗幟,并根據(jù)古文家自身的立場和時代思潮的要求對其作了擴(kuò)充、調(diào)整和改造,使其理論更具體、更充實、更有力;在考據(jù)學(xué)風(fēng)日趨月盛,成為學(xué)術(shù)界的主流時,姚鼐審時度勢,容納匯通,終于將本屬研究學(xué)問尤其是解經(jīng)通史的途徑、方法——考證歸于古文創(chuàng)作的旗下,作為其指導(dǎo)原則和方針,明確肯定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要將文與學(xué)結(jié)合起來,既要遵從文學(xué)本身的抒情狀物、藝術(shù)審美的特點,又要提升自身的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加強(qiáng)學(xué)術(shù)研究的才干,使創(chuàng)作出的成品同時具備美感與厚度,使藝術(shù)特性與智識主義共同充斥其間,使敦厚溫雅與詳實嚴(yán)密交融相契。同時,他以“雅潔”作為古文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和審美理想,從而使其文厚實而不凝重,典雅而不失生機(jī),如行山聽溪流,涓涓有聲;如求教于長者,娓娓自如。
二
雍乾之際,特別是18世紀(jì)中葉以后,隨著時代王朝的穩(wěn)定,中央集權(quán)的加強(qiáng),四海宴平的實現(xiàn),最高統(tǒng)治者雖仍以程朱理學(xué)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治國安邦的指導(dǎo)思想,但不似清初順、康之際那樣對其拜服和篤信。我們說順、康之時,由于政權(quán)剛剛確立,四野紛爭遞序發(fā)生,為維護(hù)人心,收籠士人,統(tǒng)治者對被往朝作為統(tǒng)治思想、為士大夫安身立命、被社會普遍接受的程朱理學(xué)采取絕對的信任和依賴,并刻苦鉆研,以身作則自覺奉守。而到17、18世紀(jì),這一趨勢發(fā)生了改變,程朱理學(xué)“轉(zhuǎn)而呈現(xiàn)衰微之勢”,士人由傾心理學(xué)到潛心經(jīng)學(xué)。
雍正帝一方面繼續(xù)遵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tǒng)國策,重視正統(tǒng)儒學(xué),尤其是程朱之學(xué)在政治統(tǒng)治中的作用。同時,也主張“三教并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xué)進(jìn)行改造。乾隆帝對理學(xué)的態(tài)度分兩個不同階段,以乾隆二十年前后為界。前一階段堅持程朱理學(xué)的獨尊地位,但又表現(xiàn)出倡導(dǎo)理學(xué)、經(jīng)學(xué)并舉的態(tài)度。后一階段則以“崇獎經(jīng)學(xué),立異朱子的方式,把學(xué)術(shù)導(dǎo)向尊經(jīng)窮古的狹路之中。”另外,雍正、乾隆時期,朝廷官員的任用也不似康熙朝那樣重視理學(xué)之臣。“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權(quán),正人與之梗者,多置九卿閑曹,終身不遷,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習(xí)理學(xué)者日少,至?xí)Z不售理學(xué)諸書。”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當(dāng)時社會觀念中,不少士子大夫的注意點由理學(xué)轉(zhuǎn)移到經(jīng)學(xué)上。孫嘉淦作為當(dāng)時的國子監(jiān)司業(yè),他向朝廷建議,學(xué)校應(yīng)以經(jīng)術(shù)為本,旨在培養(yǎng)治經(jīng)之能士,并指出了具體的可操作踐行的方案。他說:“學(xué)校之教,宣以經(jīng)術(shù)為先。請令天下學(xué)臣,遠(yuǎn)拔諸生貢太學(xué),九卿舉經(jīng)明行修者為助教,一以經(jīng)術(shù)選士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袁枚以詩人敏銳的目光覺察到了時代的先聲,“近今之士,竟遵漢儒之學(xué),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當(dāng)時經(jīng)學(xué)家甚至以朝代為界限,將歷代解經(jīng)釋典的成果作了高低尚卑的分劃,而宋人之作則位列最下。“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作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jīng)之學(xué),又次則為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后世應(yīng)舉之文。”要明達(dá)古圣賢之道,最佳的也是最有效的辦法是參考周公、孔子之著書,其次是漢儒對周孔經(jīng)典的傳注,又其次是參閱如《五經(jīng)正義》類的唐人疏釋,最末端的是遵從如《朱子語類》的語錄體著作及由明至今的應(yīng)舉文。應(yīng)舉文以朱熹所注的四書五經(jīng)為參考書目,闡發(fā)的是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xué)家們的思想。這樣,孫星衍所最反對的仍是程朱理學(xué)。
上面所引的是上層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傾向和學(xué)術(shù)潮流,與此同時,民間也出現(xiàn)了譏諷理學(xué)的故事。紀(jì)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下列兩則故事: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xué)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yán)詞正色,如對圣賢。忽微風(fēng)颯然,吹片紙落于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會有講學(xué)者,陰作訟牒,為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爭。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對,筆跡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賢不信道學(xué)。今日觀之,灼然不繆。’
人前大談義理,高論仁義,以衛(wèi)道士自負(fù),義正詞嚴(yán);人后則求己利、謀私欲,往往適得其反,自露丑態(tài),貽笑于人。當(dāng)時確有不少士子以理學(xué)為晉身之具,弋取功名之階梯,出現(xiàn)大批“假道學(xué)”,造成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局面,這是上至皇帝士大夫階層,下至民間百姓對喜言性理、坐而論道的理學(xué)家產(chǎn)生厭惡的原因之一,由此將矛頭直指程朱。
自雍正朝開始,理學(xué)一方面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而處于正統(tǒng)地位,另一方面受到來自最高統(tǒng)治者、士階層和民間百姓的強(qiáng)烈沖擊,講求辨?zhèn)巍⒂?xùn)詁考證、周密詳實的樸學(xué)有后起而代之之勢。然而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卻仍然對程朱興趣不減,死心塌地并有繼承程朱大業(yè)以正風(fēng)俗、維人心之壯志豪情。方苞說:“學(xué)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姚鼐更是直言“程朱猶吾父師”,他對那些詆毀、訕笑程朱之徒咬牙切齒,甚至放言詛咒,一改其昔日給人的溫恭謙和印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方東樹作為姚鼐的弟子,也直接老師的衣缽,對程朱篤信遵從,他在《漢學(xué)商兌重序》中說:“程朱之道無二,欲學(xué)孔子而舍程朱,是猶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階巾戶也。”這樣,在乾嘉之際,一邊以考據(jù)家為陣營,一邊以桐城古文家為陣營,兩者對儒家經(jīng)典的遵從各有所依,前者奉守漢代經(jīng)學(xué),后者以宋代經(jīng)學(xué)為圭臬,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漢、宋學(xué)之爭。所謂漢學(xué),梁啟超在他的學(xué)術(shù)名著《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中作了概括式的表述,“其(考據(jù)學(xué)派)治學(xué)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其研究范圍,以經(jīng)學(xué)為中心,而衍及小學(xué)、音韻、史學(xué)、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于兩漢,故亦有‘漢學(xué)’之目。”而所謂的宋學(xué),“即宋代經(jīng)學(xué)的簡稱。宋學(xué)……其經(jīng)學(xué)特點為訓(xùn)釋經(jīng)典,注重義理,授引天理、性命為說,兼雜佛、道以解經(jīng)。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尤重‘四書’,摒棄漢唐舊注,使經(jīng)學(xué)理學(xué)化。”
如前所說,清代中葉,理學(xué)已成衰微之勢,“頗無顏色”,而“漢幟大張”,堅守漢代經(jīng)學(xué)的考據(jù)之風(fēng)占據(jù)了思想界的主潮流。然而,姚鼐卻仍然固守程朱之學(xué),即使處在“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的煢煢孤立的狀態(tài)中也不改旗易幟,他雖也將考證納入其古文理論之中,但仍將其置于義理之后而位列第二,考證只是為明義理的途徑與方法,在這一思想的指導(dǎo)之下,他提出了自己具體、系統(tǒng)的文論觀,即“義理、考證、文章”。這其中的深層緣由不得不令人深思,同時也是我們深入了解姚鼐其人思想觀、文論觀的突破口之所在。
就某看來,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姚鼐本人對君子人格理想的堅守和追求以及其對程朱所擁有的君子品行的充分肯定;二與幼年受叔伯、鄉(xiāng)里名士的影響以及后來接受的教育不無關(guān)系;三是其自身所存的門戶之見。
在姚鼐的文集中,“君子”一詞出現(xiàn)頻率最多,據(jù)統(tǒng)計,除“君之子”、“君子曰”外,尚有107次之多。讀書做官是那個時代為文人安排的最好出路,而絕大多數(shù)文人所走的也都是這一條道路,姚鼐同樣不例外。他先后五次赴京考進(jìn)士,然而皆名落孫山,直至第六次方才考中,他自己不無感慨地說道:“鼐走南北,五躓一升。”姚鼐之所以能承受五次落榜的沉重壓力,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并非單純?yōu)樽龉俣非蠊γ摗⒐庖T楣,這從他中年即主動辭官歸里的事實中可以得到顯明的應(yīng)證,其深層原因毋寧說是他對堯舜圣賢、周孔君子人格理想的向往與追求。
姚鼐在品評他所贊賞的人物時,多以君子、圣人喻之。如《贈陳伯思序》中,他說:“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yuǎn)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jìn)乎圣人之教者,伯思也。”又如在給孔子后裔孔僞約作的《儀鄭堂記》中,他說:“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于慕圣,有孔氏之遺風(fēng)者歟?”姚鼐既以此評論他人,而其自身也以能成為“篤于慕圣”、“進(jìn)乎圣人之教”的君子作為人生的終極追求。他辭歸鄉(xiāng)里后,曾有人寫信給他,希望他能復(fù)任官職,他在回信中鮮明地表達(dá)了這一人生理想。“仆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跡仕于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仆雖愚,能不為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于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茍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于時,其道可濟(jì)于眾。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為慕利;雖因人驟進(jìn),而不為貪榮。何則?所濟(jì)者大也。”在姚鼐看來,古之君子出仕為官并非茍求一人之利、一族之榮,而是“度其志可行于時,其道可濟(jì)于眾”。倘若其志可行于時,其道可濟(jì)于眾,即便遑遑求得官職,因人晉身廟堂也可以接受。姚鼐的一生即以能否行時濟(jì)眾為進(jìn)仕隱退的準(zhǔn)則,青年之時,滿懷君子理想,渴望以己之才濟(jì)天下蒼生,即便五次失利也絕不灰心;當(dāng)其真正身居官場之時,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與理想的差距實在太大,自己所持之道不被見重,于是毅然辭官,以壯年之身隱于書院,直至終老。
姚鼐以君子的人格理想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同時描繪和歌頌了一系列的君子形象,并以君子的人格標(biāo)準(zhǔn)對當(dāng)時的社會作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據(jù)周中明的梳理和統(tǒng)計,姚鼐筆下的君子形象有八個類型,它們分別是“為君子所貴”,勇于為國捐軀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形象;以誠為君子之道,撫安眾庶的官吏形象;以身訓(xùn)士,教之必為君子的學(xué)官形象;守有介,行中繩,篤行君子的教師形象;樂善好施,世德相承的善人形象;出于至情,為君子所許的孝子、孝女形象;“有君子之德”的女君子形象和為實現(xiàn)君子之志而厚德載物、自強(qiáng)不息的大丈夫形象。同時,姚鼐持君子的人格標(biāo)準(zhǔn)對當(dāng)時社會進(jìn)行了六個方面的揭露、批判,分別是以君子之仕,揭露、批判封建官場使君子無容身之地;以君子之仕,揭露、批判“小人之仕”禍國殃民;以君子之義,揭露批判統(tǒng)治者“去廉恥而逐利資”;以君子之為學(xué),揭露批判當(dāng)時“學(xué)之敝”;以君子之心,揭露科舉不公,坦然對待個人功名和以女君子之賢惠,襯托和揭露“士大夫之德日衰于古”。
姚鼐對現(xiàn)實生活中有君子品行之人熱情贊揚(yáng),不吝筆墨,并且眼界頗為寬廣,上至英雄、大丈夫,下至教師、女子;對日益衰壞的世俗民風(fēng)痛心疾首,“蓋人心之變甚矣”,“風(fēng)俗日頹”;對政府官僚的腐朽墮落,對沽名釣譽(yù),以道學(xué)作為榮身之階的勢利之徒不遺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他既然以孔孟的正統(tǒng)傳人自命,以“救濟(jì)人病,裨補(bǔ)時闕”為自己的責(zé)任,就需要在歷史上找到一位品行端正、修養(yǎng)精深,為世人尤其為讀書人所認(rèn)可的,有廣泛影響力的具體鮮明的榜樣。孔孟畢竟太過遙遠(yuǎn),并且由于歷代的推崇孔孟早已成為圣人,是普通人高不可攀的。于是他將目光投注到了朱熹身上,因為朱熹作為理學(xué)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元明清三代都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上有廣泛的推廣。更為重要的是,姚鼐并非別有用心的故意夸大和抬高朱熹,而是出于忠實的敬仰和拜服,他說:“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應(yīng)該說,他對程朱之學(xué)的信奉首先來自他對程朱之品行的認(rèn)可與贊賞。姚鼐既然要肩負(fù)起維護(hù)正道、糾補(bǔ)風(fēng)化的重責(zé),就必須有一套完整系統(tǒng)的思想理論作為指導(dǎo)和宣傳,他雖也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獨到見解,但終非博洽精深的思想家,于是他將為統(tǒng)治階層所接受,為百姓所熟知的宋代理學(xué)拿過來,作為自己搖旗吶喊的口號,并作為古文創(chuàng)作理論的核心。因為在他看來,文章的目的并非純粹的娛樂,而是擔(dān)負(fù)著發(fā)明義理,維護(hù)風(fēng)俗的社會責(zé)任,“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fēng)俗,以詔世者。”這樣,程朱及其理學(xué)不可動搖的地位便在姚鼐那里得以確立,不容許任何人對其進(jìn)行攻擊或詆毀,因為對他們的攻擊、詆毀即意味著對惡劣品行、衰壞民風(fēng)的慫恿和推波助瀾,其罪不可恕。
姚鼐出生書香門第,幼年主要師從伯父姚范和同鄉(xiāng)劉大櫆,“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及長,受經(jīng)學(xué)于伯父編修君,學(xué)文于先生。”(《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姚范進(jìn)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詩、古文、經(jīng)學(xué)成就都很高。史載范平生無他好,唯獨刻苦讀書,致力于經(jīng)史,論學(xué)大旨以駿博為門戶,卒歸于平和篤實;論文思想承方苞而來,著有《望溪文集評點》,梁啟超《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中有記載說:“苞桐城人也,與同里姚范、劉大櫆共學(xué)文。”可見姚范古文理論實承方苞而來,是一脈之流。姚鼐既從幼年受學(xué)于叔伯姚范和同里劉大櫆,而范、櫆二人又都與方苞交往甚密并堅守方氏的“義法”理論;另外,姚鼐入京后又親自拜于方氏門下,親聆教誨。這樣,姚鼐對“義理”的堅決態(tài)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史載姚鼐早年心慕樸學(xué),對戴震的學(xué)問十分佩服,曾經(jīng)寫信給戴震,愿入其門下執(zhí)弟子禮,戴以治學(xué)門徑的不同回信予以謝絕。章太炎先生站在考據(jù)學(xué)家的立場上,以此為姚鼐后來持程朱之旗與以戴震為首的樸學(xué)家分庭抗禮甚至詆毀之的憑證。他說:“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愿斂衽為弟子。……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料,學(xué)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lǐng),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姚范)從子姚鼐,欲從震學(xué)。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shù)持論詆樸學(xué)殘碎。”姚鼐因求師于戴震被拒絕而心存“不平”甚至怨恨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理解,但倘若僅以此為憑證解釋姚鼐之所以別列宗主、另開派別、辯難樸學(xué)則恐難成立。然而姚鼐常以己之短而硬要與以考據(jù)見稱的戴震一較高下,并樂此不疲地糾正后者的一些細(xì)枝末節(jié)的錯誤則又明顯有存?zhèn)€人門戶之見的嫌疑。
姚鼐基于自身對君子人格理想的終生追求和對程朱品行、學(xué)識的極力推崇和敬仰;幼、青年受堅守理學(xué)思想的叔父姚范及同鄉(xiāng)方苞的影響以及個人所存的門戶之見,在“為考證而考證,為經(jīng)學(xué)而治經(jīng)學(xué)”的乾嘉之際,仍然堅守程朱理學(xué)的獨尊地位,從而使當(dāng)時的思想界多了一主張、一意識、一主義。
作者單位: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 050017
潘佳佳,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校長辦公室科員,碩士研究生,專業(yè):學(xué)科教學(xué)(語文)。潘瑩,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校長辦公室科員,碩士研究生,專業(yè):基礎(chǔ)醫(yī)學(xué)。 張博宇,河北科怡科技有限公司辦公室秘書,本科,專業(yè):服裝設(shè)計與工程。

